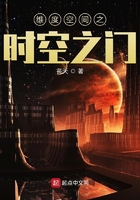“我想起你是谁了。”
我对南宫月这么说的时候,望见他眸中,蓦然升起了一股奇异的光亮。
他的表情亦是有些奇异而微妙的,唇边挂着浅浅的笑,问我:“你想起什么啦?”
就好像,在期待着什么一样。
我莫名心虚了一下。
“这里是葬花谷吧。”我小心地措辞着,一边打量着他的神情,“你是那个……传说中‘剑走偏锋’的谷主。”
就在刚才,我想起御北君和我说过的那些话了。
烟萝花,回生铃,葬花谷,南宫月。所有零碎的碎片拼合的时候,过去的对话骤然浮现。
很奇怪,只有当所有的线索汇聚到一起时,才能清晰地回忆起其实很浅显的种种细节。
我的记忆,出了什么问题吗?
为什么单凭零星的蛛丝马迹,永远无法回想起发生过的事情呢?
南宫月脸上的笑消失了。
他抿着唇,像是兴味索然,木着一张脸道:“是啊,就是我。不用这么委婉,江湖上人人都说我心狠手辣。”
后一句话仿佛在赌气,很是情绪化。
然而,我从中嗅到更多的,是……失望?
他究竟在期待什么?
见我一时无言以对,南宫月问我:“你不怕我?”
“怕你什么?”我反问道。
“怕我杀了你啊。”他的语气轻飘飘的。
我顿了顿:“你若是想杀我,就不会大费周折救我。”
“我说了,我并不是什么好人。万一我是想先救护你,然后慢慢折磨着玩呢?”
听到这话,我反而对他展颜一笑。
我笑道:“哥哥,从你对我说出这些话开始,你就不可能真的伤我害我了。”
“更何况……我的命是你救的,左右一条破命,你若是想要,就拿去吧。”
并不是在空口说大话,也不是为了敷衍。
只是因为经历了太多波澜起伏,数次行走在死亡边缘,早已经看开了。
再说了,死在绝世美人手下,不亏!
南宫月安静地注视着我。
我在他的瞳仁中看到了自己的倒影,一脸傻气地抿着嘴,目光却很坚决。
他的表情重新变得无比柔和。
“你多叫我几句‘哥哥’吧。”
红衣的美人将我揽在怀里,他附在我耳边小声地、轻声地低语着,声线有蛊惑般的魔力。
“你这么叫我的话,我永远都不会要你的命的。永远不会。”
我真喜欢他这么抱着我,像哄小孩一样摸摸我的头。
心跳会有一丝丝加速。我知道我从来没有资格奢望能和这样的人有什么千丝万缕的牵绊,所以只是瞬间的失态。
他就像我的亲哥哥一样。
被晾在一旁半天的谢容神情恍惚地看着面前的两人。
他盯着少女发呆。
内心有无数困惑,被笨拙的口舌封住了,他只能尝试着从纷杂的思绪中理出些什么,语无伦次地问:“你、你是他亲妹妹,但你们说的话又不像……”
“我们南宫家的事,轮得着你插嘴吗?”南宫月斜了他一眼,毫不客气道。
这人生得是美。谢容自诩长于名门,见过美人无数,但未曾见过这种比女子还惊艳的男人。
然而浑身上下都渗着一股阴冷的妖气,说话也总是带刺的。唯独对那名少女时,才会像个再和气不过的,好人。
太多违和之处,反而显得古怪了。
他继续盯着少女发呆。
说是兄妹,小姑娘长得跟南宫月并不像。
但是,是好看的。
苍白的,脆弱的。眼中有种……让人想要毁掉的灵气。
崩溃哭泣的时候,一定很漂亮。
……操。
谢容猛地回过神来。
他忍不住在心里骂了句脏话:这南宫家的人,一个两个果然像妖精似的,都不太正常!
他堂堂上京谢氏的公子,怎会产生如此荒诞不堪的念头!
许是见他脸色不对,少女皱了皱眉,向他走了过来。
然后趁他不注意,飞起一脚,迅速地将他手中的剑踢得远远地。
谢容:“……你!”
他下意识伸手抓向她手腕。本以为她看起来内力全无,应该躲不过,熟料他眼前红衣一晃,少女竟以一个极为刁钻的角度避开了他的手,甚至还在他手背上拍了一巴掌。
“啪”地一声脆响。
声音不大,气力也不大,却不知拍到了哪根筋上,那只手一下子麻了,完全动弹不得。
谢容登时傻眼了。
南宫月脸上的笑,亦是微微一滞。
“你既是世家公子,为何总不能好好说话,非要动手?”
“真到说话的时候,又死活不讲道理。”
“你这人怎么这样的啊!”
少女毫无察觉两人异样的脸色似的,反手一指南宫月的方向道:“你记好,我哥哥,是救了你命的恩人。”
“别做狼心狗肺的王八蛋。”
她还想说什么,却被南宫月语调温柔地打断了。
“陌,你出去吧,我跟谢公子聊聊。”
“……好。”她只得乖乖应声退了下去。
房门未被关上。谢容凝视着她,直到那背影消失在火红的凤凰林中,才将视线缓缓移回面前的青年身上。
他们沉默地对视。
南宫月抬步走到谢容面前,面无表情地开口:“我妹妹好看吗?”
谢容敢怒不敢言:“好看。”
南宫月又道:“可爱吗?”
谢容:“……可爱。”
南宫月冷哼一声:“别想了,你做梦都娶不到她的。”
谢容差点又一次被气得经脉断裂:“谁说我要娶她了!我对她一点兴趣都没有!”
“那挺好,反正我也只是给你提个醒而已。”
南宫月漫不经心地掸了掸衣服上不存在的灰。
“不管你想做什么,都是我们二人之间的事。别打她的主意。”
“我姐姐,究竟是不是你杀的?”谢容咬了咬牙。
南宫月失了耐心:“你要问她怎么死的,是死在烟萝花海,没错。”
“要说是死在我手上,也没错。”
“尸体是找不到了。说不定,从那上面长出的烟萝花,正好就是被我用来配你的药的那一朵。”
他嗤笑一声:“就当是你姐弟重聚吧。”
尖锐的话语如同利刃,刀刀扎在心脏上。
谢容差点呕出血来。
他眼眶通红,极力抑制住自己,太阳穴上青色的血管突突直跳。
“我何时,能离开?”
他死死盯着南宫月的脸,一字一句地问道。
“一个月。”南宫月道,“你未痊愈。若放你出谷,出了什么岔子,坏了我的名声可不好。”
“当然,你要是扛得住下猛药的话,最快二十天就可恢复。”
“可以。”谢容深吸一口气,勉强撑起身体,从地上站了起来。
他看也不看南宫月一眼,也不去捡被踢到远处的剑,仿佛放弃了挣扎一般,径直走向床铺。
反常得倒像个不吵不闹只想静养的患者。像是变了个人。
南宫月这下终于满意了。
他表情稍缓,甚至很是欣慰地对谢容点点头:“看来我妹妹说的一番话你也听进去了。既然如此,我也不会刁难你什么。”
“按时出来喝药,痊愈了就出谷去吧。”
他转身向外走去,一边嘀咕着:“以为谁想多留你在这里待着啊……多余又碍事。”
谢容低垂着头。
阳光透过大敞的房门洒了一地金黄,他坐着的床榻却仍是一片昏暗。垂下的黑发挡住了他的面容,将眉眼笼罩在阴影之下。
待得脚步声消失在门外,他才缓缓抬起一双血红的眸。
——姐姐。
牙关用力咬紧,无处可安的悲愤被封在紧闭的唇间,化成哽咽的低鸣。
正如南宫月所言,他奈何不了他,也威胁不到他。
也正如南宫陌所言,哪怕再多仇怨,南宫月也是把他从死亡中救出来的人。弑杀救命恩人,会被天下人唾弃。
他的确不能对南宫月下手。
但是。
恩归恩,仇归仇。
世上有无数种报复人的方式,让人痛苦的方式。不一定需要伤其血肉之躯。
南宫陌……
谢容在内心一遍又一遍地咀嚼着这个名字。
他的眼神,像是陷入绝境的孤狼。
——我们来日方长。
从那气氛压抑的屋子里出来后,我径直走到了自己那屋,站在那头背了我一路的救命恩驴边上看它吃草。
我伸手捋了捋它的毛,见它舒服地一甩尾巴,原地欢快地打起了滚,忍不住笑出了声。
方才沉重的心情稍微散去了些。
虽说对那个叫谢容的青年放了不少狠话,好像底气十足的模样,实际上我心里虚得很。
我替南宫月不值,也替他……担忧。
不知是不是我过于敏感,这位出身正派豪门的谢公子,像个偏执狂。
他真的把我说的话听进去了吗?
他会不会日后找机会又来寻南宫月的麻烦?
要不然干脆往南宫月给他煎的药里做手脚,直接把他杀了得了……不行,这要传出去,江湖上讹传南宫月医术不精,岂不是坏了他神医的美名。
我一通胡思乱想,愁得头都大了。
索性一屁股坐在柔软的草地上,大大咧咧地岔着腿。姿势极其不雅观,好在穿的是合身的长裙,遮得严实。
说来也怪,南宫月一个独身住的男子,却备了很多女子穿的衣服。
而且各种尺寸的都有,甚至还有几岁小孩穿的。
我猜,应该是因为为前来求医的病人们准备的吧?他好细心呀。
屋后是凤凰树林,屋前是大片山野。我就是从那个方向闯进这里的。
视野尽头隐隐能望见大片淡紫的色彩,鼻间仿佛又嗅到那日无孔不入的花香。
我想起御北君跟我说过的话。
“烟萝花是葬花谷独有的药草,开花时香味有剧毒,闻之则陷入迷幻发疯致死。”
但我闻了……没发疯,也没死啊?
是因为南宫月救了我吗?
但御北君不会骗我的。从我道破他身份开始,他就没有对我有过任何隐瞒了。
那双异于常人的碧色瞳仁一直很清澈,眼神亦是干净的。
除了那次我爬到方府墙上绝望地想求他帮我,他却没有出现以外,他一直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如影如随地保护我。
……除了那次。
乍然回想起同那名少年剑客的往事,我有些难过,慌忙打断了自己的思绪。
我哪有什么资格去怪别人呢,就算御北君在,我和神仙哥哥之间的结……也是解不开的。
“哎,女孩子家家的,怎么这么坐着。”
身边突然响起南宫月的声音。一双手将我打横抱起,轻轻松松地放到了驴背上。
我:“卧……我的妈呀!”
他看起来瘦瘦高高的,力气怎么这么大!
南宫月眼里带了笑意,轻轻拍了下我的背,让我坐稳,道:“带你去转转。”
他牵着绳子,步伐悠悠。火红的袖口层层堆叠垂下,衬得露出的一截手腕愈发莹白。
他似乎心情很不错。我忍不住问他:“刚才那事……没影响你吧?”
“你说谢公子?”
南宫月长眸一弯:“十年来见过的怪人多了去,他只是个没长大又闹情绪的小毛孩而已。”
我道:“小毛孩?可你看起来也没多大。”
“我今年二十一了。”南宫月轻言细语道。
“十年前,我十一岁。”
“我记得我最开心的时候,是四岁到十一岁之间的那七年。”
“我收到了一生中最好的一个礼物。虽然后来我失去了那个礼物,还因为那个礼物,失去了一切。”
我不明白他跟我说的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困惑地歪了歪头。
只突然想起来,方且臻也是二十一岁,两人年龄一样,性格却差了太多。
……所以啊,孩子果然不能富养,一富养就要变跋扈纨绔……
南宫月偏过头来,端详着我的脸,好一会儿才转了回去。
“算了。”
“只是想告诉你,不必为我担心。”
“我早已无所畏惧,因为我一无所有。”
心口像被狠狠拉扯了一下,刺痛不已。
明明是用那么平静得仿佛与自己无关的口气说出来的话,为什么我在那一瞬间,那么想流泪呢?
南宫月却没有给我出声安慰的机会。
他语调轻松地道:“你进谷时没有仔细看过烟萝花海吧?我教你怎么辨认哪些已经成熟可以入药,哪些还要等一段时间。”
说着,将我小心地扶了下来。
他又蹲下身,从袖中掏出了什么东西,示意我抬起脚,然后套在我的靴子上。
两只手灵活地不知给什么打了两个结。
“烟萝花很美,却长在尸山血海上。”
“所以,记得套鞋套。”
南宫月站起身,认真地注视着我的双眸。
“别脏了你的脚。”
“那你呢?你不套吗?”我问他,“还有回生铃你带了么?不是说,烟萝花的香味有毒吗?”
那淡香又笼罩了我的全身,然而我依旧没有太多不适感。我有些迷茫。
他只是笑,托起了我的左手手腕。我顺着他的动作低头一看,看见了腕上那根红绳,还有上面色泽温润的红玉。
“这个,材质和回生铃,是一样的。”
南宫月指着玉珠,耐心地对我解释。
“它便是解药。千万不要弄丢,知道吗?”
我惊呆了。
为什么宾以寒送给我的红玉,会是烟萝花的解药?
那么假如,假如我没有认识过他,假如他没有送给我这枚红玉。
我是不是根本不可能,活着来到南宫月面前,而是和众多闯入者一样,变成烟萝花的养料?
“烟萝花是我十年前种下的。”
南宫月牵起我的手,掌心温暖,动作轻柔,带着我向花海中心走去。
“自十年前起,只有它陪着我。”
他顿了顿。
“不过现在,我终于拥有别的了。”
我还未反应过来,傻傻地问:“还有什么?”
他说:“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