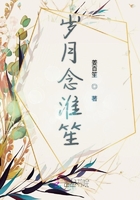两天之后,拍卖会结束,一共售得十五万法郎。
债主们分掉了三分之二,余下的钱分给家属,即一个姐姐和一个小外甥。
那位姐姐收到代理人的信,得知她继承了五万法郎,惊讶得睁大了眼睛。
这个年轻姑娘,已有六七年未见到她妹妹了,忽然一天妹妹失踪,便杳无音信,妹妹的生活情况,无论妹妹本人还是别人,都没有向家里透露。
且说她匆匆赶到巴黎,而认识玛格丽特的人一见都十分惊讶,死者的唯一女继承人,竟是一个胖乎乎的乡下姑娘,生来还从未离开过她的村庄。
她一下子就发了财,甚至不知道这意外的财富从何而来。
后来我听说她回到乡下,沉痛哀悼死去的妹妹。这巨大的哀伤当然也有补偿,她将那笔钱以四厘五的利息存入银行。
制造社会新闻之都巴黎,所有这些情况也一时成为传闻,之后又被人遗忘了,甚至我也几乎淡忘了自己为何卷入这一事件中。不料又发生了一件事,倒使我了解了玛格丽特的一生经历。我觉得她的经历中有些情节十分感人,就产生了写下来的欲望,于是写下了这个故事。
那套房子搬空了家具,开始招租,三四天之后的一天早晨,忽然有人拉响我的门铃。
我的仆人,确切地说,为我充当仆人的门房去开了门,给我拿进来一张名片,说是送上名片那人希望同我谈一谈。
我瞥了一眼,看到名片上印着:
阿尔芒·杜瓦尔
我搜寻记忆,想找出在哪儿见过这个姓名,终于想起那本《玛侬·列斯戈》扉页的题词。
赠书给玛格丽特的人要见我是何来意呢?我吩咐立刻将候见的人请进来。
于是,我看见进来一个金发青年,他高挑个头儿,脸色苍白,还穿着一身旅行服装,仿佛几天没有换下,到达巴黎也没有顾上刷一刷,还是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
杜瓦尔先生情绪十分激动,而且丝毫也不掩饰这种情绪,眼里噙着泪花,声音颤抖着对我说道:
“先生,请您原谅我冒昧来打扰,又穿着这样一套衣服。不过,除了青年之间不必过分拘谨之外,我还特别渴望今天就见到您,甚至顾不上随行李去下榻的旅馆,尽管时间尚早,还是赶到府上,唯恐来访时您不在家。”
我请杜瓦尔先生坐到炉火旁边,他坐下来,同时从衣兜里掏出一块手帕,捂住脸待了一会儿。
“您大概难于理解,”他凄然地叹了一口气,又说道,“一个不速之客,一身这样的穿戴,还流着眼泪,在这种时刻来找您,究竟是何用意。”
“先生,我来拜访,就是想请您帮一个大忙。”
“请讲吧,先生,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您出席了玛格丽特·戈蒂埃的拍卖会吧?”
这个年轻人本来暂时克制了情绪,一讲这句话,又控制不住了,不得不用手捂住眼睛。
“在您看来,我一定显得很可笑,”他又补充说道,“我这样子,还得请您原谅,也请您相信,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您肯如此耐心听我讲。”
“先生,”我回答说,“如果我真能帮上忙,稍微减轻一点儿您所感到的悲伤,那就快些告诉我能为您做什么吧,您会看到,我是个乐于为您效劳的人。”
杜瓦尔先生这样哀痛,实在令人同情,我就情不自禁地要给他行个方便。
这时,他对我说道:
“您在玛格丽特遗物的拍卖会上,买了点儿什么东西吧?”
“对,先生,是一本书。”
“是《玛侬·列斯戈》吧?”
“正是。”
“这本书还在您手头吗?”
“就放在我的卧室里。”
阿尔芒·杜瓦尔得知这一情况,如释重负,连连向我道谢,好像我保存了这本书,就已经开始帮他的忙了。
我站起身,去卧室取出那本书,交到他手里。
“正是这本书,”他边说边看扉页的题词,又翻着书页,“正是这本书。”
两大滴眼泪落到书页上。
“那么,先生,”他说着,冲我抬起头来,甚至再也不想对我掩饰他流过泪,并且还要流泪,“您非常珍视这本书吗?”
“为什么这样问呢,先生?”
“因为我来是请求您把它让给我。”
“请原谅我的好奇心,”我说道,“这本书,是您送给玛格丽特·戈蒂埃的吗?”
“是的。”
“这本书是您的,先生,您就拿回去吧,我很高兴它能物归原主。”
“不过,”杜瓦尔先生面有难色,又说道,“我至少应该还给您所付的书钱。”
“请允许我把它送给您吧。在那样一场拍卖会上,一本书的价钱是无足挂齿的,我也不记得付了多少钱了。”
“您付了一百法郎。”
“不错,”我也颇为尴尬地说道,“您是怎么知道的?”
“这很简单,我原想及时赶到巴黎,参加玛格丽特的遗物拍卖会,可是我今天早晨才到达。我一心想弄到她的一件遗物,便去找拍卖商,请他允许我查一查售出物品与买主的清单。我看到这本书是您买走的,便决定来求您让给我,尽管您出的价钱令我担心,您要拥有这本书,莫非特意留作纪念。”
阿尔芒这样讲,显然是担心我也像他一样,跟玛格丽特非常熟悉。
我赶紧让他放下心来。
“我只是见过戈蒂埃小姐,”我对他说道,“她的去世使我产生的感受,正如自己乐于遇到的一位漂亮女子死了,哪个青年都会有同样的感受。我出席拍卖会,想买下点儿什么,结果执意拍下了这本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概就想斗斗气儿,要激怒一位跟我争夺、似乎向我挑战的先生。我再向您说一遍,先生,这本书就物归原主了。我再次请您接受,切勿像从拍卖商手中买到那样,您再从我手中买走,但愿它成为我们长久交往、建立密切关系的一种契约。”
“很好,先生,”阿尔芒对我说道,他同时伸出手,握住了我的手,“我接受,对您我也终生感谢。”
我很想问问阿尔芒有关玛格丽特的身世,因为,书上的题词、这个年轻人专程的旅行,以及他拥有这本书的强烈愿望,都激起了我的好奇心。但是我也担心,立刻就询问来客,倒显得我不肯收他的钱,只为了有权插手他的私事似的。
他仿佛猜出我的渴望,对我说道:
“这本书您读过吗?”
“整本都读了。”
“我写的那两行字,您有什么看法?”
“我当即就明白,您赠书的这个可怜的姑娘,在您的心目中出类拔萃,因为,这两行文字,我不愿意仅仅看成一般的恭维。”
“此话有理,先生。这姑娘是个天使。拿着,”他对我说道,“您看看这封信。”
他递给我一封信,看样子这信已经读过许多遍了。
我展开信纸,内容如下:
我亲爱的阿尔芒,您的信收到了,您的心肠一直这么好,我要感谢上帝。对,我的朋友,我病倒了,患了一种不治之症。然而,您还是这么关心我,这就大大地减轻了我的病痛。毫无疑问,我活不到那一天了,没有福气握住写这封美好的信的手。假如世上还有什么能治好我的病的话,我刚刚收到的这封信的话语就会治好我。我将不久于人世,又相隔千里,见不到您的面了。可怜的朋友!您的玛格丽特模样大变,今非昔比了。也许还是不见为好,再见面也只能见到这副模样。您问我是否原谅您。噢!诚心诚意地原谅,朋友,因为,您对我造成的伤害,只能证明您对我的爱。我卧病不起已有一个月,我特别重视您的评价,因此每天都写日记,讲述我的生活,从我们分手之时写起,一直到我无力执笔为止。
如果您真的关心我,阿尔芒,您一回来,就立即去找朱丽·杜普拉。她会把这本日记交给您。您在日记中能看到我们之间发生事情的情由。朱丽对我很好,我们经常谈起您。我收到您的信时,恰巧她也在场,我们读着信都禁不住流了泪。
万一我得不到您的音信,她受托等您回到法国时,将我的日记交给您。您不必为这事感谢我。每天重温我一生仅有的幸福时刻,对我大有裨益;如果说您在我的日记中,能看出往事发生的情由,那么我从中则会不断得到安慰。
我很想给您留下一件东西,好让您能一直睹物思人。然而,我这里的东西全被查封,一样也不属于我了。
您理解吗,我的朋友?我快要死了,从卧室就听见客厅里我的债主们派来的人走动的声响,那看守不让人拿走一件物品,即使我不死,也什么都不会给我留下,唯有希望他们等我死后再拍卖。
唉!人就是这么冷酷无情!也许还是我错了,应当说上帝是公正而铁面无私的。
这样吧,最亲爱的朋友,我的遗物拍卖时您就来吧,买下一样物品,因为,什么我也不能为您单独留着,他们一旦发现,就可能控告我侵吞查封的财物。
我要离开的人世有多悲惨啊!
但愿上帝大发慈悲,让我死之前再见上您一面!
我的朋友,十有八九要永别了!请原谅我不能给您写得再长了,那些声称能给我治好病的人总给我放血,结果我的手不听使唤,无力写下去了。
玛格丽特·戈蒂埃
信的末尾,字迹的确不清楚了。
我把信还给阿尔芒。我拿信看的时候,他一定在脑子里又读了一遍,因为,他接过信就对我说:
“谁想得到,这是一名妓女写的呀!”
他忆起往事,情绪十分激动,注视了一会儿信上的文字,最后送到唇边吻了吻。
“一想到人已死了,”他又说道,“要再见一面都没有做到,我也永远见不到她了。一想到她为我做了连亲姐妹都做不到的事,我就不能原谅自己让她就这样死去。”
“死了!死了!临死还思念我,还写信,还念叨我的名字,可怜的、亲爱的玛格丽特!”
阿尔芒不再控制自己的思绪和眼泪,他把手伸给我,继续说道:
“我为这样一个女人痛哭流涕,别人若是看到,就会认为我太天真幼稚了。这也难怪,别人不知道当时我多么残忍,给这个女人造成了多大痛苦,而她又多么善良,多么委曲求全。我原以为是该我原谅她,而如今我却觉得不配她对我的宽恕。唉!能跪在她脚下哭一小时,就是少活十年我也愿意。”
不了解一种痛苦,就难以给予安慰。不过,我极为同情这个年轻人,既然他这么坦诚,向我倾诉了心中的哀伤,我就认为我的话未必不起作用,于是对他说道:
“您没有亲戚朋友吗?去看看他们,要抱着希望,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安慰,而我呢,对您只能表示同情。”
“说得对,”他说着便站起身,在我的房间里大步踱来踱去,“我给您添麻烦了,请原谅。我也没有考虑考虑,我的痛苦跟您没有什么关系,不该来打扰您,讲一件您不可能也根本不会感兴趣的事情。”
“您误会我这话的意思了,我一心想为您效劳,但是很遗憾,我无力减轻您的哀痛。如果我的圈子、我朋友们的圈子能为您排忧的话,总之,无论什么,如果您需要我做的话,那么我希望您完全明白,我十分乐意满足您的心愿。”
“对不起,对不起,”他对我说道,“人一痛苦,总容易神经过敏。请让我再留几分钟,容我把眼泪擦干,以免上街让闲人看见一个小伙子哭天抹泪,就该大惊小怪了。刚才您给了我这本书,就让我非常高兴了。这种恩情,我永远也不知道如何报答。”
“您的友情给我一点儿,”我对阿尔芒说道,“对我讲讲您哀伤的缘由就行了。伤心的事儿讲出来,就多少是一种安慰。”
“此话有理。不过今天,我太需要大哭一场了,对您讲也是断断续续。这段经历,改日我再告诉您,到那时您就会明白,我有理由悼念这个可怜的姑娘。现在,”他最后一次擦了擦眼睛,又照了照镜子,补充说道,“说说看,您是不是觉得我的样子太傻,也请您允许我再来拜访。”
这个年轻人的眼神又善良,又温和,我真想拥抱他。
可是他呢,泪水又开始模糊了他的双眼。他见我发觉了这一情况,便把目光从我身上移开了。
“瞧您,”我对他说道,“拿出点儿勇气来。”
“再见。”他则对我说道。
他极力克制,不让眼泪流下来,匆匆走出我的宅门,简直就像逃走似的。
我撩起窗帘,望见他又登上在门外等候他的轻便马车,刚上车就泪如泉涌,赶紧用手帕捂住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