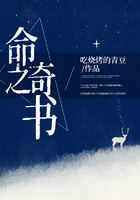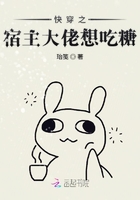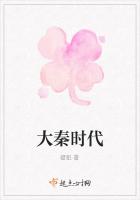——兼谈长篇历史小说的当代启示性
黄国柱
关于清宫后妃的文学艺术作品,已经汗牛充栋,泛滥成灾。即便是一部很优秀的同类题材作品,也非常容易受着胃口已经败坏了的读者的疏远和冷遇。长篇历史小说《孝庄皇太后》的问世,一直没有引起文学界的重视,我认为主要原因并不在于作品本身缺乏激发当代人兴趣的内在机制,而在于受大量艺术品位不高的同类题材作品的“株连”。当然,我并非绝对地扬此抑彼,清宫后妃题材中也不乏优秀之作,但就反映时代的广度、深度以及对当代启示的深刻而言,能与《孝庄皇太后》比肩的并不多。
许多清宫后妃题材的作品旨在揭露后妃生活的奢侈腐败,还有以刻画描摹其性压抑、性苦闷及至淫乱内幕为务的,不能说这些写不得,写得好同样很有意义,问题是“一窝蜂”,把波澜壮阔的社会历史归于几个后妃的专权甚至性压抑的结果,那就失之偏颇了。我之所以推崇《孝庄皇太后》,首先在于作者敢于避开时尚的创作角度和路数,后妃的生活史只是一种表层的现象,作者瞩意的是明末清初的政治史的关节之处,由于立足的高远,一两个后妃的生活便在全局中有了她恰如其分的分量。由此生发开去,一个广阔的历史时代便被揭开了帷幕,这是政治繁复、战云密布的时代,由于一个女人的出现和作为,大清王朝才写下了众所周知的最初的史章。
孝庄皇太后,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儿子、清太宗皇太极的妃子,清世祖顺治皇帝福临的生母。在长达六十余年的宫廷生活中,她历经三朝,辅立了顺治、康熙两个幼帝,她始终运筹后宫而未临朝擅政,审时度势而不固执旧制,为女真这个人数很少的民族“入主中原”做出了鲜为人知的贡献。老作家颜廷瑞执迷于这个人物和大清王朝发达的历史,以孝庄皇太后为轴心,展开了横纵舒卷的历史风云,其当代的启示意义是相当深刻的。
政治的拼搏,权力的角斗,王朝的更迭,战争的胜负,是《孝庄皇太后》描绘的中心。其中所有人物的登台与下场,出现与消亡,莫不与此有密切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孝庄皇太后的命运便是清王朝的命运,反之亦然。这部挥洒之间百万言的小说,并不是一部完整的传记性作品,它只截取皇太极突然驾崩到多尔衮于顺治七年死于狩猎的喀喇城这一段时间,前后约八年。第一卷《血泪清宁宫》以皇位的争夺为中心线索,以福临继位,吹响了“入主中原”的号角;第二卷《风云山海关》,从清朝发动“宁远战役”,到百万满洲人迁移北京,展示了清王朝与明王朝、与李自成的大顺王朝之间的激烈而又错综复杂的军事的、政治的斗争;第三卷《悲欢紫禁城》描写了随着大清政权的稳固而展开的内部权力斗争,最终导致“太后下嫁”这一复杂的婚姻事实。由于作者始终把孝庄皇太后作为其小说描写的中心,所有的复杂斗争,所有的人物命运都和她的思想情感联系到一起,显得脉络分明,清晰可鉴。
在近年来关于历史题材的创作评论中,“用灵性激活历史”这一提法颇受人称道。其实,在所谓“灵性”中,除了艺术的想象力,对于历史的识见是其主要的内涵。如果没有对明末清初中国各民族政治军事态势的清醒而又独到的见解,如果没有对清王朝内部文化和政治系统的独到的考察了解,那么,关于孝庄皇太后及其时代的描写将难以被赋予蓬勃的生命活力。我认为,在《孝庄皇太后》这部处处闪烁着真知灼见的历史小说中,至少有三点是十分独到的。一是对于满族“入主中原”的看法。满族是一个不足百万人的少数民族,历来被归于“夷狄”、“鞑子”一类,出于封建统治阶级长期的偏见,把他们的入侵,视为蛮族对文明礼仪之邦的践踏,以至于孙中山先生在革命之初,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作为唤起民众的口号。应该说,作为中华民族成员之一的任何一个少数民族都具有平等竞争的机会。尤其在汉民族的中央统治集团已经腐败到极点的情况之下,被强悍的、充满活力的少数民族的统治所替代,除了咎由自取之外,还有什么话可说?!至于清王朝进关之后的统治是更落后愚昧还是更开明,至于其统治阶级日益被腐朽的汉文化所同化,最终丧失了开拓的活力,导致了近代史上的大屈辱,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可以肯定,即便是李自成的大顺朝得以成功,或者是太平天国、捻军、义和拳之类政治势力建立统治,也难免近代史的悲剧。第二点,作者对满族开创基业时的创造精神、开拓精神、气度和胸怀显然是持一种十分赞赏的态度的。一个人数不足中原十分之一之数、崛起于白山黑水的村莽之间的弱小民族,竟能在短短的时间里,励精图治,奋发图强,成为上亿人的辽阔疆土的统治者,这本身便是一首壮丽的史诗。孝庄皇太后在这个事业的起点上,显然起着一种积极的凝聚作用。在皇太极突然驾崩,清朝贵族内部面临一场争夺皇位的内讧、互相残杀的危机时刻,是孝庄皇太后为了全民族的大局利益,斡旋于王公贵族、各派政治力量之间,并以科尔沁草原上其父兄所统辖的精锐铁骑为筹码,成功地化干戈为玉帛,推出福临为帝,协调各实力派贝勒、亲王的关系,明确地高举起“入主中原”的旗帜,使清朝从东北进攻中原形成了新的更强大的合力。即便抛开汉民族和满民族的狭窄的功利心理,孝庄皇太后难道不是一位顾全大局、维护大局、推动大局的女杰吗?第三点,关于清入关成功的原因和满汉关系的处理,《孝庄皇太后》的描写体现了一种恢弘的历史眼光和气度。吴三桂显然是常被人唾弃的“引狼入室”的“汉奸”一类的人物,但在《孝庄皇太后》中,吴三桂的首鼠两端,翻云覆雨,除了性格上的原因之外,更有着客观形势上的制约因素。就拉拢吴三桂手段来说,穷途末路的崇祯皇帝也远远不及清王朝的多尔衮、孝庄皇太后们来得大方和长远,至于李自成的大顺朝则更显得目光短浅。显然,即便没有吴三桂,大清的“入主中原”也是定局之势,历史的必然已无可更改。初入京,多尔衮为崇祯皇帝按明朝的礼制、皇帝的规格发表,各级汉官各安其位,官晋一级,这两招,便足以看出这个民族的胸襟、手段至少是大于、高于进城之后便忙着追索珠宝赃物的李自成们的。在满汉关系上,孝庄皇太后一方面不拘于“不蓄汉女”的祖制,大胆地在自己身边使用婉儿等贴身侍女;另一方面,则鼓励“以汉制汉”的总策略的施行,她不仅力主重用范文程、宁完我等早期来归、有真才实学的汉人,而且重用投降的明朝重臣如洪承畴、祖大寿、吴三桂等。可以说,清朝高于元朝的地方正在于“以汉制汉”的正确方针的确立和施行,这保证了他们夺取全国的统治权并获得了长达三百年的统治,此举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汉民族自身的软弱和可悲。
一部历史小说的成功,必须借助于其内在的精神气韵和当代精神的契合、融汇。三百年前一个弱小民族的强盛之路无疑具有巨大的现实启示性。而历史的回顾和描绘,如果失去其当代启示性,那么便会变成一堆毫无意义的故纸堆。一位著名的西方历史学家沃尔什说过:“历史之光并不投射在‘客观的’事件上,而是投射在写历史的人身上,历史照亮的不是过去,而是现在。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何每一代人都觉得有必要重写他们的历史的缘故。”(《人心中的历史》第177页)对于文学家、小说家来说,历史是有灵魂和血肉的,而只有在深厚的当代精神的感召之下,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那丰富而搏动着的活的灵魂。当然,这里说的和“四人帮”所说的“古为今用”、“借古讽今”,乃至阴谋文艺风马牛不相及。每一个民族都不能割断自己的历史,不论这历史是光荣还是屈辱,历史都是一面镜子,照出过去,辉映未来。过去呈现出一种规律、有序和必然,而未来却是莫测、无序和偶然,谁能真正准确地预测未来的历史呢?正如谁也无法全盘复制历史一样。正因为历史无论之于过去和未来的终极奥秘是无法企及的,所以永远会有史学家和以描绘历史为己任的文学家存在。然而,要探寻历史的奥秘一方面是熟悉过去,另一方面则是洞察今天。历史小说之所以有其存在的价值,正在于过去可以为镜,今天可以为戒;过去可供思考,今天可以图强。如果一部历史小说没有对于今天的思想冲击力,那么纵然是学富五车的博学者,其作品仍无法唤起今天读者的共鸣。新鲜的史料可以使作品轰动一时,唯有深刻独到的见解才能使后人永远地咀嚼回味,从而保留下一段特定历史时期的关于某段历史及其人物的最有代表性的见解和描述。人们不是常常钦羡文学的“永恒价值”吗?那么,历史小说的“永恒价值”便在这每一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当代意识”之中。
从《孝庄皇太后》中不难听到这样的内在的声音: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没有内部的纷争和矛盾,但是为了民族的整体利益,绝对需要克制乃至牺牲局部、小集团、个人的利益。而孝庄皇太后在平息皇太极死后的争帝位危机的时候,所使用的正是这个思想武器。每个民族都必须产生自己的英雄人物,为了民族的大功利,有时必须容忍他的某些缺点和错误。多尔衮是小说着力描写的主要人物。对于清王朝来说,他是真正的开国元勋,未称帝的帝王,尽管他也专横,也残忍,也好色,也贪婪,但是他在关键时刻,后退一步,避免了自相残杀,他有一万条错误,但开国之功足以弥其过。尽管他死后尸骨未寒便受到清算,“诏削爵,撤庙享……黜宗宝,籍财产……”甚至坟墓掘毁,破棺鞭尸。他的罪过正在于他生前功高势盛。小说在结尾处以孝庄皇太后的清醒话语,表明了对待历史人物功过是非应有的理智和客观的态度。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永恒的开拓精神才是其活力的源泉。尽管清王朝后期腐败,但其前期和中期的疆土开拓为中华民族带来了多大的利益!至今我们仍享用着。试想,如果明朝苟延残喘到一八四〇年,其已经萎缩到三百余万平方公里的疆域大概要丧失殆尽,站在中国历史的高峰回眸鸟瞰,清王朝较之明王朝给中国带来了更大的完整和统一,这未尝不是汉民族的幸运。
《孝庄皇太后》在政治斗争描绘上无疑是成功的,小说不仅描写重大政治决策会议的剑拔弩张,也描写了幕后政治活动的细微的风吹草动;既有实权派的满族王公贝勒们的飞扬跋扈,也有汉族降臣们小心翼翼的察言观色;有宫廷之上的唇枪舌剑,也有宫帷之内的出谋划策;有围猎场上的喜怒哀乐,也有酒席筵中的荣辱悲欢……其间,关于满族生活的许多风俗描写是相当引人入胜的。这多少得力于作家长期住在盛京(沈阳)的天时、地利,当然更有赖于作家对满族典籍和人民生活的深入研究和体验。
如果说上述有关政治、风俗的描写来自作家的精深研究和调查,那么关于数百年前的战争战场的描绘则更要仰仗于作家军人的职业生涯和直觉。他固然可以到宁远、锦州、山海关的古战场去凭吊流连,但是古代的冷兵器为主的战争毕竟和现代战争是另一码事情。大战宁远城的“宁远战役”和吴三桂、李自成、多尔衮这三支军队的山海关、一片石之战可谓惊心动魄。李自成的农民军虽然横扫大半个中国如秋风卷落叶,对付吴三桂的明军也还可以打个平手,但对陌生的八旗铁骑却既无心理上的准备,更无战略战术上的准备,其强弩之末之势已经十分明显。一片石之战使大顺军一蹶不振,兵败如山倒,李自成也仓皇离京而去,已成燎原之势摧垮了大明王朝的农民起义军终于败在了更强悍的满汉八旗军手下。小说中描写了将帅们的运筹帷幄,也细致描写了攻城、防御、突袭、智取等不同的战法。对于吴三桂作为狡猾的军事将领的描写,也是入木三分,颇为可信的。
显然,战争的描写并非本书的用力之所在,作为长期从事戏剧创作、年逾五十之后才进入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的颜廷瑞来说,他更习惯于那种莎士比亚式的冲突性情节构置和大段的抒情性的心理独白式的描述,这使他的小说十分显著地区别于许多当代其他的长篇历史小说,显得很有气势,引人入胜。孝庄皇太后的心理流程是很鲜明突出的,其他主要人物如多尔衮、济尔哈朗、代善、豪格、多铎、阿济格、阿巴泰、索尼、范文程、宁完我、洪承畴、崇祯、李自成、刘宗敏、吴三桂等,也都是性格鲜明、栩栩如生的。
也许作家对孝庄皇太后过于偏爱,也许作家做“翻案文章”的急切心情所致,孝庄皇太后在他的笔下是显得过于完美了。对她不可避免的文化视野及阶级属性上的局限性缺乏应有的揭示,作为一个被高度净化和纯化了的形象,其内心深处的自私乃至阴冷狠毒的一面亦缺少相应的描写。相反,对雄才大略、英年早逝的多尔衮却过多地展示了他野心家、阴谋家的一面,而对于他的积极贡献也多从谋略角度加以渲染,多少令人感到失之公允。当然,话又说回来,如果作家没有对其主人公强烈的爱憎情绪,恐怕也就没有《孝庄皇太后》这部力作的问世,这大概也如历史本身一样:进步、前进总要付出些许的代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