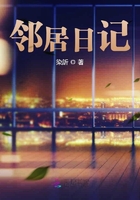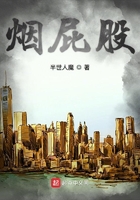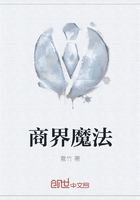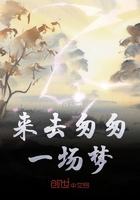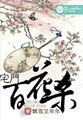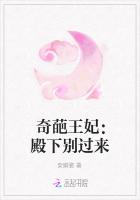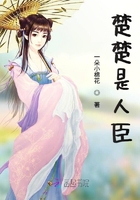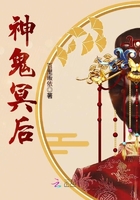我的父母是河北人,七几年时因为吃不上饭,于结婚第二个月背着一床铺盖,带着二十几块钱来到了内蒙古。
那时的内蒙古人少地多,只要有把子力气,就不愁没有饭吃。
我的三姑,季红,早几年就嫁了过来,我父母很自然的就投奔到了她门下。
后来听母亲说,三姑那年刚刚二十出头,身材略丰,皮肤白净,相貌很清秀。
那时的她正怀着第二胎,头一个孩子已经七岁了,是个男孩,他就是我的表哥,石军。
三姑父家有四十亩地,我父母去了就充作了他家的长工。
父亲二十九岁时才娶到了母亲,他在家里排行老二,老大早年间去打仗就再也没回来,上面有两个姐姐,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至于爷爷奶奶,在我的认知里他们似乎从来都没有出现过。
只是偶尔从父母的谈话中我才知道,爷爷早逝,奶奶没几年也跟着去了。
父亲十七八岁时就是季家当家做主的人,加上上面两个姐姐的照拂,总算是给两个弟弟娶上了媳妇。
而他,已经二十七了,那时的河北时兴早娶早嫁,像我父亲这样的就属于大龄青年了,而他本人也做好了要打一辈子光棍的打算。
他和母亲之间是我三姑父拉的媒人线。
我的母亲,个子不高,做事爽利,言语上也很是泼辣。
她和我三姑父是一个村的,经我三姑父介绍嫁给了我的父亲。
我父亲年轻时也算是相貌堂堂了,只因为年龄大了还没找到媳妇儿,也就同意了。
两人举行了简单的婚礼,父亲买了辆自行车,一台缝纫机,把家里的两间土房拾掇拾掇就当新房了。
至于我姥姥给母亲陪送了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说道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母亲的家世了。
那时,姥爷是个不大不小的地主,家里有存粮,窖里有黄金,外面还养着小老婆。
姥姥生了四个孩子,我大姨,二舅,三舅,和我母亲。
我三舅和我母亲是龙凤胎,如果放到现在,也算是很让人羡慕了,一胎就有儿有女了。
可当时,生龙凤胎缺不是什么好事,农村人都说,龙凤胎是童男童女转世,是要被献祭的,养不活。所以,我母亲对于她和三舅是龙凤胎的事一直讳莫如深。
姥姥年轻时一手把四个孩子拉扯大,姥爷则在外面茶楼上搂着小老婆喝酒。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母亲同父亲说起来的一件关于姥姥的事。
以前的农村都有赶集唱戏的习俗。那时我大姨大概六七岁,二舅也只有三四岁,我姥姥架不住大姨的闹腾,带着她和二舅去看戏。
戏散后,已经是暮色四合了,两个孩子都睡着了,姥姥一个小脚女人哪里能把两人孩子弄回去,她在戏台下可以远远看到在楼上喝花酒的姥爷,那晚,娘仨在戏台下佝偻着挨到天明,楼上的莺歌燕舞也一夜未歇。
后来,姥爷被扣上了地主的帽子,关牛棚,游街,家产也充了公。
没几年,他就瘫在了床上,一瘫就是十几年。
我对他唯一的记忆也留在了那间昏暗的小屋里了。
屋子里光线很暗,母亲和父亲都在,姥姥给他喂饺子,他支愣着头嘴中发出“啊,啊,啊”的叫声,浮肿的眼睛直直的看着我,意思是要先给我吃。
那一刻,我看到了姥姥转过身子用围裙试泪。
再后来没几年他终于是去了,母亲也松了一口气,家里有病人的都能理解那种心情。
我不知道姥姥是怀着怎样的心情伺候了他十几年,年轻时也许是恨的,后来也许是同情多一点吧,因为到了,在床前伺候他的也只有姥姥,他的那些小老婆都作鸟兽散了。
在母亲怀上我的时候,我们举家搬到了内蒙古一个靠近黄河的村子。
本地人管这些村子叫兵团,因为这里面住的多半是北京的下乡知青。
三姑父为人懒散,自从我父母住进来后,家里地里的事他就再没操过一点心,平时他就在村里来回晃悠,招猫逗狗的和个没长大的孩子一样。
村子不大,满打满算也只有七十户人家,村里有个小学,只有一到三年级,学生加起来也不到二十个。
表哥石军刚刚上一年级,是个非常淘气的孩子,每天放学母亲都要撤着嗓子满村子喊他回家吃饭。
夏天麦收时,表哥常常和一帮子男孩子去河里游泳。
那天河叫嘎毛河,不宽却足有六七米深,河上有一座拱桥离河面大约有五米高。
表哥喜欢站在桥上往水里跳,其他孩子则在旁边拍手叫好。
我想,那时的表哥一定觉得自己很牛吧。
村里有人看到,把这事儿告诉了我父亲,
父亲的脾气格外的直,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表哥拖回家揍了一顿。
三姑父因为这事儿和他大吵了一架。
当晚,三姑就发动了,晚饭时她吃了两碗面,还劝解三姑父说:
“季风也是好意,你瞅瞅军儿都淘成什么样子了,”
她抚上自己的肚子,
“希望这胎是个女儿吧。”
村里会接生的姓阴,她还是村里学校的老师,知青反乡时她没走,大家都叫她阴老师。
阴老师来时只看了三姑一眼,就沉着脸说道:“血崩!”
那时的医疗条件有限,生孩子死人更是常常发生的事,村里人在门前点燃一堆堆麦秸,送走了三姑。
我的表姐,石丽,在她母亲的忌日里出生了。
母亲用米糊,羊奶,将她养活了。
三姑父沉寂了一年,然后开始张罗着给自己再娶一个。
没多久,他就和隔壁的一个寡妇有了些什么,寡妇闲三姑父家里人太多,我的父母很是利落的就被赶了出来。
表哥开始每天去寡妇家吃饭,表姐被送到了河北老家一个远房嫂子的家中寄养。
村长见父母没地方住,就给拨了一间四面透风的库房住,村里人这个给借一口锅,那个给借一双筷子,一个老乡给了半袋子白面,这个库房就是我的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