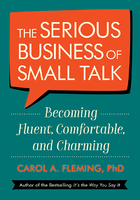清晨时分,弥漫而起的雾气笼罩了许州城,明媚的春光从东方缓缓升腾而起,喷薄出壮丽的霞光。
陈临今日起的很早。所谓一日之计在于晨,虽然脱离了学生的身份许多年,但他并没有忘记清晨是人一天中记忆力最佳的时刻。趁着早起阳光真好,微风不燥,他将论语通读数遍,力求先记住全文内容,至于含义的领会,等到了书院再向老师们请教。另外这幅身体长年体弱,虽然他已经向陈府管家跛三交代了准备些沙袋、单双杠之类的锻炼器械,但考虑到这年头没人见过,找木匠定做也需要一些时日,所以在短期内,他能想到的锻炼方式也只剩下跑步这一条,毕竟无论如何也该彻底的锻炼一番,万一以后真遇到紧急情况,起码逃命比别人跑得快也好。
在这一方面陈石与陈临的想法不谋而合,他同样的一大早起的床,拎着一根两米多长的木棍在当进门的前院里舞的虎虎生风,几个做完了差事的仆役在旁围观,不时还传出一阵叫好助威声。陈临也在旁看了两眼,这家伙的棍法打的确定不错,招招凶狠却不致命,专攻对方皮糙肉厚的部位,一看就是街头打斗出身。
“哥,你要出门吗?一起啊。”
陈临并没有拒绝他的请求,制止陈石要用凉水洗脸的行为后,向他扔了条干净毛巾:“刚出了汗先别碰凉水,这样对身体不好,容易感冒着凉。”陈石不以为然,却也不会在这种事上拂了他的好意,胡乱在脖颈脸颊上抹了几下就匆匆拉着他出了门。
已过立夏的许州仍旧焕发着活力,沿着青石铺就的街道一路前行,道路两旁砖木结构的古朴建筑形态不一,各种各样的树木,推着小车的早起摊贩,偶尔能看到一些衣衫不整的人,红着眼满脸疲倦的坐在早餐摊前,直到一碗热腾腾的米粥下肚,这才焕发起精神,往桌上丢下几枚铜钱急匆匆的离去。
转过几个弯,一群脸上画满油彩的人引起了陈临的注意,走过去问了才得知,原来今天是李员外要纳第十三房小妾的日子,这些人都是被请过来到李家表演戏法的。幸福往往来自于某些不幸,但对于某些人来说,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当他同陈石谈到李员外新纳的小妾的年纪时,陈石的看法却出乎他的意料——娶妻娶贤,纳妾纳色。无论如何,十一岁的小妾也太小了些,平板板的生不了也乳不了孩子,也就是李员外心善,愿意领回家多浪费两年粮食,如果是他绝对不会娶回家……
真XX人渣。
其实陈石的话放到当下也是无可厚非,因为他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着大部分北宋土著人的观念,更何况重男轻女的思想本就是古代最为人诟病的一点——?困兽犹斗、破釜沉舟……无论是何种语言,所言出的话术永远为目的而服务。上位者的行为无论正确与否,言出法随,总归会被人将其解释正确。就好似喊出了‘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的刘玄德,依然还是那个后世人眼中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的伟大的汉昭烈帝。
说到底,华夏传统的儒学思想与西方哲学理论,抛去表面的那层外衣,其核心的内容终归还是在总结人生道理,或许所采用的表达方式不同,但条条道路通罗马,殊途同归的结果还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东西。
开门营业的店铺越来越多,酣睡一夜的乞丐们也钻出巷子,敲着叮当响的破碗向路人讨要钱粮。不论世道如何,对于活着的人来说,怎样填饱肚子才是最重要的,许州城比不了富庶的江南,但这里的生活更加安逸,总归来说容易满足的人到哪里都容易获得快乐。
陈石在吃过包子后也与他分手了,虽说几家铺子都有掌柜,但陈临要上学,母亲又年纪大了,出门不方便,自然而然各间铺子巡视的工作就落到了他的身上。
陈临倒是很闲,青丘学院虽放课晚,但早上的开课都差不多到九点多快十点了。不过这年头没消遣,大早上茶肆里说书的人还没来,清楼听曲……这个时间点会去的,除了色鬼外就只剩下官差。
其实对于陈母所说的出人头地,陈临并不算特别感兴趣,虽说当了官确实可以出人头地,但堂堂北宋王朝也不剩下多少时间,更何况即便是寒窗苦读也要几年,到时好不容易中了举,还要在别人眼皮子底下培植一帮势力,想想都觉得麻烦。更何况万一手下再出几个誓死保家国的二货,那可真是想走都走不了。
至于说搞什么一鸣惊人,帮助北宋度过难关打败金辽,陈临觉得这任务一定是地狱级难度。先不说当今的皇帝是个扶不起阿斗,即便是他真的说服了皇帝,可眼下朝廷里那帮奸诈如狐的文官又有哪个肯信他,难不成要告诉那些人‘你们的皇帝,连同他的老婆孩子在未来的某一天都会被金人抓走?’,那样说怕是他第一个就被砍了脑袋——无论如何他也不会拿性命去冒这个险,想想都觉得太傻了。
晨风微凉,他坐在岸边的石头阶梯上,一边捡着石子扔向水里,一边在脑子里想着这些。
其实根本没办法,不管采用何种方式,对如今的他来说,都将会有被杀头,甚至是被灭门的风险。
商贾之子是硬伤,往前推两百年他甚至连出仕的资格都没有。至于研发qiang炮学着西方搞一个工业革命,顺便造个反取代宋朝……
emmmmmmmmm……
太累了,而且完全get√不到当皇帝的好处在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