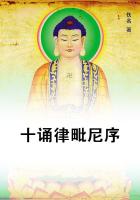大姨出殡后的第二天,我和我妈还有三个舅舅表兄他们吃完了午饭就赶路回家,我的二姨还有舅妈在大姨父家帮忙。大舅让我们在他家住个一天两天再回,我妈说建芬一个人在家,她不放心。于是大舅想了想,埋怨我妈没有带建芬一起来,也同意我们回家。舅舅他们还打算用自行车给我我们送一程,我妈对三个舅舅说:“你们看,我的儿子建业已经长大了,他昨天一路走来,没有喊一声累。”
三个舅舅听到了,都高兴的笑了,说:“建业这孩子确实长大了,比上次来的时候都高出一个脑袋了。”我听了,在一旁嘿嘿的傻笑。
妈妈问我:“建业,告诉你三个舅舅还有五个表兄,你现在还能一路走回家不喊疼吗?”
我说:“妈,我,我不累,也不疼。”
三舅说:“男孩子嘛,本来就要顶天立地,你爸没在家,你妈妈一个人有时候照顾不周全,你和你姐姐可要互相帮助,不要在外面惹是生非,不要和别人吵嘴打架,在家可要听妈妈的话,知道没有?”
三舅说这话的时候,表情非常的严厉,一种不得反驳的语气。我回答说:“舅舅,我知道了。”
当我和三个舅舅在他们村和沥青路的交叉口分别时,舅舅让两个表兄帮我妈挑着扁担和篮子一直送到了路廊。我妈妈一再让他们回家。最后,在那个路廊才挥手告别。
当我和我的妈妈回到家里时,已是下午四点,虽然和我的妈妈舅舅说不累不疼,那是我在撒谎,我不想让他们在这个时候,引起他们担心。我的双脚都冒水泡了,走起路来,都不敢太用力。而我妈妈的双脚大概也磨出了水泡,她挑着那个篮子,虽然不是很重,但是那么多的路下来,也是非常的不容易。
两个鸡笼里面的公鸡母鸡从鸡笼的方孔里面钻了出来,脑袋一晃一晃的,用一种非常好奇的眼神打量着我们。我妈把那些鸡从鸡笼里面放了出来,然后在地上洒了两堆谷子,那些鸡就像是饿了三天三夜一样,一个个围着两堆谷形成了一个大圆圈,那四只公鸡仗着自己鸡高马大,不时地去赶那些母鸡。那只高大一点的公鸡威风凛凛地站在谷堆旁,像占山为王的强盗一样,捍卫自己的粮食。我看不惯它那种架势,右脚狠狠地踢它,它还是比较给我面子,退了三步,进了两步。
我那踢出的右脚太过用力,大腿抽筋了,我坐在凳子上,愤愤地说:“你小子给我等着瞧,等下我拍你巴掌。
我妈看到了,说:“你这是在干嘛,打这么重,会把它给打死的。”
我感觉揍得差不多了,往鸡笼里面使劲一扔,然后把上面的出口用砖头给盖上了。
半个月后,我的外公也走了,在我的印象里,我只记得一次和外公有比较亲密的接触,就是那次在那棵非常高大的乔木下做礼拜遇到的那次,还记得当时他给了我一块钱,让我去买瓜籽吃。当他把钱递给我时,旁边的大爷问他:“这是你的什么人?”当他们得知我是他的外孙时,他们感到非常的惊讶。
那时,我的外公已经很老了,已经差不多七十多岁,,和我相差了整整六十多岁。而我的外婆在我妈出嫁前就已过世。所以,每当我听到《外婆的澎湖湾》这首歌时,我就非常的向往我的外婆家,我非常想看一看我外婆的模样,想看一看我外婆家的前后左右有没有像澎湖湾一样美丽的景色。
后来,终于有一次,我来到了我的外公的家里,他家四周的景色果然没有让我失望。外公家也是两层木瓦房,楼上那层不是很高,是用来当卧室的,一排有六间。他家的前面种着一堆竹子,竹子那修长的竹竿,绿油油的竹叶随风飘动,发出嘶嘶——的响声。外公是在那一排六间中最靠西的那间,在外公的西侧,种着一堆生机勃勃的芦苇。而在芦苇和竹子的外面就是一条弯折的小河,那个小河不是很宽,大概七八米的样子,小河上面有一座石桥,河水不是很深,但是碧绿碧绿的,在河的对岸就是我二舅的家。
我外公的死,其实早在我妈和三个舅舅他们的意料之中,因为他的身体一直很差,现在他的大女儿也先离他而去,不免更加的伤感。外公生前本来是信基督教,还时常会去教堂。但是我那三个舅舅信的是佛教。最后,那丧事就被办成了佛教的那个样子。
当我舅舅那边来人报信外公的死讯时,我的妈妈比上次大姨死时哭的更为伤心。那个出殡的早上,我妈带着我和我姐,让我和我姐扛着那个扁担篮子,一直从家里哀嚎着走出狮盘村,狮盘村那些好心的阿婆也被感动的落下眼泪来,安慰她说:“不要哭,不要哭,人老了,总是会死的,你要看看你那两个孩子,你这样子会吓住他们的。”
当我们走出狮盘村时,我妈也停止了哀嚎,她的嗓音已经嘶哑,说话时的声音完全变了,她用那嘶哑的嗓音对我们说:“建芬建业呀,妈没事,妈好着呢,这可是我们这里的习俗,爸死了,嫁出去的女儿就得从家里哭着走出自己的村庄,然后还要哭着走回自己的村庄。”
我妈这句话的意思有两层的含义。第一是安慰我们,第二是在委婉地告诉我们,他给外公送丧回家,还得哭着从村庄入口回到家里,在让我们提前做好心理准备。
我们一家三口,像以前几次一样,走在那条充满回忆,充满感情,充满酸甜苦辣的那条道路上,那条路线已经牢牢地刻进了我们记忆深处。那棵高大的乔木和那个长长的路廊已经成了我们记忆中的路标。后来我长大后,我再次沿着那条道路,去寻找乡愁时,我发现,那条在宽阔的菜花地中间的那条泥路已经被杂草覆盖,那棵高大的乔木也被台风刮折了腰,从乔木到路廊那段路已经变得荒芜,中间的石桥也断了。有一条新修的水泥路可以直达我舅家前面的沥青路。只是失去了儿时的那种味道。
我外公出殡时,作为外公最小的外孙女,她要给他挑灯笼,而我作为最小的外孙要给他捧遗像。我就跟随着他们把我的外公家周边又转了一遍。那周边方圆十公里就是我外公我舅舅生长的地方,是我妈小时候生长的地方,让我充满了好奇,我很想知道他们和这块土地上的人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可是,那也只能自己去想象了。
外公去世的那个晚上,在他家的前面摆放了三个晚上的电影,还有很多的和尚给他做法事超度。不知我的外公生前有知,会有怎样的想法。
这次,我们在我大舅家住了两个晚上,那个傍晚,当我们从狮盘村入口处快要走到家里时,我姐提醒妈说:“妈,你忘记嚎哭了,你说过要从村口哭嚎着回到家里,好让村里人都知道你悲痛欲绝,你还说这是我们这一带的习俗,你可不能破了我们这一带的习俗啊。”
我妈抬头看了看,又转回头看了看,这时天色已黑,我妈就开始像去的那个时候一样,哭嚎了起来,声音都是一抽一抽的,让我们不忍听之。我狠狠地瞪了我姐一眼,姐也觉得是自己多嘴,不该多说话,她默默地垂下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