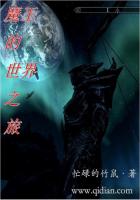文/杨黎光
父亲去了,却把手的感觉永远留给了我。
“听风听雨过清明”。今年清明前夕又是一个“雨纷纷,风萧萧”的季节。
这天夜里,风雨声中我似睡似醒。忽然门开了,父亲径直走到床前,轻轻地握着我的手。这只手粗糙温暖,中指少了一截。
我惊醒:父亲已经去世多年了打开灯,房间里只有我一个孤独的身影。床头的挂历告诉我:又是清明。
如水般的思乡之情从心底涌出——归心似箭。
父亲埋在故乡安庆的墓地里,远在深圳的我却常有一种握着父亲手的感觉。
记得两年前那个大雨滂沱之夜,折磨了父亲几十年的高血压,终于顶破了他脆硬的脑血管。他倒下了,再也没有站起来。那夜,老天像决了口的天河,大雨滔滔不绝,以致无法将父亲的遗体从急救室送往太平间。
子夜时分,除了风声就是雨声。家人们都去张罗丧事了,我陪在他的身边。我无法相信这是事实,又像往常一样握着他的手。父亲的手骨节很大,像一段一段粗糙的竹根。右手的中指断了一节。
那是在父亲退休前夕,一次工伤绞断了他的一节中指。我赶去医院看他。为了怕儿女们揪心,父亲竟装得若无其事,我却在他换药时,看见了白花花的骨头。这只劳动了一辈子,养育了我们三个儿女,供养我读完大学的手,却在他晚年即将退休时,伤残了。我握着这只断指,第一次在父亲面前落泪了。从那天起,我猛然感悟到做儿子的责任和义务。
父亲感情细腻却寡言,直到临死也没有留下一句遗言。我因当记者搞创作,整天东奔西走,回家看他的时候很少。他病中格外想我,每当我回家,他的病就好了一半,躺在床上望着我,满面的笑容却仍然很少说话。我只好默默地握着他的手,抚摸着那只断指。父亲的手虽粗糙却温暖。父子之间的情感,全在这轻轻一握之中。父亲病危送医院后,一直处在昏迷之中,抢救中他显得躁动不安,只要我握着他的手,他就会平静下来。
父亲的晚年,我的女儿是他的心肝宝贝。父亲对孙女的爱也是无言的,只是常将孙女稚嫩的手握在他那粗大的手中。每当这时,平时好动的孩子就变得十分安静。父亲一下一下轻拍着孙女的手,把一个垂暮老人的慈爱,无言地送进了一个懵懂无知的童心里。
父亲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他生前从未教诲儿女们怎样做人,却以他忠厚善良的一生让儿女们懂得“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父亲要去另一个世界了。作为他唯一的儿子,我知道晚年的他把每次看到我和孙女,当做生命的节日,而我却没有满足老人这唯一的愿望。直到他去世了,我才感到揪心的内疚。我握着他的手为他送行。就在这时,好像在回答我似的,心跳已经停止的父亲似乎轻轻回握了我一下,我感到无比的满足,然后,这只手在我的手心里变凉变硬……我知道,父亲去远行,他在和儿子做着最后的诀别。他告诉我,上路时不孤独。
父亲去了,却把手的感觉永远留给了我。我觉得,母亲的爱,像唠唠叨叨的小溪流过心田;父亲的爱,像辽阔的海洋深而无言,父爱更博大。
离开故乡回深圳的头一天,淅淅沥沥下了多日的雨突然停了,久违的太阳也露了脸。赶紧,一大早我和母亲、妻子、女儿去为父亲扫墓。“春日迟迟,卉木萋萋”,墓地十分宁静,母亲在坟前烧起一堆纸钱,我明明知道这不过是活人的一种“自我安慰”,可却感到父亲来到了我的身边,轻轻地握着我的手。女儿悄悄地在坟前放下一个塑料小盒,然后就满山去采野花献给她的爷爷。我好奇地打开她的小盒,里面是一小片纸,一行工工整整的稚嫩小字:爷爷,我永远爱您。我的视野湿润了。
突然,女儿抱着一束采来的野花叫我:“爸爸,你看——”
我回头,看到一幅壮丽的景观:漫山遍野走来许许多多的扫墓人。呵,又是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