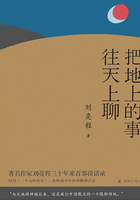一
那是一个有些闷热到令人昏昏欲睡的夏天的午后,我接到了老朋友佐藤从日本打来的越洋电话。
“摩西摩西,想请你帮个忙。”他的声音混在嘈杂的背景音当中,“帮我找一个叫作佐伊的女孩子。”
“谁?说清楚点。”我当他又看上了哪个中国女孩。
“一个叫作佐伊的孩子,大概十五岁,三米高,六吨重。”
“别逗我了,”我笑出了声,“这哪是孩子,明明就是大象。”
“对啊,佐伊,它是一头母象,”他一本正经地回答,“我刚才没有说吗?”
二
寻找大象,这大概是我这辈子接受过的最为离奇的委托了。但佐藤却坚称这份工作非常重要。“事关人命”,这是他的原话。
靠着佐藤那模糊暧昧的言语和支离破碎的描述,我还真的在本市的动物园里,找到了一头名叫佐伊的非洲象。它是我见过的最忧郁的大象,总是独自伏在象山下的一片阴影里,不出声、不走动,也不和其他大象玩耍嬉闹。
“佐伊是八年前捐赠到中国的,捐赠人的名字叫作高桥英之。那个时候它虽然还小,但却已经训练有素。”
“为什么会叫它佐伊?”我问饲养员。
“你看它的耳朵。”依着饲养员手指的方向,我看到大象的耳朵上,有着什么在闪闪发亮。
“它被送到我们动物园的时候,耳朵上就带着那个耳环,内侧还刻着‘Z-O-E’三个字母。我们曾经尝试过给它改名,但它从来只回应佐伊这个名字。不信你试试。”
“佐伊。”于是,我和一群春游的孩子一起,隔着护栏喊着它的名字。
它果然微微地抬了抬头,瞥了一眼人群,接着又很快低下头去。但就在它抬头的那一瞬间,我看到了它奇怪的一面。和其他大象不同,它没有象牙。
饲养员说,这应该是盗猎者干的好事。但奇怪的是,被割掉象牙的大象往往会因此丧命,佐伊却幸运地活了下来,就连饲养员也觉得不可思议。
我将找到佐伊的消息告诉佐藤,在电话那头,他非常高兴地说:“太棒啦,这下我可以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佐伊女士了。”
“等等。”我打断他的话,“佐伊不是你让我找的那头大象吗,怎么又成了人?”
“因为拜托我寻找大象佐伊的女士,她本人的名字也叫作佐伊。这其中的故事有些复杂,就连我也没有听过完整版本,等过几天,佐伊女士要亲自去中国看大象佐伊,到时候,请她自己和你讲吧。”
三
趁着我还没有被佐藤给绕晕,我终于在机场里接到了从日本赶来的他,和另外两个我从未见过的日本女人。其中一个年轻漂亮,另外一个年长而羸弱,坐在轮椅上,不能自己行走。两个女人的眉眼颇为相似。佐藤告诉我,年轻的那个是他刚刚交往半年的女朋友,而年长的那个,则是女友的母亲。
“你好,我是高桥麻美。请多多关照。”年轻女人颇为礼貌地向我鞠躬问候。
“你就是佐伊女士吗?”我问。
“不,佐伊是我母亲的英文名字。”她轻轻抬手,为母亲掖了掖身上的披肩。
“下午好,我叫高桥美智子,你也可以叫我佐伊。”坐在轮椅上的女士,声音有些有气无力,“谢谢你帮我找到佐伊,现在我们能去动物园看看它吗?”
在驾车前往动物园的路上,我听到了这位又名佐伊的高桥太太讲述的,关于佐伊的故事。
“我的先生是在非洲工作的动物学家,而我,在女儿出生之后,就把她留在日本,一个人来到非洲,陪他一起工作和生活。”
“你的先生,是不是叫高桥英之?”不知怎么的,我的脑海里突然冒出这样一个名字。
“是的,是的。”高桥太太看我的目光有些惊讶,但那点惊讶很快又被一层温柔覆盖,“佐伊就是我用他的名义捐走的。也算是对故人的纪念吧。”
“故人?”
高桥太太说:“他是九年前走的,在一次驱赶偷盗者的时候,中了流弹,打中了大动脉,失血过多走的。”
“我很抱歉。”我低下头。
“这并不算一个意外的结局,他本来就是一个野生动物保护主义者,常常在各种危险的场合和那些盗猎者周旋。危险,是必然的。我们没有把女儿带到非洲,也是因为那里的环境太过辛苦和危险。”
“那佐伊,也是你们……”看到她抬起头,我补充了一句,“我是说那头大象。”
高桥太太轻轻点了点头。她告诉我,佐伊的身世很可怜,当她和丈夫在丛林里发现它的时候,它还不满一岁,倒在血泊里呜咽。在它象牙的位置有着两个明显的伤口,往外汩汩冒血。它的一侧耳朵上有一个弹孔,看来,偷盗者本想一枪索命,却打偏了。在它的身旁,倒着几头同样被切掉牙齿的成年大象,都已经咽气了。当高桥先生尝试着去为佐伊的伤口止血的时候,它不停地挣扎,眼神里满是恐惧。看着它的眼睛,高桥先生明白,它大概永远都忘不了这种毁掉它的身体、杀光它的家人的,叫作人类的残酷种族。
因为治疗及时,这头小象奇迹般生还了。高桥先生亲自收留了它,对它非常疼爱。他甚至用妻子的名字给它命名——“佐伊”。他特地做了一个和结婚戒指相同款式的漂亮的金耳环,挂在了小象耳朵上的弹孔上。他总是告诉小象,即使没有象牙,它也是这世界上最美丽的存在。
“他还说,我和小象,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佐伊。”高桥太太扬起了嘴角,我也跟着笑了起来。
高桥先生每天都和佐伊玩耍,为它训练,教它如何在驯养的世界里开始新的生活。或许是因为童年的创伤,佐伊从来都不亲近人,也不亲近别的象群。但高桥先生是唯一的例外。他们如同父女一般,有着超越种族的爱和信任。只有在高桥先生的身边,佐伊才会恢复一只幼年小象的天真和活泼。
“虽然我没有见过佐伊,但从小就常常听到爸爸妈妈在电话里提起她。小时候,我还因为这头小象而吃过醋,觉得它比我更像是爸爸妈妈的孩子。”高桥麻美有些撒娇似地说,高桥太太怜惜地摸摸女儿的手。
一切美好因为一声枪响而终结,高桥先生的意外将他从两个他深爱的佐伊身边带走,同时,也带走了她们所有的笑容。尤其是大象佐伊,它每天傍晚都会守在庄园入口,注视着高桥先生回家的方向,一直等到天黑。
对于高桥太太来说,失去丈夫已经让她终日以泪洗面,看到大象佐伊的一举一动,都令她想起丈夫生前训练佐伊的时光。触景生情,她陷入痛苦的追忆里,无法自拔。
“所以,我决定离开非洲这个伤心地,回到日本,回到家人的身边。临走前,我将佐伊捐到了异国的动物园。我想着,不再见到它,我也就不会再因为思念逝去的丈夫而悲伤了。”她回忆说。
“但不知道是因为伤心过度还是因为环境不适,在回到日本之后,母亲的身体一直不好,去年还查出了乳腺癌。病情恶化得厉害,医生说,母亲的生命,可能已经不长了……”高桥麻美一边说一边哽咽了起来,佐藤轻轻搂住了她的肩膀。
“傻孩子,别哭了,妈妈不是还在这儿吗。”高桥太太安慰了自己的女儿,接着继续对我说,“虽然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但我还有一件事,一直想要问问佐伊。”
正当我想要问问高桥太太究竟有什么重要的事,能够让她特意拖着病重的身子、穿越大洋来询问一头大象的时候,载着我们几个人的车子已经到达了我们的目的地——佐伊所在的动物园。在和佐藤一起将高桥太太的轮椅从车上抬下来之后,我们直奔象山,在那里,生活着那头与众不同的大象。
三
在和饲养员说明了情况以后,我们一行人被特许进入象山,和佐伊近距离接触。和我几天前看到的并无二致,佐伊还是孤身一象,趴在角落的阴影里,偶尔用大耳朵扇扇风,上面挂着的小金环也跟着一闪一闪的。
“佐伊。”高桥太太轻轻唤了一声,佐伊听到了,抬起头来,望着轮椅上的她眨巴眨巴眼。
“真的是它。”高桥太太的音调因为兴奋而高扬。同一时间,佐伊似乎也认出了高桥太太。它缓慢地立起身子,一步一步地向她走近。它的长鼻子一甩一甩,像是在和她打招呼。
“是的,好久不见了,佐伊。”高桥太太好似能够听懂佐伊的语言一样,“这些年,你过得好吗?”
佐伊朝着天空,用高高扬起的鼻子来回应高桥太太的问题。高桥太太对着身旁的女儿耳语了一番。不一会儿,麻美从车上拿下了一个足足有半米高的四方形的、用丝绸包住的物件。她小心而又隆重地把这个物件交到母亲的手里。我看到高桥太太一点一点揭开那块丝绸,里面露出了一个木质的巨大相框,而相框里面,是一个男人的黑白照,大约四十多岁,唇齿清秀,眉目和气。
“这是……”我看了眼佐藤,他对着我点了点头。
“高桥英之,那位为了保护野生动物而死去的动物学家。”佐藤说,“也就是高桥太太的丈夫,将佐伊抚养长大的人。”
佐伊没有眼白的大眼睛直直地盯着那幅有些年月的相片。
“佐伊,你还记得他吗?你还记得英之吗?”高桥太太的语气有些颤抖。这两个佐伊的对话,竟让我感到一阵莫名悲伤。
我从来没有听过大象说话,但如果它可以说话,它又会怎样评价一个已经离开这个世界许久的人呢?是悲伤、是平淡,或是残忍的遗忘?我不明白高桥太太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时候,问一头或许根本听不明白她的语言的大象这样一个问题。环顾四周,佐藤和麻美的脸上,也带着一丝不安。
这时候,大象佐伊的鼻子突然动了起来,伸向了那幅老相片。它用鼻尖最柔软的部分,抚摸着照片里高桥先生的脸,从脸颊、到眉眼、再到鼻梁。它的动作很轻柔,仿佛怕弄疼这个已不存在的人一样。
接着,从佐伊的喉咙深处,传出了一声“咕噜”,坚定而又有力。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佐伊说话,也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听懂了动物的语言。
突然,佐伊转身走回了它休息的洞穴,正当我们感到奇怪的时候,它用长鼻子卷着两根长棍子,又一次走了出来。
“这是佐伊的宝贝,跟着它一起捐到动物园来的训练棍。”饲养员认出了那个物件,抱怨道,“从来没有一头大象像它那样,这么依赖那两根破棍子。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其实它早就不需要训练棍来训练了,但它从不许我们丢掉或者换掉它们。”
佐伊卷着那根训练棍,凑到了高桥先生的遗照前,它将棍子伸向那个静止的男人,仿佛在请求他,像往日一样再一次与它玩耍。它轻轻呜咽,如一个单纯的孩子。
看到这一幕,我的心里酸酸的。
高桥太太怜爱地摸摸佐伊那满是褶子的长鼻子,说:“谢谢你,谢谢你还记得英之。可是他已经不在了,再也没有办法陪你玩耍了。”
像是听懂了高桥太太的话,佐伊甩着鼻子,发出了一阵呜呜的声音。从它张开嘴里,我看到两道伤痕,那里曾经长着两根巨大的、洁白的象牙。即使已经过了那么长的时间,即使伤口早已愈合长好,但曾经的那种刻骨铭心的疼痛,依然近在眼前。
佐伊用自己的鼻子,轻轻地蹭掉了高桥太太脸颊上挂着的泪珠。高桥太太笑着,怜爱地抚摸着佐伊满是褶子的长鼻子。我想,她大概已经听到了自己想要听到的答案。
四
那天半夜,在动物园折腾了一天的我好不容易进入了梦乡,却被一阵尖利的铃声吵醒。接起电话,另一头是佐藤火急火燎的声音,他前言不搭后语地说了半天,我才听懂他的意思,“高桥太太半夜发病,现在已经被送到医院,快不行了。”
等我赶到急症室的时候,刚好看到穿着白大褂的夜班医生从ICU里出来。他用凝重的表情,对着焦急等待的佐藤他们轻轻摇了摇头,说了一声:“节哀顺变。”
虽然语言不通,但佐藤他们还是立马懂得了医生的意思。高桥麻美的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她用手抱住头,不停哭泣。佐藤试着安慰她,却不想,泪水也早已从自己的眼角溢了出来。
我一直杵在角落里,踌躇着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去面对这个刚刚失去母亲的女儿。麻美看到了我,擦了擦泪水对我说了事情的始末:“回到酒店我就觉得不对。妈妈的情绪特别激动,一直坐在书桌前写东西,我怎么劝她都不肯休息。拗不过她,我就先上床了。半夜,我迷迷糊糊地被一阵声响惊醒,叫了她好几声,可她都没有回应。我知道事情不对,抬头一看,整张椅子连着她一起倒在了地上。她双眼紧闭,眉头深皱,一看就很痛苦。等救护车把她送到医院的时候,她已经意识模糊了,用力抓着我的手,叫爸爸的名字。来中国之前,我们一直担心她的身体会吃不消,没想到最可怕的噩梦真的发生了……”
麻美从包里掏出一张对折的信纸:“这就是妈妈今晚一直在写的东西。”也许是想到这张薄薄的纸同时成了母亲的绝笔,她的悲伤一瞬间又涌了出来。
“不要难过,有我们陪着你。”佐藤红着眼睛,握着麻美的手说。麻美点点头,慢慢打开了那页纸,缓缓读了起来。
五
“一个死去的人,他曾经活过的岁月,究竟有什么意义?”
从麻美年轻而又忧伤的声音里,我看到了一个时日不多的高桥太太,一个坦然面对的高桥太太。她做着自己人生最后的思考,写下了这些从未与他人言的、生命最后的文字。
在信里,高桥太太说自从检查出乳腺癌晚期的那一天起,自己就从未停止过思考死亡。在高桥先生意外去世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她都陷在一个非常悲观的状态之中。死亡,不仅带走了她最爱的人的生命,还带走了他们所有的欢笑和幸福。留下来的那些记忆,倒不如说是一种痛苦。当初的日子越是美好,孑身一人的现今就显得愈发痛苦和孤单。
“如果注定要失去,那倒不如永远都不曾拥有。”那段日子,高桥太太宁愿所有的快乐和陪伴都不曾发生过,也不想再忍受一切美好终结时刻的煎熬。如果死亡只能给还留在世上的人带来悲伤,那自己这并不漫长的一生,又究竟有什么意义?
“当自己生命中所剩的时间越来越少的时候,人就会自发地回忆起很多东西。”这就是高桥太太选择在她人生中最后的时间里不远万里地来到中国,找寻佐伊的原因。也是为什么,她要向一头大象询问,是否还记得一个已经逝去的故人的理由。
“也许,我并不是仅仅是想要听到佐伊的回答,我也在找寻自己的答案。”她曾经想过佐伊的各种反应,遗忘、痛苦、悲伤……然而,当她看到它依然清澈的眼睛,在英之的遗像前一如往昔的纯真和亲昵,那种无法用人类语言所描绘的、超越种族和生命的羁绊之时,这么多年来一直堵在所有的情绪一下子涌了上来。在和佐伊一起流了一场眼泪以后,她突然释然了。
“死亡给仍然活着的人带来的痛苦,愚蠢的我,曾经因此而难以释怀,想尽办法去逃避。但现在我才明白,这正是故人留在世间的痕迹,是他曾经活过、爱过、被爱过的证据。”高桥太太说,她曾经怨恨过丢下自己先行离开这个世界的丈夫,但现在,她感谢他:“如果生命还能够重新来一次,我想,自己还是会做出一样的选择,去爱,去痛,去失去,去回忆。对于一个走到生命尽头的人来说,这些经历,才是一生当中最后的财富。”
在那封不长的信的最后,高桥太太说,她已经做好了离开这个世界的准备,她唯一希望的,是自己的女儿,以及所有爱着自己的人,能够更加坦然地接受这次永远的分别。
“一个死去的人,他将会永远活在记得他的人的心里。就像英之与佐伊一样,每次回忆起来,都能带来力量。”
六
在临回国之前,高桥麻美特地通过佐藤,与我见了一面。在一家极其普通的咖啡馆里,她一反常态地没有化妆、双眼红肿地坐在我的面前,在简单寒暄几句之后,她告诉我,她将会带着母亲的骨灰回到非洲,和父亲葬在一起。在那里,不仅有父亲的陪伴,同时也有他们两个人最美好的回忆。
“这样她就不会寂寞了。”她说着,红通通的眼睛直直地望着面前的拿铁咖啡,似要落泪,但嘴角又有笑容。
“今天找你,其实是有事拜托。”
她从手袋里拿出一个黑色小包,放到我的面前。我打开,黑色的丝绸里裹着一枚纯金的指环,表面的磨痕显出不少年月,但也看得出它一直被主人细心保养。在指环的内侧,我看到三个字母,Z-O-E。
“这是妈妈的结婚戒指。”麻美解释说,“爸爸亲手做的,这世界上只有两枚,另一枚挂在佐伊的耳朵上。”
“可这是你母亲的遗物,你真的不想保留它吗?”
“我很想。但它们本来就是一对,留给佐伊,比留给我更有意义。至于我,”麻美指了指心口的位置,“妈妈永远活在这里。”
七
从此之后,动物园多了一只会唱歌的大象。传说,听到它歌声的人,就可以得到幸福。
于是,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游客围在象山前,他们挥舞着香蕉和草叶,想要吸引佐伊的注意。然而,在大多数时候,它只是趴在角落里,偶尔挥挥尾巴,并不被打扰。
只有在天气转凉,早秋的清风带着淡淡的桂花香气,从远处拂来吹过的时候,风经过草丛、抖动叶片、吹散花瓣,同时,也打响了佐伊耳朵上那两个连在一起的耳环。它们一个属于佐伊自己,而另一个曾经属于那位也叫佐伊的高桥太太——那个苍白羸弱的女性,现在应该已经回到了自己最爱的先生身边安息了。在风里,那两个金色的小环叮叮咚咚地跳跃,好似风铃。
每当这时,佐伊就会开始歌唱,起先只是一阵阵咕噜咕噜的呢喃。后来,它的歌声随风变得愈发响亮,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能够清楚地听到它从嗓子里发出的每一个音节。
“唔唔唔……”
所有人都因为听到了这珍贵的歌声而欢呼。
但在我听来,这并不是歌声,而是佐伊的呼唤。它在呼唤那个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却永远活在自己记忆中的人。
我看着佐伊,它也看着我。
那张没有象牙的嘴微微咧开,我不知道它究竟是在微笑,抑或是在悲伤。但我确定那一刻的它是幸福的,因为在它的心里,有着一段永远鲜活的曾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