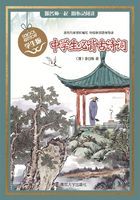朋党上
臣闻朋党者,君子小人所不免也[119]。人主御群臣之术,不务嫉朋党,务辨邪正而已。邪正不辨而朋党是嫉,则君子小人必至于两废,或至于两存。君子小人两废两存,则小人卒得志,而君子终受祸矣。何则?君子信道笃,自知明,不肯偷为一切之计;小人投隙抵巇[120],无所不至也。
臣请以《易》道与夫尧舜汉唐之事明之。《易》以阳为君子,阴为小人[121]。一阳之生则为复[122],复者,反本也[123]。三阳用事则为泰[124],泰者,亨通之时也[125]。而五阳之极则为夬[126],夬者,刚决柔也[127]。以此见君子之道,必得其类,然后能胜小人也。一阴之生则为姤[128],姤者,柔遇刚也[129]。三阴用事则为否[130],否者,闭塞之时也[131]。而五阴之极则为剥[132],剥者,穷上反下也[133]。以此见小人之道,亦必得其类,然后能胜君子也。阴阳相与消长,而为惨舒,为生杀。君子小人相与胜负,而为盛衰,为治乱。然皆以其类也。臣故曰:朋党者,君子小人所不免也。
尧之时有八元、八凯十六族者,君子之党也[134]。又有浑沌、穷奇、梼杌、饕餮四凶族者[135],小人之党也。舜之佐尧有大功二十者,举十六相、去四凶而已。不闻以其朋党而两废之,亦不闻以其朋党而两存之也。臣故曰:人主御群臣之术,不务嫉朋党,务辨邪正而已。
东汉钩党之狱[136],海内涂炭二十余年。盖始于周福、房植,谓之甘陵南北部[137]。至于李膺、陈蕃、王畅、张俭之徒,遂有三君、八顾、八俊、八及、八厨之号[138]。人主不复察其邪正,惟知震怒而已。故曹节、侯览[139]、牢修[140]、朱并[141]得以始终表里,成其奸谋。至于刑章讨捕,锢及五族,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卒不知修、并者乃节、览之党也。
唐室之季,朋党相轧四十馀年,搢绅之祸不解,盖始于李宗闵、李德裕二人而已[142]。嫌怨既结,各有植立,根本牢甚,互相倾挤。牛僧孺、李逢吉之属,则宗闵之党也。李绅、韦处厚之属,则德裕之党也。而逢吉之党,又有八关十六子之名[143],人主不复察其邪正,惟曰:“去河北贼易,去此朋党难。”[144]而其徒亦曰:“左右佩剑,彼此相笑。”[145]盖言未知孰是也。其后李训、郑注用事,欲以权市天下,凡不附己者皆指以为二人之党而逐去之,至于人人骇慄,连月雺晦,卒不知训、注者,实逢吉之党也[146]。
臣故曰:邪正不辨而朋党是嫉,则君子小人必至于两废,或至于两存。君子与小人两废两存,则小人卒得志,君子终受祸矣。
【总说】
《朋党上》、《朋党下》两篇,当作于元祐二年(1087)以后,系针对当时朋党之争而发。熙宁新党被放废弃置,怨谤横生,旧党当国,亦各为党比,以相訾议。朝廷派系林立,有洛党、蜀党、朔党等。秦观的老师苏轼被目为蜀党党魁。
北宋庆历党争,欧阳修著《朋党论》,旗帜鲜明地提出“君子有党论”,与“小人党”对垒,为党争的排他性奠定了理论基石。秦观的《朋党上》、《朋党下》论熙宁、元丰期间的新旧党争,其思想仰承欧阳修的《朋党论》。其党派意识有君子小人之辨,党同伐异的特点很明显。秦观对党争中君子党的命运洞若观火,照他看来,君子党的受祸是必然的。为什么呢?“君子信道笃,自知明,不肯偷为一切之计;小人投隙抵巇,无所不至也。”一下子抓住了小人的病态人格,洞彻小人肺腑,小人的可怕恰恰是没有道德负担,无所不为。林纾说得好:“小人得罪君子,君子虽有权,不之较也。君子取怨小人,小人即无权,亦必报复,犹之胡人以残杀为生业,举族皆能战,中华文胜,言战,非其匹也。文决小人卒得志,千古不刊之论。行文尤警醒动人。”秦观对小人的论断,当得起“千古不刊之论”。此文对欧阳修《朋党论》有所突破,就是对小人的洞察堪称燃犀下照。从论证过程来看,此文以《易》道阴阳消长论证“朋党者,君子小人所不免”的观点,确有义理。接着以尧舜汉唐时期的朋党政治来阐明之,颇有说服力。但秦观的朋党意识陷于君子小人之辨,是一种排他性的线性思维,失之简单化。
【辑评】
[近代]林纾《林氏选评名家文集·淮海集》:小人得罪君子,君子虽有权,不之较也。君子取怨小人,小人即无权,亦必报复,犹之胡人以残杀为生业,举族皆能战,中华文胜,言战,非其匹也。文决小人卒得志,千古不刊之论。行文尤警醒动人。
朋党下
臣闻陛下继位以来,虚怀仄席[147],博采公论,悉引天下名士与之经纶,至有去散地而执钧衡[148],起谪籍而参侍从者[149],虽古版筑、饭牛之遇[150],不过如此而已。君子得时,则其类自至,数年之间,众贤弹冠相继而起[151],聚于本朝。夫众贤聚于本朝,小人之所深不利也。是以日夜忷忷[152],作为无当不根[153]、眩惑诬罔之计,而朋党之议起焉。臣闻比日以来,此风尤甚,渐不可长。自执政从官台阁省寺之臣,凡被进用者,辄为小人一切指以为党,又至于三君、八顾、八俊、八及、八厨之名,八关、十六子之号,巧为标榜,公肆诋欺[154]。一人名之于前,万人实之于后。传曰:“下轻其上爵,贱人图柄臣[155],则国家摇动而人不静也。”然则其可以不察欤?
臣闻庆历中仁祖锐于求治,始用韩琦、富弼、范仲淹以为执政从官,又擢尹洙、欧阳修、余靖、蔡襄之徒列于台阁,小人不胜其愤,遂以朋党之议陷之[156]。琦、弼、仲淹等果皆罢去[157]。是时天下义士,扼腕切齿,发上冲冠,而小人至于举酒相属,以为一网尽矣[158]。赖天子明圣,察见其事,琦、弼、仲淹等旋被召擢,复蒙器使,遂得成其功名[159]。今所谓元老大儒,社稷之臣,想望风采而不可见者,皆当时所谓党人者也。向使仁祖但恶朋党之名,不求邪正之实,赫然震怒,斥而不反,则彼数人者,皆为党人而死耳,尚使后世想望风采而不可见耶?今日之势,盖亦无异于此。
臣愿陛下观《易》道消长之理,稽帝虞废举之事[160],鉴汉唐审听之失[161],法仁祖察见之明,杜媒糵之端[162],窒中伤之隙,求贤益急,用贤益坚,而信贤益笃,使奸邪情沮而无所售其谋,谗佞气索而无所启其口。则今之所谓党人者,后世必为元老大儒社稷之臣矣。
【总说】
此文与《朋党上》同气连枝,上文重在立论,此文则立足于元祐“朋党之议”,强调君主不能“但恶朋党之名,不求邪正之实”。秦观站在旧党的立场上指斥新党为小人,这是派性意识的体现,其是非的标准是模糊的,忽略了士大夫政治人格和道德人格的复杂性。就文章而论,上篇为体,下篇为用。林纾评云:“此非论体,直是一篇辩证之书,明白晓畅极矣!”“辩证之书”四字确能道出此文的特点。此文有三句话振聋发聩,堪称名言:“求贤益急,用贤益坚,信贤益笃。”
【辑评】
[近代]林纾《林氏选评名家文集·淮海集》:此非论体,直是一篇辩证之书,明白晓畅极矣!
人材
臣闻天下之材,有成材者,有奇材者,有散材者,有不材者。器识闳而风节励,问学博而行治纯,通当世之务,明道德之归,此成材者也。经术艺文、吏方将略,有一卓然过人数等,而不能饰小行、矜小廉以自托于闾里,此奇材者也。随群而入,逐队而趋,既无善最之可纪[163],又无显过之可绳,摄空承乏[164],取位而已,此散材者也。寡闻见,暗机会[165],乖物理,昧人情,执百有司之事无一施而可,此不材者也。
古之人主,于成材则付以大任而备责之,于奇材则随所长而器使之,于散材则明赏罚而磨砺之,于不材则弃之而已。四者各有所处,然而奇材者,尤人主所宜深惜者也。盖天下之成材不世出,而散材者又不足以任能事,不材者适足以败事而已。是则任天下之能事者常取乎奇材。有奇材而不深惜焉,则将与不材同弃,而曾散材之不如矣。夫匠氏之于木也,楩楠豫章[166],易直而十围者,必以为明堂[167]之栋、路寝之楹[168]。七围八围者,虽多节,必以为高明之丽[169]。拱把而上者,虽小桡,必以为狙猿之杙[170]。稍修则以为榱桷[171],甚短则以为侏儒[172]。至于液满轴解、亟沉而易蠹者[173],然后以之爨也。今有楩楠豫章于此,七围八围,拱把而上,特以多节小桡之故,遂并弃之,岂不惜哉!
人主用天下之材亦何以异于此。今国家之人材,可谓富矣。养之以学校,而取之以贡举,名在仕版者,无虑数万。然一旦有事,则常若乏人。何哉?以臣观之,未能深惜天下之奇材故也。盖不深惜天下之奇材,则用之或违其长,取之将责其备,虽有嵚嵜历落、颖脱绝伦[174]之士,执事者始以名闻,未及试之,而媒糵[175]其短者,固已圜视而起矣。夫奇材多自重,又不材者之所甚嫉也。以自重之势,而被甚嫉之毁,其求免也,岂不难哉!一旦有事,而常若乏人,其势之使然,无足怪也。
昔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176]。裨谌能谋,于野则获,于邑则否[177]。黄霸为丞相,功名损于治郡时[178]。人固有所长,亦有所短也。皋陶喑而为大理,天下无虚刑[179]。师旷瞽而为太宰,晋国无乱政[180]。贤如萧何,而有市田请地之污[181]。直如汲黯,而有褊心忿骂之鄙[182]。文如长卿,而有临邛涤器之陋[183]。将如韩信,而有胯下蒲伏之辱[184]。吏如张敞,而有便面拊马之事[185]。此数子者,责其备,则彼将老于耒耜之旁,死于大山龛岩之下耳,人主岂得而用之?
陛下即位以来,屡下明诏,举监官御史台阁学校之臣,刺史牧民之吏,与夫可备十科之选者[186],所得人材,盖不可胜数。臣愿陛下取其名实尤异者,用之而不疑。人情不能无小过。非有显恶犯大义,所当免者,宜一切置而不问,以责异时之功。则彼将输沥肝胆,捐委躯命,求报朝廷而不可得。一旦有天下四夷之事,何足患哉!
【总说】
重用奇材乃此文之大旨。成材过于理想化,可以说百年难遇。在现实中占据官位的通常是散材,这些人资质平庸,不思进取,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尸位素餐;奇材“卓然过人数等”,一旦被重用,定能建立不世功勋。但是他们往往有着细行不修、孤傲不驯等毛病,容易遭人嫉恨,被妖魔化,统治者若轻信谗言、求全责备,“奇材”将遭冷落摈斥,甚至困顿至死。这样一来,朝廷中“散材”庸碌,“不材”为祸,“一旦有事常若乏人”。宋朝元祐时期最严峻的问题是党争,党争给人才的任用带来较大负面影响,少游的人才论产生于这一历史背景下,具有鲜明的政治针对性。他提出要重视“奇材”,劝谏君主发挥奇材的长处而忽略其瑕疵,不拘一格降人才。此文结构谨严、论点明晰,文中采用譬喻,将不同的人才喻为不同的木材,想象生动,趣味盎然,颇得《庄子》神髓。
少游所列举的四类人,无论在哪类社会都存在,所指出的“奇材”不遇的悲剧,千载之下亦在所难免。他的《人材》篇因而获得了超越时空的认识价值,对我们当今如何选拔人才,任用人才都有着宝贵的借鉴意义。
【辑评】
[明]段斐君本《淮海集》徐渭评语:重奇材是大旨。〇(“昔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人主岂得而用之”)文势迅利,酷似长公(指苏轼)。
[近代]林纾《林氏选评名家文集·淮海集》:文即勿以寸朽弃连抱之材意,推阐而辩明之。读之颇有英爽之气。
论议上
臣窃闻役法之议,不决久矣。有司阅四方之牍,眩蜂起之说,牵制优游,相视而不断者,二年于兹[187]。虽稍复笔削[188],著为一切之令,取济期月,卒未有确然定论可以厌服人情传万世不弊者也[189]。其所以然者无他焉,士大夫据偏守独,各有私吝[190],不能以至公为心故耳。
何则?夫所谓役法者,其科条品目虽曲折不同,大抵不过差免二法而已。差役之法,虽曰迭任府史胥徒[191]之士,率数年而一更,然而捕盗者奔命不遑,主藏者备偿无算,囷仓竭于飞挽[192],资产破于厨传[193]。执事者患其弊也,于是变而为免役之法。虽曰岁使中外之民,悉输僦直[194]以免其身,然而平估[195]至于室庐,检括[196]及于车马,裒多以为宽剩[197],厚积以为封桩[198],则其弊又有甚于差役者矣。盖差役之法不弊,则免役之法不作;免役之法不弊,则今日之议不兴。然而士大夫进用于嘉祐之前者[199],则以差为是而免为非;进用于熙宁之后者[200],则以免为得而差为失。私意既摇于中,公议遂移于外。呜呼,岂特二年而无定论哉?虽十年而无定论,不足怪也。
昔唐室赋役之法有租庸调[201]者,最为近古。自开元之后,版图既隳,丁口田亩皆失其实,法以大弊,故杨炎变之以为两税之法[202]。已而盗起兵兴,征求无节,法又大弊,故陆贽以七事者力诋其非[203]。然而终唐之世,不复改也。夫唐之诸臣岂不知两税为非古、租庸调为近古哉?盖以晚节末路,俱为弊法,以此易彼,实无益也。今差役免役之法,盖类于此。
然则何为而可耶?臣闻楚人有第二区者,其甲则长子之所构也,其乙则少子之所构也。规摹不同,而岁久皆弊。其父谋所止,二子各请止其所构之庐,至数日不决。有邻人告之曰:“昔少君以甲第坏甚,于是营乙以舍族人。今乙第又坏,而长君复欲徙之于甲。是以坏易坏,非计之得也,何不合二第可用之材,别营一区而弃其腐桡者乎?”父以为然,其论遂定。今陛下以役法之议付于嘉祐、熙宁之臣,何异楚人之谋于二子也,盖亦质诸邻人之论哉?陛下若以臣言为然,愿诏有司无牵于故新之论,毋必于差免之名,悉取二法之可用于今者,别为一书,谓之“元祐役法”,则嘉祐、熙宁之臣皆黯然而心服矣。若夫酌民情之利病,因五方之所宜,条去取之科,列轻重之目,此则有司之事,臣所不能知之;亦犹楚人之第,某材可弃,某材可留,皆当付之匠氏,不可问诸邻人也。
《传》曰:“虽有丝麻,无弃菅蒯。虽有姬姜,无弃蕉萃。”[204]唯陛下择焉。
【总说】
《论议上》以讨论赋役之法为中心,关于差、免二法的优劣问题,直到元祐初年依然在新旧两党间纷争不休。秦观敏锐地指出,之所以讨论两年而无定论是因为“士大夫据偏守独,各有私吝”,深中党争之弊。少游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评议王安石的新法,褒贬取舍之间,颇能秉公而发,唯理是论。在他眼中,差、免二法各有利弊,差役法使“捕盗者奔命不遑,主藏者备偿无算,囷仓竭于飞挽,资产破于厨传”,让百姓常常不得自由,使民心无定、社稷不安。可是免役法“虽曰岁使中外之民,悉输僦直以免其身,然而平估至于室庐,检括及于车马,裒多以为宽剩,厚积以为封桩”,也同样弊端颇多。虽然免役法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对农民的人身束缚,但扩大了征敛面,朝廷得到巨额收益,底层人民却苦不堪言。元丰以后,皇帝的内藏库(即封桩库)逐渐增多,以便储存金帛。少游指责免役法剥夺百姓财富,是有现实根据的。他提出折中的意见,于差免二法之外别立“元祐役法”,亦可见出他为天下计的良苦用心。然而这只是一个过于理念化的建议,少游本人并没有考虑付诸实施的具体立法的细节。
此策论艺术上一个显著的特色是善于运用寓言,作者讲述了一个楚人择屋的小故事,朝廷徘徊于差、免二法之间而莫衷一是的状态便昭然若揭了,既娓娓动听,又蕴涵哲理。
论议下
臣闻世之议贡举者,大率有三焉:务华藻者以穷经为迂阔,尚义理者以缀文为轻浮,好为高世之论者则又以经术文辞皆言而已矣,未尝以为德行[205]。德行者,道也。是三者,各有所见而不能相通。臣请原其本末而备论之,则贡举之议决矣。
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动,当周旋进退之时,必称《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206]。其后聘问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于布衣,于是贤人失志之赋兴,屈原《离骚》之词作矣。此文词之习所由起也。及其衰也,雕篆相夸,组绘相侈[207],苟以哗世取宠而不适于用,故孝武好神仙,相如作《大人赋》以风其上,乃飘飘然有凌云之志[208]。此文辞之弊也。昔孔子患《易》道之不明,乃作《彖》、《象》、《系辞》、《文言》、《说》、《序》、《杂卦》十篇,以发天人之奥[209]。而左氏亦以《春秋》之法弟子传失其真,于是论本事作传,以记善恶之实[210],此经术之学所由起也。及其衰也,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故汉儒之陋,有曰秦近君能记说《尧典》二字至十馀万言,但说“若稽古”犹三万言也[211]。此经术之弊也。
古者民有恭敏任恤者,则闾胥书之;孝悌睦姻有学者,则族师书之;有德行道艺者,则党正书之[212]。而又考之于州长,兴之于乡老大夫,而论之于司徒、乐正、司马[213]。所谓秀选进造之士者是也。然后官而爵禄之,此德行之选所由起也。及其衰也,乡举里选之法亡,郡国孝廉之科设,而山林遗逸之聘兴。于是矫言伪行之人,弊车羸马,窜伏岩穴,以幸上之爵禄。故东汉之士有庐墓而生子[214],唐室之季或号嵩少为仕途捷径[215]。此德行之弊也。是三者莫不有弊,而晚节末路文辞特甚焉。盖学屈宋而不至者,为贾马班扬[216];学贾马班扬而不至者,为邺中七子[217];学邺中七子而不至者,为谢灵运[218]。沈休文之撰《四声谱》也,自谓灵均以来此秘未睹,武帝雅不好焉[219];而隋唐因之,遂以设科取士,谓之“声律”[220]。于是敦朴根柢之学,或以不合而罢去;靡曼剽夺之伎,或以中程而见收[221]。自非豪杰不待文王而兴者,往往溺于其间。此杨绾、李德裕之徒所为切齿者也[222]。熙宁中,朝廷深鉴其失,始诏有司削去诗赋而易以经义[223],使学者得以尽心于六艺之文,其意信美矣。然士或苟于所习,不能博物洽闻以称朝廷之意。至于历世治乱兴衰之迹,例以为祭终之刍狗,雨后之土龙,而莫之省焉[224]。此何异斥桑间濮上之曲[225],而奏以举重劝力之歌[226]?虽华质不同,其非正音,一也。
传曰:“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骅骝骐骥,一日而驰千里,捕鼠则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鸱鸺夜撮蚤、察毫末,昼出瞋目而不见丘山,言殊性也。”[227]今欲去经术而复诗赋,近乎弃本而趋末;并为一科,则几于取人而求备。为今计者,莫若以文词、经术、德行各自为科,以笼天下之士;则性各尽其方,技各尽其能,器各致其用,而英俊豪杰庶乎其无遗矣。
【总说】
此篇专论贡举。神宗熙宁以前之科举,先策论,次诗赋。熙宁四年(1071),更定科举法,从王安石议,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专以经义、论、策试士。哲宗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请立经明行修科。吕公著当国,请复制科。当是时,在经义、诗赋、德行分科试士方面,尚争论不休。
少游采用“原其本末”的方法来解决纷争。他开篇明义地提出文辞、经术、德行这三科都各有其弊。接着引证史实,分别指出:文辞之弊,在于“哗世取宠而不适于用”;经术之弊,在于皓首穷经、老死章句;德行之弊,在于令“矫言伪行之人”也能“幸上之爵禄”。特别是唐末五代时期的以文辞取士,使人溺于“靡曼剽夺”之小技,其弊尤甚。因而肯定熙宁中废诗赋乃“朝廷深鉴其失”、“其意甚美”,但他也不赞成以经义全盘取代诗赋,而是建议“以文词、经术、德行各自为科,以笼天下之士”。秦观的建议是客观中肯的,的确能达到最大限度吸纳各类人才的目的,元祐四年,朝廷分经义、诗赋为两科取士,就毫无疑问地证明了其建议的可行性。
少游批评文词之弊的一段文字,是针对当时还存在的西昆体的馀风而发,反映了他重视文学的社会价值,反对形式主义文风的积极文艺观。然而,他说“学屈宋而不至者,为贾马班扬;学贾马班扬而不至者,为邺中七子;学邺中七子而不至者,为谢灵运”,却是不切实际的文学退化论。
官制上
臣闻王者用人之术惟资望[228]而已。岁月有等,功劳有差,天下莫得躐而进[229]者谓之资。行能术业卓然高妙,为世所推者谓之望。用人以资而已,则盛德尊行、魁奇隽伟之人,或拘格而邅回[230],如张释之[231]十年不得调,扬子云[232]位不过侍郎之类是也。用人以望而已,则狂缪之流、矫亢之士,或以虚名而进拔,如晋用王衍[233]、唐用房琯[234]之类是也。
古之善用人者不然,以资待天下有常之士,以望待天下非常之材,使二者各有所得,足以相推而不足以相碍。故自一命以至九命,自受职以至作牧,非有功不迁,非有缺不补,而天下不以为淹[235]。或举于耕[236],或举于版筑[237],或举于屠钓[238],加之士民之上,委以将相之权,而天下不以为骤。何者?资之所当然,望之所宜尔也。
国家以寄禄格为有定之制,而以职事官为不次之选[239]。于先王用资望之术,可谓得其意矣。然臣愚犹以为未者,太必于用资,太不必于用望也。何则?夫郡守者,民之师帅,天子所与共理者也。衣冠而坐堂皇之上,则宾客造谒于前,掾属趋走于下,政教赏罚军旅之事,一皆听其可否。所为是,则千里蒙其赐;所为非,则数十万室受其害。可谓天下之重任矣。今将相大臣自朝廷而出者,不过为郡守;而仕尝再为通判者,苟无大恶显过,有保任人亦必至于郡守[240]。是将相大臣与保任尝再为通判者,相去无几耳。夫贤者能使所居官重,不肖者反之。今二千石所以不至尊重难居者,非特法令使然,亦其人材之所致也。岂非所谓太必于用资乎?馆阁[241]者,图书之府,长育英材之地也。从官于此乎次补,执政于此乎递升,故士非学术艺文屹然为一时之望者,莫得而居之,可谓天下之妙选矣。今中材凡吏,一为大臣之所论荐,则皆得居其位,尝有金谷之职[242],兵刑之劳[243],则皆得假其名。呜呼,比岁已来,校书正字[244]之职,龙图集贤[245]之号,何其纷纷也!
传曰:“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246]此不几于以名器而假诸人乎?臣所谓太不必于用望者,此也。昔汉制,郡守入为三公[247],学者以东观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248],言其清祕,常人所不能到也。愿下明诏,应中州已上,非更台、省、寺、监、漕、刑[249]之任者,不得为郡守。慎惜馆阁之除,以待文学之士。则用人之术,庶乎其尽矣。
【总说】
少游《官制下》云:“先皇帝恻然悯之,始诏有司作寄禄格。”“先皇帝”当指宋神宗,于元丰八年(1085)驾崩。故知《官制上》、《官制下》两篇作于元祐初。
在《官制上》、《官制下》两篇中,少游对国家如何合理任用人才,授予官职提出了建议。上篇主要围绕“资”与“望”的问题进行讨论。在他看来,资历和声望在仕进之途上有着同等的重要性,需要统治者权衡考虑,如果只注重一方,忽略另一方,就会造成“盛德尊行、魁奇隽伟”之士沉沦下僚或“狂缪之流,矫亢之士”身居高位的不公现象。只有“以资待天下有常之士,以望待天下非常之材,使二者各有所得,足以相推而不足以相碍”,才能真正做到人尽其才,令天下心悦诚服。少游认为当下国家采用的职官制,总体上是得“资望之术”真意的,但是又指出其中的弊病,即所谓“太必于用资,太不必于用望也”。一方面当今官制重视资历太甚,而获得资历的程序又过于容易,以至于资质平庸之人也能身居要职、声名显赫。另一方面名器轻易假人,有损馆阁的纯净,文人的尊严。这些议论皆是针对北宋职官制的弊端而发,作者冷静敏锐地看到了隐藏在官制下潜在的危机,为有宋一代的“冗官”泛滥现象敲响了警钟。无怪明人张评曰:“至于灼见一代之利害,建事揆策,与贾谊、陆贽争长;沉味幽玄,博参诸子之精韵;雄篇大笔,宛然古作者之风。”
【辑评】
[近代]林纾《林氏选评名家文集·淮海集》:以资望定入仕之途,复能指出太用资望者之弊,大有分风擘流之能力。
官制下
臣闻国家次五代一切之制,百官称号,最为杂糅,名存而器不设,文具而实不应[250]。所谓台、省、寺、监者,朝廷之官也,而其泛及于州县管库之吏,其滥至于浮屠黄冠之师[251]。乖违之条,爽缪之目,至不可胜数。先皇帝恻然悯之,始诏有司作寄禄格[252],以易天下之官而归之于台、省,还之于寺、监。然后循名可知其器,而缘实亦得其文,可谓帝王之盛典矣。
然有所未尽者,臣窃昧死而妄议焉。何则?自正议大夫以上,迁进太略;自中散大夫以下,清浊不分也[253]。夫迁进太略,则大臣侥幸,而其弊也至于无以复加而法制乱;清浊不分,则小臣偷惰,而其弊也至于莫为之宠而资望乖。旧制侍郎至仆射凡十二迁[254];其兼侍从之职者,八迁、九迁;其任执政之官,犹六迁也。盖侍郎以上,皆天子之臣,非多其等级,则势必至易极。易极,则国家庆赏将窒而不得行。此制官之深意也。今寄禄格则不然,自正议大夫,不问人之如何,四迁而至特进[255]。故大臣为特进者,遇朝廷有大庆赏,则不得已而以司空之官予之。夫司空者,职事官也,寄禄无以复加而予焉,岂非所谓乱法制之甚欤?旧制少卿之官,率一秩而有四名:太常、光禄、卫尉、司农是也[256]。郎官、员外,率一秩而有八名,如礼、工、祠、屯、主、膳、虞、水之类是也[257]。京朝之官,率一秩而有三名,如太常、秘书、殿中诸丞是也[258]。盖入仕之门,有制策进士、明经诸科、任子杂色之异[259]。历官之途有台、省、寺、监、漕、刑、郡、县之殊。非铢铢而较之,色色而别之,则牛骥同皂[260],贤不肖混淆,而天下皆将泛泛然偷取一切,不复淬励激昂,以功名为己任。此亦制官之深意也。今寄禄格则不然,自中散大夫以下至承务郎,秩为一名而已。故尝任台省之职、或任漕刑之司者,人心有所不厌而莫为之宠,则往往假以龙图、集贤之号。夫龙图、集贤之号,所以待天下文学之士也。而以诸吏莫为之宠而假焉,岂非乖资望之甚欤?
盖爵禄者,天下之砥石,圣人所以砺世磨钝者也[261]。夫不为爵劝不为禄勉,古之人有行之者,蒙榖是也[262]。齐死生,同贫富,等贵贱,古之人有行之者,庄周是也[263]。今朝廷之臣皆得庄周、蒙榖而为之,则爵禄之器,虽不复设可矣。如其不然,则迁进太略、清浊不分之弊,安得而不革哉?
晁错曰:“爵者上之所命,出于口而无穷。”[264]韩愈曰:“圣君所行,即是故事。自古岂有定制也?”[265]愿诏有司以寄格再加论定,稍放旧制,自正议大夫以上更增四秩之号,自中散大夫以下秩之号为三等之名。如此则迁进颇详,而法制不乱;清浊稍异,而资望不乖,是亦先皇之志也。惟陛下留神省察。
【总说】
此篇紧承上文,着重论述“寄禄格”的弊端。秦观指出其失在于“自正议大夫以上,迁进太略;自中散大夫以下,清浊不分也”。接着分而论述“迁进太略”及“清浊不分”所导致的严重后果。旧制官吏品阶较多,国家的庆赏制度尚可保证通行无碍。而如今朝中大臣升迁过快,遇朝廷大庆赏只能屡授司空之显职,造成混乱。旧制官员,一机构之下一秩多名,职责各异,统辖清晰。而如今秩为一名,多假本该授予文士的“龙图”、“集贤”之号以为之宠,造成资望乖谬。进而举蒙榖、庄周之例说明世人没有超脱爵禄的境界,再次强调“寄禄”之弊不得不革。少游并没有一味推崇旧制,主张返回旧制,从他将《汉书》原文“盖爵禄者,天下之砥石,高祖所以砺世磨钝者也”中的“高祖”换为“圣人”便可看出,他主张的是“圣人”之制,而非“高祖”之制,只有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对官制予以调整,才能做到“法制不乱”、“资望不乖”。
【辑评】
[近代]林纾《林氏选评名家文集·淮海集》:痛论寄禄格之弊,自是见到当日升转滥处;然“易极,则国家庆赏窒而不行”句,语如铁铸。
将帅
臣闻将帅之难其人久矣[266]!势有强弱,任有久近,敌有坚脆,地有远迩,时有治乱,而胜败之机不系焉,惟其将而已矣。
昔智氏以韩魏三国之兵伐赵[267],马服君之子以四十万之众抗秦[268],可谓强矣,而溃于晋阳,坑于长平。廉颇率老弱之卒守邯郸[269],田单鸠创病之余保即墨[270],可谓弱矣,而栗腹以摧,骑劫以走:是不在乎势之强弱也。穰苴之用于齐,拔于闾伍之中也,一日斩庄贾,晋师罢去,燕师渡水而解[271];韩信之击赵,非素拊循士大夫也,背水一战而擒赵王歇,斩成安君[272]:是不在乎任之久近也。以周瑜之望曹公,不啻虎狼,而吴兵捷于赤壁[273];以玄德之视陆逊,甚于雏,而蜀师衂于白帝[274]:是不在乎敌之坚脆也。东西异壤也,而邓艾以缒兵取成都[275];南北异习也,而王镇恶以舟师平关中[276]:是不在乎地之远迩也。夫以东晋之衰,而谢玄得志于淝水[277];开元之盛,而哥舒翰失利于潼关[278]:是不在乎时之治乱也。故善将者势无强弱,任无久近,敌无坚脆,地无远迩,时无治乱,不用则已,用之无不胜焉。故曰惟其将而已矣。
虽然,有一军之将,有一国之将,有天下之将。走及奔马,射中飞鸟,攻坚城,破强敌,所向无前,此有勇之士,一军之将也。出奇制胜,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279],攻辄破,击辄服,此有智之士,一国之将也。福于己而祸于人,则功有所不立[280]。利于今而害于后,则事有所不为[281]。功成事毕,自视缺然,无矜大之色[282],此有道之士,天下之将也。古者阃外之事,将军制之,军中不闻天子之诏[283],其委任责成如此。非有道之士,其可以轻付之哉?
国家将帅可谓盛矣!阅礼乐而敦《诗》、《书》者肩摩而毂击[284],纵横剽悍、称智囊而号肉飞者[285],至不可胜计。然驿骑有赤白囊至[286],则庙堂之上为之纷然。进止赏罚皆从中决者何也?岂以为将帅者皆智勇之人,非有道之士,不可独任故耶?
夫庙堂议边事,则王体不严;将帅之权轻,则武功不立。呜呼,可谓两失之也。臣以为西北二边[287],宜各置统帅一人,用大臣材兼文武、可任天下之将者为之。凡有军事,惟以大义上闻,进退赏罚,尽付其手,得以便宜从事[288]。如此则虽有边警,可以不烦庙堂之论。而豪杰之材,得以成其功矣。
【总说】
秦观的策论,大都有为而发,不尚空言。许多建议都深中积弊。鉴于唐五代藩镇割据拥兵自重的恶果,宋朝开国以来,一直猜忌防范武将,不敢授以重兵、委以全权。自太宗以后,将帅出征,朝廷都会预受策略和阵图,将帅只能“主文书,守诏令”,以至积习愈深,弊病愈多。在元丰四年(1081)对西夏的战役中,宋神宗刚愎自用,任用李宪、王中正等宦者监军,导致错失良机,反胜为败。《将帅》篇极力强调将帅的重要价值,就是针对北宋军事上的孱弱而言的。文章开门见山地提出“势有强弱,任有久近,敌有坚脆,地有远迩,时有治乱”,胜败之机皆不系于此,而系于将帅,并引用一系列历史上的著名战役,来论证将帅的决定性作用。“采故实于前代,观通变于当今”(《文心雕龙·议对》),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将帅既如此关键,那么将帅的智勇与人品就显得格外重要,因而秦观对将帅又有“一军之将,一国之将,天下之将”之辨析,他认为“天下之将”乃“有道之士”,可委以军机重任。而对朝廷兵气之不振,他发出了慨叹:“夫庙堂议边事,则王体不严;将帅之权轻,则武功不立。呜呼,可谓两失之也。”为了改变这种“两失”的状况,他建议朝廷放开手脚,在西北边关“各置统帅一人,用大臣材兼文武、可任天下之将者为之。凡有军事,惟以大义上闻,进退赏罚,尽付其手,得以便宜从事”,给予“智勇”、“有道”之将充分的权力,使之统领全局。秦观的意见无疑是剀切的,然而北宋王朝帝王独揽兵权已是积重难返,可叹也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
【辑评】
[明]段斐君本《淮海集》徐渭眉批:历叙雄爽,然多主蒙庄《说剑篇》。〇(“昔智氏以韩魏……惟其将而已”)工炼。
[近代]林纾《林氏选评名家文集·淮海集》:宋鉴于唐藩镇之祸,故无特将专师之人。用一狄武襄,犹怀疑忌,而进退赏罚,尽付其人,能动听邪?然文字实切中北宋之流弊。
奇兵
臣闻万物莫不有奇,马有骥,犬有卢,畜之奇也[289]。鹰隼将击,必匿其形,虎拟而后动,动而有获,禽兽之奇也。天雄、乌喙、堇葛之毒[290],奇于药。繁弱、忘归[291],奇于弓矢。鹈、莫邪,奇于刀剑[292]。云为山奇,涛为海奇。阴阳之气,怒为风,交为电,乱为雾,薄而为雷,激而为霆,融散而为雨露,凝结而为霜雪,天地之奇也。
惟兵亦然,严沟垒,盛辎重,传檄而出,计里而行,克期而战,此兵之正也。提百一之士,力扛鼎而射命中者,缒山航海,依丛薄而昼伏,乘风雨而夜起,恍焉如鬼之无迹,忽焉如水之无制,此兵之奇也[293]。兵之道莫难于用奇,莫巧于用奇,莫妙于用奇。何以言之?凡用奇之法,必以正兵为主,无正兵为主而出者,谓之孤军。孤军胜败,未可知也。霍去病所将,常选有大军继其后,是以深入而未尝困绝[294]。李陵提步卒五千,转斗单于于漠北,而无他将援之,其擒宜矣[295]。故曰:莫难于用奇。
夫材有勇怯,技有精冗。勇者克敌,则怯者奋;冗为敌破,则精者却:自然之势也。善将者,择其精勇以为奇,悉其冗怯以为正。奇兵虽少,而以锐为正之势;正兵虽杂,而以众为奇之势[296]。长短相补,强弱相资,则寡者亦为众,冗怯者亦为精勇也。故曰:莫巧于用奇。
昔岑彭泝都江而上以拔武阳,绕出延岑军后,而公孙述惊[297]。邓艾取阴平道,下油江,破绵竹,径薄成都,而刘禅降[298]。孙处自江左浮大海,直揜番禺,而卢循破[299]。李愬越文成戍,歼张柴栅,夜袭蔡州,而吴元济擒[300]。此数子者,皆智谋足以料敌,勇敢足以决胜,故能乘变投隙而就其功名。使敌虽有强将劲卒,不得尽试其能,而固已败也。故曰:莫妙于用奇。
孙膑曰:“解杂乱纠纷者不控捲,救斗者不搏撠,批亢捣虚,形禁势格,则自为解耳。”[301]则非夫通阴阳之幾、达万物之变以得用奇之奥者,何足以及此?
今夫屠者之解牛也,经肯綮则以刀,遇大则以斧。至庖丁则不然,批隙导窾,游其刃于空虚,而磔然已解矣[302]。弈者之斗棋也,谛分审布[303],失其守者,逐而攻之。至弈秋[304]则不然。倒行而逆施,用意于所争之外,而沛然已胜矣。夫屠、弈,鄙事也,有奇技则无与抗者,况于兵乎。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胜。”[305]然而天下之狃[306]于常而骇于变,知所以合者多,而悟所以胜者少也。
【总说】
本篇作于元丰三年(1080)。《汉书·艺文志》载录兵书五十三家,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类而罗列之。《奇兵》即少游从四术中“权谋”类的“以正守固,以奇用兵”引申阐发而来,反映了他颇为精到的军事理论。
秦观豪隽慷慨,喜谈兵论战的个性特征,最鲜明地体现在他有关军事的策论中,自少年时代起,少游便渴望在边塞战争中建功立业,他长期研究兵法,深得其中精髓,并融汇为自成体系的军事理论。文人论兵,秦观堪与唐代杜牧媲美,清代姚莹《论诗绝句》论杜牧云:“谁从绛蜡银筝底,别识谈兵杜牧之。”这两句也同样适用于他。在本篇《奇兵》中,少游着重强调出奇兵以致胜的重要性。他首先指出天地万物莫不有奇,以一系列的比喻形成排比之势引出奇兵,气势磅礴而文采斐然。接着提出论点:“兵之道莫难于用奇,莫巧于用奇,莫妙于用奇。”分头阐述这三点之原因,以霍去病和李陵胜败的对比揭示出用奇兵之难,以“长短相补,强弱相资”揭示出用奇兵之巧,以岑彭、邓艾、孙处、李愬攻敌不备从而取胜揭示出用奇兵之妙,进而又用庖丁解牛同弈秋斗棋两个典故,进一步说明奇技之重要。本文引用大量史例以古证今,严密而有说服力。既构架谨严,又流畅自然。
【辑评】
[明]段斐君本《淮海集》徐渭评语:笔端奇横,是古今文中利器。
[清]王敬之《小言集·宜略识字斋杂著》:元祐邑贤中,惟少游进策谈兵。
盗贼上
臣闻治平之世,内无大臣擅权之患,外无诸侯不服之忧。其所事乎兵者,夷狄、盗贼而已。夷狄之害,士大夫讲之详,论之熟矣。至于盗贼之变,则未尝有言之者,夫岂智之不及哉?其意以为不足恤[307]也。
天下之祸尝生于不足恤。昔秦既称帝,以为六国已亡,海内无足复虑,为秦患者,独胡人耳[308]。于是使蒙恬北筑长城,却匈奴七百馀里[309]。然而陈胜、吴广[310]之乱乃起于行伍阡陌之间。由此言之,盗贼未尝无也。夫平盗贼与攘夷狄之术异,何则?夷狄之兵,甲马如云,矢石如雨,牛羊橐驼转输不绝,其人便习而整[311],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边也,利速战以折其气。盗贼则不然,险阻是凭,抄夺是资,亡命是聚。胜则乌合,非有法制相縻;败则兽遁,非有恩信相结。然揭竿持梃,郡县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群起也,速战以折其气[312],勿迫以携其心[313]。盖非速战以折其气,则缓而势纵;非勿迫以携其心,则急而变生。
今夫虎之为物,啸则风生,怒则百兽震恐[314],其气暴悍,可杀而不可辱。故捕虎之术,必先设机穽,旁置网罟,撞以利戟,射以强弓,鸣金鼓而乘之[315],不旋踵而无虎矣[316]。至蛇与鼠则不然。虽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风生之勇;其贪足以蠹物,而非有震恐百兽之威。然不可以骤而取者,以其急则入于窟穴而已。故捕蛇鼠之术,必环其窟穴而伺之,薰以艾,注以水,彼将无所得食而出焉,则尺棰可以制其命。夷狄者,虎也。盗贼者,蛇鼠也。虎不可以艾薰而水注,蛇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撞。故曰:平盗贼与攘夷狄之术异也。
虽然,盗贼者平之非难,绝之为难。平而不绝,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盖招降与穷治是已。夫患莫大于招降,祸莫深于穷治。何则?凡盗贼之起,必有枭桀而难制者[317]。追讨之官,素无奇略,不知计之所出,则往往招其渠帅而降之,彼奸恶之民见其负罪者未必死也,则曰:与其俛首下气以甘饥寒之辱,孰若剽攘攻劫而不失爵禄之荣。由此言之,是乃诱民以为乱也。故曰患莫大于招降。凡盗贼之首,既已伏其辜[318]矣,而刀笔之吏不能长虑却顾,简节而疏目[319],则往往穷支党[320]而治之。迫胁之民见被污者必不免也,则将曰:“与其婴锢金木[321]束手而受毙,孰若遁逸山海,脱身而求生。”由此言之,是驱民以为乱也。故曰:祸莫深于穷治。
且王者所以感服天下者,惠与威也。仁及有罪则伤惠,戮及不辜则损威。威惠两失,而欲天下心畏而力服,尧舜所不能也。《夏书》曰:“歼厥渠魁,胁从罔治。旧染污俗,咸与维新。”[322]盖渠魁尽杀而不赦,则足以夺奸雄之气;胁从污染不治而许其自新,则足以安反侧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肯舍生之途而投必死之地哉?呜呼,先王已乱之道,可谓至矣!
【总说】
少游论盗贼之文有三篇,皆作于元丰三年庚申(1080),此为上篇。
宋代开国以来,就处在农民起事的风暴中。从初年的王小波、李顺起事,到庆历年间京东王伦、京西张海、贝州王则起事,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事始终未绝,摇撼着赵宋王朝的政权。面对起来造反的民众“小则蜂屯蚁聚,掳掠闾里;大则擅名号,攻城邑,取兵库,释死罪,杀掠吏民”(《盗贼下》)的状况,少游从安定社稷的大局着眼,向朝廷提出了平定盗贼的建议。他首先点明盗贼对国家的治乱与夷狄有着同等威胁,士大夫必须对此隐患提高警惕。接着指出平盗贼与攘夷狄之术不同,攘夷应“速战以折其气”,平贼则“勿迫以携其心”,在作者眼里夷狄是老虎,盗贼乃蛇鼠,形象地阐述了消灭实力性质不同的敌人应该采用不同的策略。长期以来,朝廷对待盗贼的措施只有“招降”和“穷治”两种,这样只会造成“平而不绝”的窘况,由此得出“患莫大于招降,祸莫深于穷治”的结论。因为招降就等于暗示民众,走投无路时与其忍气吞声,倒不如扯旗造反。因为造反还能受招安,博个封妻荫子的前程。这无疑是“诱民以为乱”。而穷治又过于严苛,往往殃及无辜,那些被构陷牵连的百姓有口莫辩,为了生存只好对抗到底,这又无异于“驱民以为乱”,只有惠威并施,宽严相济,“渠魁尽杀而不赦”,“胁从污染不治而许其自新”,才能从根本上肃清盗贼。秦观清醒地看到安内问题的严峻性,并提出合理有效的建议,极有实用价值,无怪乎他的朋友道潜赞其“胜理非空文,灼可资庙谋”。
从艺术上看,此文说理透彻,入木三分,又能设喻巧妙,形象与思理兼而得之,洵称佳构,可摩东坡之垒。当然,秦观把起事的农民一概称之为盗贼,完全是出于士大夫的阶级立场,不足为训。但起事农民中确有一些只起破坏作用的流氓无产者,称之为盗贼,仍有一定的合理性。
【辑评】
[近代]林纾《林氏选评名家文集·淮海集》:大旨全在擒贼擒王,亦是常解。然招降、穷治两弊,却说的切实无伦。其曰负罪者未必死,被污者必不免,穷深极邃,文无遗意,仿佛苏家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