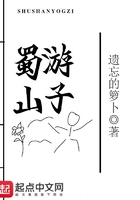遝颓得了安夷公主允诺,欢喜不尽的回到衡山派长安总领处。总领处在长安城西柳市中。柳市是长安九市之一,本就商贾云集,自衡山派在此建总领处后,各地豪强游侠皆是蜂拥而至,柳市便更是繁盛了,所谓:“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阖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可见一斑。方到门口,朱正风便一脸焦急的拉住了遝颓,道:“先生可算是回来了,再寻不着你,我们就要闯进长秋殿了!”遝颓心情大好,笑道:“朱大哥如此牵挂于我,我可消受不起。”朱正风急道:“先生毋要玩笑,天塌下来了!”遝颓狐疑道:“甚么事?”朱正风附耳道:“李掌门、赵总领和几位副总领皆受伤了,总领处的大夫束手无策。”遝颓几是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当今武林,谁能有此实力?”焦急之下,亦没了那么多客套,叫道:“你啰嗦个甚,快带我去!”
情形要比遝颓想象的要严重的多,赵侽门和几个副总领已是昏迷,不省人事,李囬妟略好些,却也是委顿不堪。一见遝颓,挣扎道:“快瞧瞧侽门!”遝颓探了下脉,皆是上焦经脉受损,难怪寻常大夫不能用药,沉吟良久,方才开了一方子,自己亦无十分把握,只将单子交给朱正风,道:“速去速回。”朱正风如何敢怠慢,飞也似的去了。遝颓又给赵侽门几人服了几颗自炼的丹药,方才给李囬妟检视,同样是上焦经脉受损,伤势却是要轻许多,无甚大碍,便道:“李掌门伤势只需用些药,静养两三月便好。”李囬妟盯着遝颓道:“侽门呢?”遝颓道:“若是熬过今晚,心肺淤血能够化开,遝颓当有七分把握。”李囬妟脸一下涨的血红,点点头,却没有说话。
遝颓总觉着李囬妟对赵侽门非同一般,却不敢细问,只道:“赵总领不是去和各处商帮协商去了么?怎会和掌门一起受伤?当今武林,又有谁家有此实力?”李囬妟道:“是我们大意轻敌了。中了阿拉提和华山派的埋伏,当时我正和阿拉提对掌,没成想华山派半路杀出,张耀偖那老匹夫忽施偷袭,若不是侽门和几个副总领拼死相救,这次便折在他手里了。”遝颓道:“张耀偖敢如此公然撕破脸皮,必定是周密策划,算准不会失手,可是他还是低估了李掌门和赵总领。只是,我们昨日方才商议好计划,今日华山派便抢了先机,是谁走漏了消息?昨日之谈话,可止我们三人知晓。”李囬妟默然良久,没有接话,遝颓忽的明白,便亦不再做声,良久,李囬妟才道:“距下月初一止有五日,我和侽门皆不能赴华山,便是从其它总领出调遣人手,亦是无充裕之时间,华山之会,你是孤掌难鸣。”遝颓摇摇头,道:“正要向掌门禀告。”便将安夷公主之事说了,连拜师张五郎亦未隐瞒。李囬妟却没有听说过张五郎,也没怎么放在心上,但对安夷公主表示支持衡山派很是欢喜,道:“如不是你,衡山派今日一败涂地。”
正说话间,朱正风端着几碗熬好的汤药过来,遝颓恰着几人的人中方才将汤药灌到肚中去,李囬妟见状,满脸忧思,自己也喝了一碗,强自和遝颓守到丑时,赵侽门和几个副总领果真都呕了好几口淤血出来,遝颓方才长舒了口气,道:“李掌门可安心歇息了,淤血一出,性命再无忧了。”李囬妟这才放心,朱正风便自扶着去了卧房,遝颓却是还需随时看护,强打着精神又陪了一个时辰,终是熬不过,便伏在案上沉沉睡去。
醒来之时,却见脚下放着一盆炭火,肩上盖着件银狐披风,嚜岫正在给几个副总领喂汤药,李囬妟亦不知何时来到了房间内,欣喜的看着门下弟子。遝颓很觉不好意思,尴尬一笑,道:“不知怎的就睡着了。”李囬妟道:“无妨,这又非你份内之事。”又对嚜岫道:“你且下去。”嚜岫应了一声,很是幽怨的瞧了遝颓一眼,便退了出去。李囬妟道:“现下长安总领处一个总领、四个副总领皆不能理事,这担子,遝颓先擔着罢。”遝颓便一边给赵侽门一干人探脉,一边道:“如今华山派已公然对衡山派动手,长安总领处需得再增人手,遝颓不能久处长安,还是从别处调来几个副总领为好。”赵侽门和几个副总领早已醒转,见遝颓探视,皆点头示意,遝颓便道:“莫要动,诸位需得静养些日子才行了。”李囬妟道:“我已经传书于枏先生了,叫他调配人手,这些日子,你还是得替我管一下才行。”
遝颓舒了口气,道:“岂敢不效劳?”李囬妟道:“华山派已知你假死之事,这些时日,切莫外出。只是去华山之时,若无得利人手相护,只怕华山派下黑手。”遝颓道:“这个掌门毋须过虑,有安夷公主在,应是无碍。”李囬妟道:“虽是如此,只怕华山派狗急跳墙。”遝颓点点头,道:“不若这样,华山派下属各小帮派,掌门不如先给他灭掉几个,便是野马帮,亦是可以有所动作了。一则,衡山派首脑受伏击,岂能无报复之理?二则,清除了这些小帮派,他日料理华山派,便无挂碍,三则,是分散华山派之注意力,使之不能全力以赴华山之会,四则,亦是向匈奴人和各处商帮展示衡山派之实力,使之能通晓利害。”李囬妟叹道:“江湖从此多事矣。”遝颓几是有些不可思议的看着李囬妟,暗想:“这是真心还是假意呢?道:“江湖哪日不曾无厮杀?”
李囬妟沉吟良久,方才道:“此非我本愿。”遝颓亦是良久才道:“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居八九。”李囬妟道:“前些时日过塑方,听一老夫人唱《诗经》: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遝颓知道,这是《诗经.卫风》中的一首《伯兮》,讲的是一位妇女因担忧远征的丈夫而痛苦不堪,丈夫尚未达到战场,她已经是生活于孤独与恐惧之中。李囬妟唱罢,道:“其声哀哀,我每每思之,便觉如今之事业,不知使多少弟子离散,使多少弟子妇人独守空房,孤老一生,其事果可为乎?”遝颓道:“掌门有此悲天悯人之心,华山派有乎?如今箭在弦上,掌门却操此妇人之仁,衡山派便是就此止息干戈,亦不需华山派有此心乎?当断不断,它日李掌门便是想做一富家只怕亦是不能!”
李囬妟叹道:“只是有感而发罢了,多年江湖漂泊,多少有些倦怠了,牢骚几句而已。如何能不知此中利害!”遝颓道:“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居八九。想不到李掌门如此人物。亦有此烦恼。”李囬妟笑道:“没有烦恼,岂不是神仙了?”遝颓道:“那日雨夜之前,遝颓便不知世间之苦。”,不知想到了甚么,李囬妟没有接话,良久才道:“要闹,索性便闹大些罢!总归不是你死便是我活。”顿了一下,便道:“传书各总领处,对于境内华山派下属帮派,限时剿灭之,各总领处境内,凡与华山派有牵扯之人众、帮派、商帮,限时厘清与华山派之界限,否则衡山派一律以华山派论处。”遝颓吃了一惊,却没有说甚么,按着李囬妟的意思写好了帛书,李囬妟用了印,遝颓便飞鸽传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