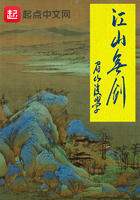遝颓正要答话,却见父亲背后一剑刺来,惊叫道:“小心……”蔡夗偢微微一笑,右手从左颈环过,食指和拇指轻飘飘的就捏住了剑尖,已是离后颈不过一寸距离,力道角度分毫不差,当真是妙到巅峰。沉声道:“万帮主,且容蔡某吩咐下身后事,尔后要杀要剐,悉听尊便。”这一剑事先无半分预警,实是不折不扣的偷袭,那万帮主师出华山派,在昌邑国开帮立派,江湖上亦颇有几分名声,全力之下,长剑竟在对方两指之间不能动弹半分,他和蔡夗偢原无仇怨,只是想帮师门尽几分力,但自知武功相差太远,便立即撒手退了下去。
蔡夗偢这手神功一露,各大派尽皆骇然,皆想:“果真群起而攻之,这场上泰半之人难保性命。”一时间,人人都生了怯意,叫嚣声、骂喊声都停了下来,场中一片寂静。就连李囬妟亦想:“这指力虽不易,自己自信亦能做到,但仅听长剑破空之声就能断出何门何派何人,实是有些匪夷所思,非自己所能。”蔡夗偢原本是来做了断的,担心是一上场便起争斗,便有意显露武功,又申明愿意伏诛,软硬兼施,方才有如此场面,但知平静时刻不会太久,便对遝颓道:“这是你我父子相聚的最后时光了。”遝颓看着父亲,不过数月间,却仿佛苍老了十年,两鬓上已有了些许白发,以前竟未注意,不知是早就有了的,还是最近才生出的。亦不知道如何答话,怔怔的只管掉眼泪。
蔡夗偢见状,沉声道:“男人的眼泪是不值钱的。往后,莫要再如此了。”遝颓擦干眼泪,道:“知道了。”蔡夗偢点点头,道:“时间不多了,交代你几件事情,你只管听,只管照做,不要问为甚么。”遝颓知道父亲脾性,说话从无更改,更何况是此时此刻,便道:“孩儿一定照父亲吩咐。”蔡夗偢道:“第一件,不要去寻剰膤,第二件,不要有报仇的念头。”遝颓心念急闪:“父亲要我不要寻仇尚可理解,但为甚么不让找妹妹?”心中虽是疑惑,但遝颓坚信父亲所做的,必定是有益于剰膤的,便道:“孩儿定然恪守不渝。”
蔡夗偢对于遝颓这点是一直很欣赏的,点点头,道:“去吧,好好照顾李师父,这里的事情和你无干系了。”遝颓心下凄然,恭恭敬敬的磕了几个头,道:“孩儿谨遵教诲,不负父亲苦心。”便即回到了衡山派中。蔡夗偢看着遝颓,冷静的仿佛旁人的的遭遇一般,蓦地想起:“这还是那个自己眼中懦弱敏感的儿子?”想起年少的自己和此刻的遝颓如出一辙,蔡夗偢心想,自己用性命换儿子一生安稳做平常人的想法,只怕是不能如愿了。但开弓已无回头箭,他无暇细想,便道:“诸位同道,蔡某罪孽,百死莫赎,这些年备受良心煎熬,更不愿让子辈再陷江湖仇愿,因是恩怨蔡某一身当之,甘愿伏诛,但请诸位信守承诺,莫要为难小儿。”
话未落音,早有一人走上场来,却是青城派出尘子。蔡夗偢抱拳做礼道:“道长有礼,没成想道长争了个先。”出尘子却没客套,道:“当年在丈人观,贫道掌门师叔、师伯、师傅、师兄尽皆命丧你手,青城派从此元气大伤,这是宁封真君创派以来未有之大耻辱,贫道若是落于人后,又有何面目面对青城派历代真君。”出尘子平平淡淡的说来,没带半分戾气,却让在场之人听得毛骨损然,蔡夗偢黯然良久,方才道:“道长请便,要杀要剐,蔡某再无二言。”
出尘子摇摇头,道:“拳头上的耻辱,便只能在拳头上讨回来,要你性命何用?”蔡夗偢自是明了,但此刻如何还能和出尘子动手,输了,于己无益,赢了,徒给遝颓留后患。沉吟良久,方才道:“恕蔡某不能从命。”出尘子一声长啸,道;“那便由不得你了。”长剑出鞘,一招“老君一瞥”直刺蔡夗偢眉心,长剑破空之声裹挟着出尘子十分内力,响若龙吟。正是青城派绝技——龙跻剑。相传青城派创派祖师宁封子在青城山修道,黄帝曾向其学习驾驭风云的“龙跻之术”,以此抵御蚩尤的进攻,宁封子便据此将青城剑术唤为龙跻术。出尘子深知蔡夗偢武功,因此一上手便运起全力,使出了龙跻术中威势最强的一招,以期抢夺先机,不料一剑使出,蔡夗偢纹丝未动,恍若不见,出尘子心念直闪,迅即变招,运剑下沉,一招紫气东来,又刺蔡夗偢膻中。蔡夗偢依旧不动如山岳,出尘子剑尖已刺破蔡夗偢衣裳,刚触肌肤,便戛然而止。这一下举重若轻,收放自如,已近巅峰,场中喝彩之声如雷。出尘子收剑回鞘,森然道:“贫道微末之技,不入你之法眼么?”
蔡夗偢道:“道长言重了。青城龙跻术,轻灵飘逸,又不失沉稳,江湖之中,再无其它剑术与之比肩。方才道长小试,神形兼备,龙跻术之精髓,道长十得其七,已胜青城前辈多矣,蔡某岂敢轻漫?”这话既赞了青城派,又捧了出尘子,若是旁人说出来,不免有须臾拍马之嫌,但出自蔡夗偢之口,出尘子颜色大好,道:“既如此,接招便是。”
蔡夗偢又是摇摇头,道:“蔡某将死之人,心力交瘁,道长胜之不武,败之何如?”出尘子心念一动,暗道:“此言倒是颇有几分道理,十数年声名,一招不慎,就是毁于一旦。”心下颇有悔意,口中却道:“于情于理,贫道都无退缩之理。言似决绝,实却松动,蔡夗偢心中大是不屑,却不敢流露半分,道:“蔡某连杀妻之仇都弃之不顾,五入仇家,次次皆隐忍未发,只为不给子女生事端,留后患,此间苦衷,万望道长体谅。”言罢,运起内力倒施,全身经脉尽毁,一口鲜血喷出,仰天便倒。出尘子忙上前探了一下脉息,便知神仙亦难救了,叹道:“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心中却着实松了口气,蔡夗偢如此武功,自己胜算甚微。便即朗声道:“蔡夗偢自断经脉,生死已定,诸位恩怨自了罢。”场中之人都是刀头舔血,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过来的,这等血腥是日日要经历的,早就习以为常,除了一些成名人物顾及身份,其余之人早就涌上场中,将蔡夗偢围了个水泄不通。
蔡夗偢虚弱的躺在地上,看着四周仇恨的眼睛,不由自主的苦笑了一下,艰难道:“诸位稍候片刻。”从怀中取出一卷帛书,道:“蔡某毕生武学,亦算颇有小成,只恨误入歧途,贻害江湖。现下将所学录于此书,周之于众,诸位若不嫌弃,习之应有裨益。虽说是明珠弹雀,但亦聊胜于无,稍补我心之所愧。”众人面面相觊,皆想:“甚么嫌弃不嫌弃,场上泰半之人不就奔着这个来的吗?只没成想得来如此轻易。”
只是虽是人人垂涎,但谁亦不敢第一个伸手,此等情形,只怕伸手便死,众人都是心知肚明,各自思量。蔡夗偢又从怀中取出一卷帛书,道:“此间所书,乃是匈奴人此次来袭之原因,烦请转于衡山派,请李掌门定夺。”勉力说完,已是奄奄一息,远远的看了一眼遝颓,见遝颓朝着自己,弯腰低头,长跪于地,心内大安,道:“诸事已了,烦请哪位同人送蔡某一程,不胜感激。”场中又是一片静寂,不知是何原因,无人动手,倒是出尘子见蔡夗偢惨状,动了恻隐之心,道:“恩怨既了,便由贫道来罢。”蔡夗偢长舒口氣,道:“道长慈悲。”出尘子和什一礼,道了声:“无量天尊。”长剑出鞘,直送入蔡夗偢心脏。蔡夗偢闭上眼睛,轻轻道:“来时无一物,去时情满怀。记得留念处,他生还复来。”恍惚中,年少的妻子笑盈盈的朝自己走来,还是当初第一次相遇时的一袭白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