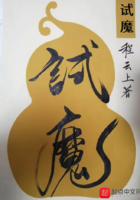再说殷小云一行人。
自瓜洲至句曲山不过百余里,以习武者的足力,若全力施为,便是徒步也不过半日工夫,难处只在于如何渡江。瓜洲埠口倒是停满了大船,可偏偏那里正是两军极力争夺的要冲,只能另寻他法。
好在一路上出逃者甚众,随便拉住几家,便问出了个大概。城外诸铺俱已沦落敌手,北朝不及出战的战船并诸多货船,已尽数焚毁于埠内,可江风山月亭一带沿江私宅中或有船只尚存。众人调整方向,不多时便到了。
昔日人称这江风山月亭,“云移鸟影沈江树,雨带龙腥出海涛”,端的是壮阔非常。只是如今也无人有心欣赏这江淮盛景,前头探路的几人来报,说此处街面已无人,司兵亦不见踪影。待大队来到,也不多言,三两脚踹开一座巨宅大门。顾不得自九曲回廊中绕路,便各自施展轻功跃上房顶。
这其中数殷小云功力最为精深,身形微晃,已窜出十余丈外,先了众人一大截,已到了后院所在。双目一扫,便暗道一声晦气。只见地上只拖着半大老长一根缆绳,想来这家主人料到不对,便匆匆领家眷下人上船,已是逃命去了。便又冲后头吹了声口哨,又挥出个手势,径直往别家去了。彩衣班上下会意,亦紧跟其后。
如此一连数家,总算寻到间空宅。这宅中船虽不大,众人却也勉勉强强可以挤下,便匆匆整顿行囊,预备出发。
只是正在此时,前院忽地响起声音,原是一队南兵见院门洞开,四下无人,便一路进来,预备为自己谋一点好处。不想举刀冲到后院,正与彩衣班众人面面相觑。见人群中男女老幼皆有,以为是宅子的主人家,恐图谋败露,便互相交换了眼神,个个目露凶光,俯身,举刀,一步步逼过来。
殷小云闭眼暗叹一声:你们时运不佳,怪不得旁人。吩咐道:“莫理他们,我来处置。”话音未落,已一纵身飘了过去。那些兵卒只觉人群中窜出个人影,快得简直看不清,心中骇然。只来得及把手腕往回抽了一点,又眼前一花,脖颈处已浮起一条淡淡的血线,先是渗出些血珠,渐渐又飙出血来。手中长刀当啷落了地。他们胡乱捂住伤口,喉中咕噜了几声,血又止不住地从指缝里涌出来,终于支撑不住,仆倒了一地。
再看殷小云,连气也不曾喘上一声,只是抽出方手帕,把簪子细细地擦了干净。正有人高声喊道:“班主,好啦!”闻声便跃回船上,“走。”当下有人斩断船缆,支起长杆点向岸头,内力一吐,船只震动,如离弦箭一般朝江中荡去。
彩衣班中人各有所擅长,亦不乏行船的好手,渡江也算妥帖。只是那楚待霄却一路愁容不展。殷小云天资聪颖,如何看不透她的心思,见已暂时离了危险,有些喘息的工夫,便走到她身旁道:“妹妹可是感觉对不住那些枉死的军卒?”
楚待霄点点头:“是。我随我师傅习练武艺十二载有余,他常对我说:‘我这一生偷盗无数,却不曾害了一人性命,不曾行过一件不义之事。盗亦有盗的规矩。’我也从未见他出手伤人。”
殷小云温言劝道:“盗帅风流,人皆仰望。只是你也瞧见方才那模样,若我等是寻常人家,顷刻间就得做他们刀下之鬼。便是我不动手,只怕这邻舍里也难免有人遭他们毒手。”
楚待霄只是闷闷地应道:“我亦明白这个道理,怪不得姐姐,只是……”便不多言语。
殷小云只道她这般金枝玉叶,不曾见识战场凶险,头一遭遇见这般难免长吁短叹,便放她独自安静去。又走到掌舵者近旁问道:“过江还需多久?”
“这才连江心还未到呢。”
好事的围在船舷旁,数着江中漂过来的战船残骸,见殷小云走近,连忙报道:“已见挂北朝旗号的三十有七,南朝只七艘,桅杆折断辨不清楚的约有四十艘。”
殷小云暗道,昔日南渡之时,康帝把几乎所有水战好手都带过了江去。北人鞍马娴熟,却不谙水性,入主中原不过寥寥十七年,还养不出一支善战的水师。今日一见,果不其然。
又小半刻工夫,掌舵者差人来报:“班主,此番南朝水师尽出,江上巡防想必不多,方便我等靠岸,可也需择定一偏僻岸口停船。黄老二说距……”
“就依他的。”
“是。”
总算未遇上巡江的战船,待泊到一处浅滩,众人便弃了船登岸。眼下距句曲山还有百里,虽屡遭凶险,已是有些疲乏,却还走得动。殷小云便教众人胡乱吃了些干粮,继续赶路。与北岸相较,这一路倒也算平安,全力施展之下,黄昏时分,已到了句曲山下。
这句曲山上清宗坛,依托山势,兴建了所谓“三宫一十二观”。山脚下亦起有山门,来客须得在此通报,获准后方可上山。这是自前朝起便派给各大宗门世家的特权,方圆三十里内,一应事务皆由各派自行约束,除非谋逆,官府俱不得干涉,亦不得征发赋税徭役。也因为如此,这些地方往往会形成集镇,句曲山下也不例外。
各派首领世袭一等公爵,弟子若自愿入朝中或军中任职,皆从优提拔。对穷苦人家而言,若有幸能入宗门,便算脱离了苦海。只是每年道门受箓,佛门受戒,世家中招收外族客卿弟子,规模却有定额,需受朝廷节制。每年人口增减,职务变动,亦要上报,由派驻各世家宗门的理事主办。
却说殷小云一行,备好拜帖,又由楚待霄略作交代,请山门处黄冠代为呈上。彩衣班上下也摆出一副规规矩矩的戏班神态来。等了半个时辰,终于有人来报,言上清派副掌门并盗帅已下山来迎,众人整顿衣裳,敛神屏气,向山门中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