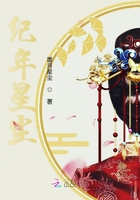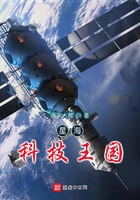月上柳梢。叶若云抱着白狐在崔府中转悠,卓雪幸福的快死过去了。暮春之夜,花香虫鸣,亦有所思所念之人陪在身旁。真特么的是岁月静好,死而无憾了。
崔嘉见苏问并未在府中过夜,心中好奇便去找崔缤问个明白,崔缤摇着扇子道:“我可不像某些人,连女皇的人都敢动。”
崔嘉知道她在说琴女之事,不觉道:“这又不是什么大事,你怎么就咬着不放了?”
“我崔家可还是要脸的。”崔缤道,“至少没人敢在明面上做这样的事。你可知道,为了咱崔家的清誉,我私下托人里把那琴女的家底查了个透,然后又给她白银一白两,告诉她要是别人问起,就说是自己撞伤了脸。”
“不至于吧。”崔嘉道,“这事儿传几天也就没人记得了,那可是一白两白银啊。”
“得了吧您,一白两还不够您一个月花的呢。”崔缤道。
“这不刚停了半年俸禄嘛。”崔嘉小声道。
“重点不在这儿。”崔缤道,“我一查,那丫头的师傅姓乐。昨日女皇让户部查苏问,结果苏问祖上犯了案,就查到了我们大理寺,我和那边官员一聊才知道,苏问的师傅也姓乐,赶了巧,他跟那丫头还是同籍。”
“嘶——”崔嘉倒吸了一口冷气,“他二人可是有些渊源?”
“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便去打探了一下,苏问是过年后进的京,那丫头是一个月前进的京,哥你说他们像不像一个找一个啊。”
“所以你今天把他叫来试探?”
“嗯呐。”
“结果呢?”
“八九不离十。”
“嘶——”崔嘉抚着额头,“你说我算不算得罪了以后女皇身边的大红人。”
崔缤摊着手,“不知道啊,不过我们崔家这么穷,女皇是不可能动的,但是我担心有人飞上了枝头以后携私报复。”
“他要是真敢报复,也算个重情重义的人。”
崔缤一扇子打在崔嘉头上,大声喝到:“你脑袋给我放清楚点!”
崔嘉揉着头道:“这回怎么倒是你想多了,如你所说,既然陛下不会动我们崔家,他苏问出身寒门,就算真有此心,凭他一人之力,能成什么事呢?”
“有道理。”崔缤道,“只是可惜我的玉钗啊,我最喜欢那一支了。”
“你还送他东西?你要是钱多的没处花,救济救济为兄吧。”
“我这不是想着凭郭大人那性子,见他回去的晚肯定要搜身盘问,一旦搜出了我的钗子,肯定是一顿打。两边一对比,他必然会更念着我崔家的好。省的得了势以后天天给陛下吹耳边风,说我们崔家的坏话。”
苏问离了崔府后,并未直接回去郭府。按照崔缤所言,他绕路去了那个名为半日闲的茶楼。茶楼很好找,就在路边。那不是什么奢华幽雅的场所,就是一个普通倒不能再普通的茶楼。门旁还靠着一个穷困潦倒的老道士,他面前放着个破碗,进出的茶客偶尔会扔一两个铜板在碗里,茶楼里,评弹老艺人带着女儿卖艺,正唱道:
“思量起,泪如倾。青鸾彩凤两离分。而今追忆到长生殿,人影衣香七夕盟。”
苏问寻人未得,又闻此曲,心中不免伤怀,暗道:人家还有个七夕长生殿之盟,他们什么都剩不下了。他忽一转念,又道,既然来了京城,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于是转身欲走,靠在门上乞讨的道士问了句:“公子找人啊?”
苏问一面拼命告诉自己,回郭府,回郭府,一面鬼使神差的转过身,向着那道士作揖问道:“请问此间可有一个慕姓姑娘?她琴弹得很好。”
“啊,慕姑娘啊,她刚走。”道士抓着头发想了一会儿,“她家在外城,公子沿着这条路往东走就到了。”
苏问放下一锭银子,道是报酬。道士拉着他的衣袖连声道:“谢谢大善人。”
待他走远,茶铺掌柜才慢悠悠地晃过来,向着李游道:“就你话多。”
“那慕姑娘着实可怜。”李游摇摇头,“心中不忍。”
“他们的命运发生了一丢丢变化,可惜,结局未变。”文承眯起眼睛,“你会干涉多少?”
“随缘吧。”李游道。
苏问确实该回郭府了,为了早点回去郭府,他并没有走去外城——他跑着去了。那道士说的地方他大致知道,城中的手工艺人大都住在此处。
他抄近路过去,到的时候,夜已深,各户门窗紧闭,劳作一天的人,都已陷入梦乡。他也不知那慕姓姑娘居于何处,便放缓步伐,四处张望,每路过一户都要在心中怀疑半天。
踌躇间,苏问碰翻了一户人家堆在门外的竹篮,想来是编制竹篮为生。苏问心中一动,他父亲早逝,家中生计全靠他双目失明的母亲,老母亲就是靠着编制竹篮,将他抚养成人。
苏问赶忙弯下腰收拾,身旁出来推门的声音,苏问正欲开口道歉,却听见竹杖得得得连续点在地上,跟着传来一个他熟悉的不能在熟悉的声音。
年迈的老妇人双手抓着竹杖,问道:“谁啊,是归儿回来了吗?”
苏问的眼泪一下子涌了上来,他咬着手臂蹲下身,努力压抑自己抽噎的声音。一双绣着兰草的白色的绣鞋闯入他的眼帘,跟着就有药包落到地上,浅绿色的长裙、白色的半臂,蒙着面纱的女子负着琴,她瘦瘦弱弱地,仿佛一阵风都能把她吹跑。
她站在那儿望着他,双手捂着嘴,泪水沿着眼眶往下流。
老妇人听到动静,循着声音的方向问道:“归儿是你吗?”
她的声音里明显有些慌乱,苏问将食指立在嘴前,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
慕归会意,抹干眼泪,捡起失手落在地上的药包,扶着老妇人柔声道:“阿婆,是我,今天有点事,回来的晚了些,我先扶您进去,您好好休息,我等下还要去药铺拿药,马上就回来。”
苏问在原地立了片刻,见她娘儿俩都进去了,收拾好碰翻的篮子,转身离去。
慕归很快追出来,却寻不到他的身影。夜晚静悄悄的,就像无人来过。慕归又急又气,忽然忆起他身上所穿衣物皆是上等的料子,不是住在这里的人可以负担的起的,心中暗道他一定是往内城去了,便立刻起身往内城追去。
内城与外城的东段以苇江而分,过了一座石拱桥,就到了内城的城门口。苏问心中很乱,他在桥上停了下来,看着月亮在水中的倒影碎了合,合了碎。在看到慕归的那一瞬间,他很清楚的意识到,他回不去了。从他离家进京起,他们就走向了两个不同的世界。
慕归跑得很急,她生怕追不上他。一旦入了内城,阡陌纵横,她可能就再也找不到他了。
她在城门外的桥上看到了他,她大声呼喊着他的名字,她就怕一个不小心,此生便不能相见。她太着急了,以至于脚下一拐摔在地上,不过没关系,至少苏问为此回头了。他跑过来抱起她走到苇江边,把她放在一块还算干净的石头上,伸手就要脱去她鞋袜,想借着月光查看她的伤势。
慕归握住他的手,笑着摇了摇头,道:“我没事。”
“傻笑什么?”苏问板着脸,又生气又心疼,甩开她的手继续去脱她鞋袜,“跑那么急干什么啊?”
“我怕慢了就追不上你了。”慕归说得怯生生的。
苏问抬头,正对上一双狡黠地眸子,苏问失笑,道:“装什么可怜?”
慕归伸手环住他脖颈,笑道:“可怜是装的,但是心情是真的,我真的很害怕。”
苏问垂下眼没有接话,没有回话就代表无法承诺,慕归眼里的期待变为失望。
“我送你回去吧。”苏问道,虽然慕归伤的不重,完全可以自个儿走回去,但他舍不得。
慕归把头转向江面,月华落在她脸上,风从身后吹来,吹起面纱的一角。
苏问慌了神,转而又露出几分狠厉。他轻轻揽着她肩膀,生怕惊到她。“是谁?”
慕归捂着脸噙着泪,她缓缓摇了摇头。
“是谁?”苏问又问了一遍。他神色凶狠,慕归悲伤地摇摇头,说道:“我初来京城时是在一处教坊中卖艺,有天夜晚我不小心撞倒了烛台,跟着摔了一跤,正巧摔在烛台上,就被......”
苏问想查看她脸上的伤势,可慕归用手捂着脸,偏向一旁。这种事,苏问也不好继续坚持。只好爱怜地揉揉她的头发,道:“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可能除了你,就没人愿意娶我了。”慕归捂着脸,蹙着一双柳叶眉,可怜兮兮地望着他。
“我给你一笔钱,然后你可以招赘。”苏问看着她的眼睛,说的十分认真。
慕归失笑,眼泪落了下来:“跟我回去好不好,我们可以去教书,可以去......”
“我送你回去吧。”苏问温柔地道,他抱起她折身往外城走去。慕归没有反抗,她疲惫地靠在他怀里,泪水弄湿了他胸前衣襟。
“要是我想你了,该怎么找你。”慕归问道。
“我会来找你。”苏问回答。
慕归泪水流得更凶,她咬着唇,把头埋在他怀里。
“别害怕,只要我活在这世上一日,便绝不让你受半点委屈。”苏问正色道,慕归没有答话。一路无言。
苏问将她送到门口,他耽搁得时间太久了,他必须赶快回去郭府。慕归看着他转身离开,心中甚是不舍,止了不久得泪又夺眶而出,她从身后抱住他。
“别走,好不好。”
苏问解开她的手,道:“乖,过些时日我再来看你。母亲那边,暂时先瞒着吧。”
她还是没能拦住他。
苏问回去郭府时已是清晨,女皇言身体抱恙,所以未上早朝,郭依依便在家里等着他。苏问一进门便被绑了,脱去上衣,吊在屋檐下打。郭府的仆人从他身上搜出了崔缤给他的玉钗,郭依依接过玉钗看了半天,道:“你不来伺候你正四品的主子,却去爬一个从七品的属官的床,苏公子的行事风格还真是让人猜不透。”
苏问不答,他总不能供出慕归来。郭依依只要和崔缤一通气就知道他并未在崔府中留宿,他一时也编不出像样的谎话,便咬紧牙关硬撑。
“回话啊!”郭依依怒斥。
苏问道:“无话可说。”
郭依依摩挲着手中的莲花玉钗,道:“你看那莲花表面上干净可爱,可实际上根却是埋在烂泥里的,如果不在烂泥里,就没有莲花。”话里话外,分明告诫苏问莫学书生的清高,莫忘他本身烂泥一般的身份。
苏问笑道:“世人皆道,莲者出淤泥而不染,独大人不知?”
郭依依怒起,用力把一直握在手中的莲花玉钗扔进身旁的缸里。那缸里原本种着莲花,可是未到花季,所以水面上只飘着几片小小的叶子。随着玉钗沉入缸底,那几片荷叶迅速枯死。不过在场诸人各想各的心事,也没人注意到这几片小荷叶。
“别以为爬上女皇的床就可以目中无人了,只要我们愿意,重新换个皇帝也未尝不可!”郭依依冷笑一声,给下人吩咐道,“给我狠狠打,别伤到脸就行了,打完洗干净了丢到我房里去。”言罢,她拢拢头发,吃她的早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