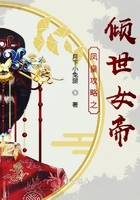朱赫来一度都没有了任何幻想,中央的文件都下来几个月了,可是学校是没有任何反映可言。丫挺的谁都知道这事在上面是千层浪,到了下面就是几片涟漪了。
一天早上,李小曼打我的电话。说要约我出来,我们约好了在咖啡屋见面。见面的时候,我是带着一个笔记本去的。她拿过来我的笔记本,那上面正好有一首我刚写的诗,很长时间以来我都只觉得诗才是离我最近的东西。小时候,我觉得谁都别跟我提钱是最高尚的,但是李小曼却试图告诉我,现在这个时候,谁能拿出钱来谁就是最高尚的。
李小曼低声读了几句诗,那诗是我献给几个老歌手的。已经贴在SOHU上有一段日子了。
献给罗大佑,黑豹,苏芮,伍佰
童年不在了
还有什么会在?
我想去台北的什么路
看那里留给你的记忆还有多少
记得爱人的样子
是否已经衰老
无地自容
冰冷的世界
谁听你的呼唤
只有对远方的向往
在贝司中不再相信什么道理
现在早已不是从前
莫名的寂寞
家乡的老酒
以及对所有的怀念都已经老去
长歌当哭
只有我们彼此相熟
不在乎别人
无奈
还有那个在北欧的梦
美丽的新世界
不管是不是边缘
也不在意她是否能容纳我的毛躁
随意
仍旧嚎叫
一路嚎叫
李小曼读完了诗,以往的时候我都会告诉她再看几遍。这是文人的通病--自恋。李小曼瞧都不正眼看我一眼。她平静地说:“有当朋友见死不救,在这就知道写诗骗小姑娘的吗?”
我说我骗谁了?
她当时像一只亢奋的狮子,随时都要扑过来似的。几乎要喊出来。
“你还是人吗,是朋友你就那么在乎那点钱?”
“我怎么不是人?我就那三千块钱。好,我借他。不,我给他。那他还有六千多块钱怎么办?你给他?”前些年有一个电视剧说是一个学生要失学了,一帮哥们义演集的钱让他继续念书。都他妈的扯淡!哪有那样的好事?我就没看到。那才是最骗人的诗!
李小曼更加激动了,她被我噎得半天没有一句话。
“我自己的小说也不是被毙了吗?我痛苦的时候谁他妈安慰我来了?编辑部天天要青春小说,老子心理年龄测试都他妈过四十的人了,哪还知道什么是青春?我也想有钱,我身边的人有个依靠,那多牛啊,可我不也就是一小人物?天天看编辑脸色写东西?我想认真点当一作家,可是谁他妈在乎我的想法?作家太多了,写他妈几个字就是作家。我就这点钱了,你看能用你就用,不能用上算了。”
李小曼的声音收拢了,气色也平和了许多。“这不是来找你想办法嘛?大家都没主意了。”
我看了看表,已经是快要上课的时间。“下午的课还上吗?”
李小曼看看我,说下午的课没人帮着喊到,没有办法,我们也只能先回去上课了。这节课还是小胖在上面讲传播学。一个人在讲台上喋喋不休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在中文系上课,最无聊的则是写作课,我们的老师会用一节课的时间去讲怎么描写学校的一个广场,然后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写得好。老师不知道,教室里还有一个男生在继续写着中国版的《洪堡的礼物》。当我们在看《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时候,电影的最后,姜文的一句“古伦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一直都在固定的模式中变化着。而我们的所谓的教学改革,也只是把电影中"欧巴"的台词改成了"傻逼”。
而我这首诗呢?应该什么都不是。一瞬间我觉得我自己一度为之奋斗的写作事业竟是那么的做作。它像玩笑一样并不需要我们付出多少真情在上面。当我知道我的事业心也和我的爱情一样变成了无关紧要的搭配时,我就在想,我还能在什么事上认真起来呢?每年秋天的时候,农民们都开始收稻子了。一茬茬的稻子种下去的时候都是苗,收的时候就都是稻子了。可是写文章的人就没那么幸运了,广种薄收的日子太多了。这话说的太片面,有的会赚钱的作家,种几亩的狗尾草,秋天的时候,一帮人也会去田里抢着吃。而你若是个认真的人,不管你施了多少肥在上面,也避免不了青黄不接的结果。
生活上的青黄不接,最多也就是像赵树理写的那样,多点债务,借几石米过日子,或者给地主打几个月的长工。如果命好点,遇上红军进城,债务一下子都清零了,倒也安生。精神上的青黄不接,就是有几分吓人的可怜了。当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人都去狗尾草地里去抢食的时候,才能看出疯狂的所在。写东西真的是太累了,写了两年了,身心俱疲。有的时候,想写点爱情故事吧,写的就是没有人家写的纯。有时候自己做梦也做的和别人不一样,说的梦话也有文学水平。寝室的哥们第二天都会告诉我昨天晚上说什么了,有一句最经典的一定要说:“同样是写婚外情,为什么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琳娜》就成了名著了?”
看来写作终究不是速成的。命运的天平也不是天天就给自己倾斜的。即使出了几个少年作家,被媒体吹得多玄,到底有多大的份量也只有行里边的人能掂量明白。朱赫来曾经问我:“你个大作家怎么考这来了?考哪不比这学校强啊?”
我告诉他,当时一个艺术面试的老师问完我问题后对我说:“我们家缺车。”
我当时一激动就问他:“你要永久还是飞鸽?”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朱赫来当时笑了,他笑我太激动,太容易愤慨。换句话说就是对什么事都太在意了。其实大可不必,我们都不是生活在一个简单的二元世界里的。于是我们也没有理由要求世界简单点。朱赫来就是一个乐于理解的人,而我习惯被别人理解。我知道我天生就不是艺术家,所以来这儿也不觉得多憋屈,在这挺好的,至少这的姑娘天天想的是怎么把自己给打扮漂亮了,而不是想着几十个人脱个干净,裸体排个圈然后说自己是行为艺术。当时有个哥们上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就说了:“知道衣服是干什么的吗?那是冷的时候穿的。这帮姑娘也就是敢在广州那边招摇过世,有能耐三九天到哈尔滨来。咱们这冬泳那好歹还是个挺健康的体育运动,我就不信这帮孙子敢零下三十多度的跑这装亚当夏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