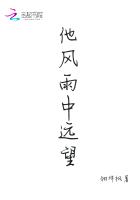剑圣鲁绝的尸体被人发现挂在了洛阳城的城墙上。
起初是一个叫王多的中年守卫发现的,那天他早上准备换岗,刚想回家好好睡上一觉,走了没几步时脸上感觉有水滴落下来,那时他还以为是下雨了,于是用手一摸,定睛一看立时吓了一大跳,这水滴竟然是鲜红色的,王多立刻醒了一大半,再抬头看去,当即吓了个半死,只见一个男人的尸体挂在城墙上,鲜血顺着城墙砖的石壁就流了下来,滴到了他的脸上。
那城墙都被染成了红色。
于是在九月的这个早晨,本应该是寥寥无几的城门口,吸引来了无数人聚众围观,大家纷纷议论开来指指点点,到底是谁有这样的好武艺把人挂在这么高的城墙上,纷纷猜测江湖那些有名有脸的人物,争论不休,便有好心的人提议着把尸体放下来,在野外挖个坑埋了得了。
便在此时一个苍老的声音自人群后面响起:“你们可知道这个人是谁么?”
众人一齐回头望去,只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拄着拐杖在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地搀扶下走了过来,大家立刻静了下来,纷纷上前葛老葛老地叫个不停,那老者也不回应,干咳了两声后又像在自言自语说道:“能将鲁绝挂在这里的人,武功已经不知道有多高了。”
“什么,他是剑圣鲁绝?”
“剑圣鲁绝?是那个铁剑破万里,三十年来纵横江湖无人匹敌的剑圣鲁绝?”
“葛老是见过大世面的,他说是鲁绝那准没错了,你想啊,除了剑圣,谁敢自称鲁绝?”
“我也听说近些年鲁绝很少拔剑,因为他的剑法似乎早已经如入化臻,天下已经没有能匹敌的对手了,那么到底是谁,不仅杀死了他,还把他的尸体挂在这里羞辱?”
说到这里,一群人不寒而栗。
也有人这样说道:“剑圣原来就长这熊样,也没比我好看多少。”
……
一时间众说纷纭,竟没人留意葛老早已经悄然离去。
看热闹的多,胆子大的却没有,把鲁绝挂在这高空中,对方武功如此高,保不准会在某个地方偷偷观察,好事者要是把尸体放下来,保不准会被当成鲁绝的亲人而被斩尽杀绝,于是一时间竟然没人敢与这位昔日的剑圣扯上关系,整整一个上午大家都围在城门口,却没有一个人敢把尸体放下来,江湖人士不敢,之后赶过来的官差不敢,躲在远处指指点点的老百姓则更是不敢。
第一天鲁绝的尸体就挂在那里,血迹已经慢慢干涸了。
第二天鲁绝的尸体依旧挂在那里,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少,而关于凶手的传言众说纷纭,有说是西域魔僧又回来了,也有说是被自己亲弟弟暗算,也有说是被下毒迷倒之后一剑穿心……各种各样的传言笼罩着洛阳,在黑夜来临时候渐渐散去。
第三天鲁绝的尸体不见了,说来也巧,发现这件事的还是那个叫王多的守卫,虽然之前被吓了个半死,但是当班还是要当的,他站在城门口胆战心惊,往日都会深夜时分打个盹,但是这件事发生后想睡都睡不着了,鲁绝的身影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那天晚上他就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随着一声鸡叫声响起,他长长松了一口气,终于可以换班了,他托着疲惫的身躯往家走着,有些时候人总是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虽然他内心对其恐惧无比深,越恐惧却也越好奇,虽然内心一直告诉自己不要回头看,但是走了一百步左右时候还是忍不住回头撇了一眼,这一眼又是让他惊地坐在了地上,久久没有缓过神来。
鲁绝的尸体,真的不见了。
城墙上空空如也,要不是那一行鲜红的血迹,没有人会相信曾经有一具尸体挂在那上面,王多于震惊中苏醒时候,他回想起昨天晚上,自己机会一夜没有睡,连一个盹都没有打,怎么尸体会凭空消失呢,这件事越想越奇怪,到最后,王多起身撒腿就跑,到了家之后也不管妻子询问,打开被子便躺了进去。
于是,第三天,整个洛阳城都知道鲁绝尸体消失了。
各种传言再次在洛阳城中四散,剑圣鲁绝这样一个传奇剑客也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王多是在第四天被官府唤去问话的,官府本来对江湖中事不管不问,但是如今鲁绝尸体被挂在洛阳城墙上确实有损洛阳城脸面,所以洛阳知府等官老爷也是下令要严查此事,王多口中说的经历着实让知府大失所望,一具挂在那么高城墙上的尸体被挪走却没有发出一点声响,这显然不合理,王多却也没有理由撒谎,一切都显得不可思议,想查也无从下手,于是渐渐也就没人再提此事。
炎热夏天的温度还没消散,大家逐渐忘却此事,人总是被新事物所吸引,毕竟,所谓的剑圣也不过一个江湖人士罢了,江湖上打打杀杀本来就多,就算鲁绝是多么绝顶的高手,既然死了,关于他的传闻也就算就算适可而止了,就连当初被吓个半死的王多也恢复了神态,继续站在城门下面,守护着洛阳这个历史悠久的都城和城中日夜操劳的百姓。
于是就这样,日子也还算平稳的过着,边关小小战乱也没影响到这繁华的都城,人们依旧忙忙碌碌,也把大多数事当做笑谈来听。
这一日,本来熙熙攘攘的街道显得更加烦乱,此时距离当初剑圣尸体丢失整整过去了一个月,人们只听见正街上传开阵阵女人哀嚎的声音,于是便纷纷放下手中的事,全都围了上去。
只见一个身着紫衣的女子瘫坐在地上,她衣衫破旧,皮肤黝黑,脸上满是麻点,虽然五官端正,却难和美人二字联系到一起,甚至说还有一些丑陋,头发被一条白色丝巾裹着,裙子沾染了尘土,这女子看上去二十多岁,脸上流着泪水,楚楚可怜的样子。
在她身前是个身材矮小的男人,相貌平庸,看上去三十多岁,身上穿着散发雍容华贵气质的枣红色袍子,鲜艳夺目,一看就是大户人家子弟,只见他趾高气扬地盯着坐在地上的女子,开口便道:
“你跑啊,继续跑啊!蓉蓉,我看你能跑到哪里。”
说完还冷冷笑了几声,声音犹如水中的破锣,沙哑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