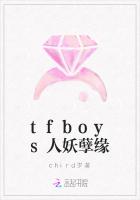热热闹闹的一顿饭,一直吃了两个多小时才散场,吕静静说下午还要陪男友,郭行就在隔壁的包间,饭吃到一半的时候他过来和我们喝了杯酒,打了个招呼。
这两人居然约在一个饭店和各自的友人相聚。
反正寒假还长着,我让她有时间了记得约我,我们一群人就和她挥手告别了。
因为喝了酒,下午大家都不想再学习,于是五个人老规矩,严历家打麻将。
这是我第二次喝酒了,气氛那么好,我也不知道自己喝了多少,但是应该比上次多吧~
刚开始还没什么感觉,到快要散场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可能真的喝多了,因为我眼看着自己的杯子变成了重影儿。
我勉强让自己保持直线的走到了饭店门口。等吕静静和我们告了别,转身回到饭店去之后,在饭店的门口景彦突然抓住了我的手腕,我抬头看了看他,挣了挣手腕,等他松开后,我抬手抓住了他的手腕。
我现在急需要扶着点儿什么东西。抓住之后我就只管跟着他走就是了。
到了严历家之后我就坐在沙发上不起来了。
“要不要喝水?”景彦被我抓着手腕也拉着坐了下来。
他一问喝水,我突然想上厕所。。。。。。于是我松开他的手腕就往卫生间的方向走。
“何汐~你。。。。”景彦在身后喊了我一声。
听他喊我,我解释了一句,“我不喝水,我要上厕所。”
解决了个人问题,我就想找个地方靠一会儿,于是还奔沙发走去,景彦还在那里坐着。
“景彦~就等你了!”乔淼喊道。
“马上来。”景彦答道。
我走过去瘫了下来。
“你有没有事儿?”
我闭着眼说:“我想睡会儿。”
话音刚落就感觉景彦从沙发上站起,接着我的双腿被他抬了起来,拖鞋被摘掉了,我扭了扭身,选了个舒服的姿势,就不动了。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我感觉自己也就翻了个身,就在‘嘭’的一声中躺在了地上。我双手大张,懵然地望着天花,在想自己在哪儿?在干嘛?
愣愣地看着景彦的脸出现在我上方,慢慢放大,,他抄着我的腿弯和后背,把我从地上抱起来放在了沙发上。
当他的手在我的腋下用力收紧的时候,我总算清醒过来。
可是摔下沙发好尴尬,我只好继续装傻,等他把我放在沙发上,我才吐口气坐了起来。
“早知道会这样,之前就该让你进卧室去睡。”景彦站在沙发前,带着点儿训斥,轻声的说。
我低下头,不想提这件丢脸的事儿,景彦也没有再说话。
看他不说话,我向后伸了个懒腰,仰着头问他:“几点了?”
“快四点了,我们打了一小时就散了,他们俩也睡呢。”
“你呢?怎么不去睡?”
“不是很困。”他接着又问:“你睡觉都这么不老实吗?”
“嘿嘿。。。我不知道。”又补充了一句,“不过我妈说是。”
“走吧~我送你回家。明天接着补习。”
“景彦~不能再休息一天吗?”我做哀求状。
“不行,你这补习也算是私人定制了,我还没说累~你再多享受一阵儿吧~”
“春节我得去庆市,等我走了你就解放了。”景彦透露了一个消息。
“啊?你不在齐市过春节啊?”
“从小到大都不在的。都是去庆市姥姥家,亲戚都在那边儿~”
“哦~”我突然有点不希望过年了。
快过春节的时候,景彦走了。
自从我爷爷过世,我家就开始单独过春节了。一时间想起小时候过年的情景,说不出的怀念。那个时候叔叔还没有结婚,姑姑家的表哥表姐们每年都会来齐市,叔叔每年会领着一群孩子在院子中放烟花。
爷爷会乐呵呵地给每个孩子派发压岁钱,妈妈和婶婶一起在厨房油炸各种果子,过年前几天桌上就会随时摆满了好吃的。
可惜时间总是过的太快,一转眼物是人非。有的人去世了,有的人远走他乡,有的人很多年没有再来这座城市,有的人不再是这个家的一份子。
留下这些还在的人,却只能偶尔在记忆中怀念曾经一起过年的他们。
约好年后回来到严历家相聚,小团体就暂时解散了。
我家虽然今年已经搬来了齐市,奶奶也在齐市的小姑姑家,可我们还是会单独过春节。
我父母今年准备摆摊卖一些春联和福字,在小姑姑家药店的外面。
东北的冬天零下20来度,在外面伸出手来两分钟就会吹的通红,冻的僵硬。
他们从腊月二十开始摆摊,像其它卖春联的小贩一样,把套在透明塑料布里的春联和福字用砖头或者碎玻璃压住,免得被寒风吹跑。然后穿得厚厚的,站在寒风中等待过往的行人驻足购买。
哥哥从第一天就开始跟着忙活,我发现放了寒假后,他跑出去鬼混的时候明显变少了,就劝他开学后不要再和张龙峰混到一起,可每次一说,他就急眼,我只得作罢。
我在补习结束的时候跟着去卖半个下午,就被妈妈劝回了家,说是女孩子不抗冻。
我每天白天自己在家做做题,等到下午快要收摊的时候穿的厚实一些去帮忙。
晚饭一直是妈妈回家才做,我不会烧火,家里也没有燃气灶。
日子就这样慢慢的走到了腊月二十九,我又去跟着卖了半个下午,听妈妈的话,穿的特别的厚,可依然挡不住冬日彻骨的寒冷。我坚持到了收摊的时候,和父母兄长一起回了家。
我仿佛就在这十天之中知道了生活的不容易,懂得了父母的艰辛。
腊月三十家家都在忙碌着做好吃的,我的父母还要去摆一上午的摊,哥哥也依然去帮忙了。
我平生第一次一个人揉好了面,剁好了肉和菜,虽然不知道味道调的如何,至少知道放些盐和酱油,一个人包好了饺子,默默的坐在土坑上等待父母哥哥三个人回家吃午饭。
这一刻我深深的明白,我不能帮他们做更多事情的时候,我至少能顺从他们,让他们不为我操心,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去抗起生活的重担。
在这个冬日的午后,我突然就放下了对父亲的一切不满,包括他不让我转科的一点小小怨念。
也许是我和哥哥今年的表现取悦了父母,我们忙忙碌碌的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春节。
春节过后去小姑姑家给奶奶拜了一次年,然后就是哥哥每天又开始不着家的日子,也不知道他都去哪里找谁玩儿,但是偶尔我会闻到他身上的酒味儿。
我觉得父母应该也闻到了,但是或者是因为过年,或许是因为他并没有喝多,所以并没有人来说他。
98年2月,景彦年后回来的时候已经初八了,因为今年过年比较早,开学还要一阵子,我们的补习小团体再次设立。
补习的日子痛苦而充实,一直补到二月二,龙抬头,景彦他们都剪了头发,我跟着他们去了,但是他们都不让我剪。
其实相对来说我更喜欢马尾的长度,夏天可以扎起来,会凉快许多。只是当时被我妈逼着剪成短发后没有耐心再留起来而已,要知道留头发的过程。。。。。。我小学的时候经历过一次,其实并不想再经历。
可当身边的人都阻止我剪头发的时候,我也就顺其自然的接受了留头发的建议。
98年3月1日,开学了。
老爷子宣布4月要体育会考,让大家这一个月多加强体育锻炼。
于是我们的四人羽毛球小分队又开始行动了,因为天气不暖,风也很大,羽毛球自然是打不成的,我们改成了晚饭后,晚自习之前在操场跑步。我拉着景彦,高婷拉着乔淼,四人团体变成了六人团体。
我发现虽然景彦和乔淼两个人平时并不参与各种球类运动,体育课也并不积极,但是两个人还是很能跑的,总结一下,不是不能运动,是懒得运动。
而我平时打羽毛球跑起来还不错,真跑起800米每次都要死要活的。
景彦说我是自找苦吃。
“就因为跑的不好才跑啊!我不努力的话,会考的达标成绩肯定没戏。”
“你跑的时候光张着个嘴大喘气,没跑一会儿就上不来气了,能跑下来就不错了。”
“啊?那不张嘴怎么喘气?”
“你的鼻子是摆设吗?”景彦对我嗤之以鼻。
“我觉得闭着嘴光用鼻子吸的气不够用啊!”我烦恼的很。
“唉~~~那是你肺活量不行。不是不让你用嘴呼吸。把嘴合上一点,与鼻子同时呼吸,深呼吸啊~~”
“哦~”我听是听懂了,但是跑的时候还是总会忘记,于是景彦就开始和我并排跑,监督我。在他的监督下我的800米确实好了许多,至少不会每次跑完喉咙像火烧一样了。
愚人节过后,很快就到了体育会考的这一天,整个高二年级组都集中到了操场上,虽然是分班组在各项轮流进行,但是时间还是很紧张的。
测试的项目有男生1000米跑和女生800米跑,立定跳远、引体向上(男)和一分钟仰卧起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