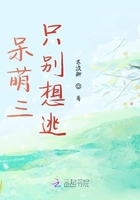“可你明明驻外多年,也不止一次上过战场,为什么非要排斥这个称谓?”
是啊,为什么要排斥?大家的兴趣也被挑了上来,眼睛齐刷刷地看过来。
只是一个瞬间,气氛就有些变了,一段对话变成两股交锋,彼此注视的眼睛里都闪着光。
顾川这才有空去打量面前的这个女人,或者更确切地说,女孩。她绑着高马尾,面容清秀,眉宇之间存着几分稚气,然而咄咄逼人的样子,一点也不可爱。
顾川顿了几秒,刚要张嘴,又听到她说:“我想问的不是这个问题,你可以不用回答。”
顾川拧了拧眉,眸光犀利,凉凉地落在苏童脸上,如同抵着她的一把锋刃:“那你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苏童已经完全放开了:“十一年前的XX战争,你当时率领了四个人的报道组一路奔赴前线,就驻扎在动荡不安的首都,却偏偏在战争正式打响的前两天带领全体成员撤离,乘坐飞机回到了国内,这是为什么?”
“没有战斗,就已经做了逃兵,这是为什么?”一语说完,全场哗然。
时间过去太久,当时引起轰动的一段往事早已被时间洗得褪色。十一年了,十一年前的他们,还不过是有些懵懵懂懂的小学生罢了。
顾川没有想过有一天,当同行们放弃了对他的死缠烂打,却又在一个孩子嘴里重新听到有关这件事的问题。
顾川觉得喉头有点紧:“看来你对我很了解,应该也看过有关于我的采访吧。”
苏童点点头。
“那这个问题,我也已经回答过不止一次了:从当时的形势来看,撤出就是最好的选择。”
苏童却摇头:“这不是回答。”
旁边有人附和,数夏子皓的声音最大:“是啊,这算什么回答!”
顾川已经意兴阑珊,说:“好,今天就到这儿吧。”顾川冲会堂里发蒙的人群挥手,另一只手已经伸进口袋里摸烟了。
他想走,苏童却一把拽住他的胳膊,说:“我还有一个问题呢!”
顾川拧着眉望她,将那只手从身上扒下来:“你说有三个,但我没说一定要听完。”他和她玩文字游戏,急于要脱身。
苏童也顾不得那么多,一只脚往坐凳上一踩,另一只直接踏上桌面,脚一使力,整个人站了上去。
校长老儿背着手站在她面前,仰着头看向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姑娘,气沉丹田地问了句:“你哪个班的?”
苏童脚下一软,往下跳的时候又别了一下,整个人就像软布口袋,一下子全铺在地上。
夏子皓起身来看的时候,苏童正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作孽啊!
苏童到底还是赶上了顾川。和刚开始的某种意气风发不同,此刻摔得灰头土脸,还不停往下滴着鼻血的苏童就有几分落魄的味道了。
顾川正开车门,瞧也不瞧她:“你还挺执着的。”
苏童拉着他的车门,说:“因为你没回答我的问题。”
顾川看着车门上搭着的一只血手,像莹白的玉上溅了朱砂一样。
顾川心里不是不生气的,然而半支烟压了下去,他冷静了下来,抽了几张纸递过去,摇头道:“我已经回答过,只是不是你心里的答案罢了。”
苏童接过纸,匆忙说了声“谢谢”,按在湿漉漉的鼻子下头。
顾川正好把车门关起来,发动车子,一踩油门就走。
苏童这才反应过来,追着车子,大喊:“顾川!”
顾川夹着烟的手搁在窗户外,朝她挥了挥。
顾川沉寂多年,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重回世人眼前,再次和一众国际政治狗血八卦抢夺版面,靠的不是爱岗敬业,而是在那一场大学校园里发生的不堪闹剧。
顾川心一塞,攥着左拳,狠狠捶了下桌子——没留神磕到了他的宝贝手表——呵,他的心更塞了。
尘封这么多年的往事一旦被重新提起,热度之高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神秘,莫测,流血,牺牲,肾上腺素的飙升,人性最深层次的拷问——如果说在和平年代宝贵的平淡生活里,还有什么能激发最原始的好奇,战争绝对是个既不错又沉甸甸的话题。
奔跑在硝烟战火里、血与泪之中的战地记者肩负使命,要将战争的真相告诉世界,他们不是战士却胜似战士。不战斗,就撤退,刺痛的不仅仅是记者的尊严,还有中国人那股永不服输的劲头。但也只有顾川知道,被刺痛的还远远不止这些。
顾川在随后很长的一段日子里忙得不行,应付领导,应付工作,还要应付一个接着一个的采访电话。
“喂,顾记者吗?我是《梨子日报》的记者,想就十一年前的战地采访撤退事件采访您一下,请问您最近有空吗?”
“没空。”
“喂,顾记者吗?”
“不是。”
“喂,顾记者——”
“死了。”
等得罪了一圈人,事情也降下温度,终于得空闲下来的时候,顾川仔细思量,真是不知道该说是自作孽好,还是自作孽好。
反正手脚伸得再长,也怪不到那女孩子身上,这场热闹里,她顶多就算是个打助攻的罢了。叫什么名字来着,苏童还是苏桐?
再一次见面是事情发酵的一个月后。校长给他打电话,把那天“捣乱”的两个罪魁祸首给交代了出来,又说为了表示学校和他本人的歉意,特地订了一桌饭菜来向顾川赔罪。
顾川原本说什么也不肯去,实在架不住他的三请四邀才赴宴,谁知道刚一下车,把钥匙交到泊车小弟手里的时候,就见到了站在霓虹灯下的苏童。
初夏时节,夜风还带着寒意,苏童贪凉穿了条及膝的连衣裙,露出两条笔直的腿。她站在风口上,冷得浑身直打哆嗦,一边打着电话,一边狠狠地跺脚。
她这次没扎头发,长发就那么随意地垂在肩上,鬓角的散发掖在耳朵后头,露出半边清秀的脸,一笑,仿佛从嘴角绽放开一朵花,直漾到弯弯的眼角。
顾川站在原地,忽然一动不能动。
她最终和夏子皓两个人肩并着肩走进了饭店。
哪怕顾川已经猜到这其中的隐情,也还是没能控制住自己的双腿,走进了包厢。包厢里除了校长老儿,果然还有夏子皓和苏童。
校长过来打招呼,说:“孺子可教,这两个孩子哭着吵着要一起来向你道歉,你就大人不记小人过,原谅他们吧。”
顾川没吱声,视线往这房里一掠,最后落在桌边衣衫单薄的这位身上。她正低头专心致志地咬着茶杯,大眼睛往上一翻碰到他的视线,就连忙移了开来。
一餐饭吃得各有心思,上水果的时候,苏童给夏子皓使了一连串的眼色,只差往外下刀子了,还是没能让他放下那片汁甜水又多的哈密瓜。
苏童没了耐心,一把将他拉起来,说:“你过来,我有话和你说。”
两个人像一对闹脾气的小情侣,边闹边走。
校长老儿看得很是羡慕,感叹:“还是年轻点好啊,随心所欲的。”
顾川早放了筷子,正襟危坐地看他,直把人瞧得心底发毛。校长连连告饶:“好好,我承认这顿饭不是我请的,是夏子皓提议的。至于夏子皓是不是听了旁人的话,那我可就真不知道了。”
顾川冷笑:“为了个毛头孩子,你连我都卖了?”
校长讪讪道:“夏子皓这孩子其实是我老朋友家的独子,宝贝得不行,他这次借着他爸爸的面子好容易和我张一次口,你说我能拒绝吗?而且,人家孩子是真心实意想和你道歉的,你就给他们一个机会呗。”
顾川点了根烟,笑着摇头。
老头子又道:“我听夏子皓说,那女孩子一直挺崇拜你的,从小就拿你当偶像。这次纯粹是爱之深恨之切,看到你的新闻都着急坏了。”
顾川吐出口烟,被熏得微微眯起眼睛,笑着问道:“老师,以前没发现你这么会帮人游说啊。”
老头子笑起来:“真心的,真心的。”又忽然想到什么,凑近他,压低声音道,“顾川,你有没有觉得苏童这丫头挺眼熟的?”
顾川的手指一颤,烟头的灰烬坠到西装上。他连忙将烟叼进嘴里,站起来一边拍衣服,一边说:“我先走了。”
校长没留他。
眼熟,当然眼熟了,夜风将她的头发吹起,丝丝缕缕中露出半张明媚的脸时,他就已经发现了,走神了,吃惊了。顾川深深吸进一口烟,将烟蒂死死按到垃圾桶上的沙盘里。
忽然有人在后面喊他的名字,不大不小,有点发怯,不用转身,她已经走到他面前,打量着他道:“你要走了?”
她乌黑的长发分在两边,衬得一张脸更白更小,顾川垂目看着:“你喊我什么?”
他不低下巴,就显得有几分倨傲,苏童抿了抿唇,迟疑片刻:“顾川。”
顾川说:“小丫头,我比你大得多,又是你前辈,你不用敬语可以,就这么直呼我的名字?”
苏童张了张嘴,决定还是不要争辩,他是名嘴,弯的都能说成直的。
顾川冷哼:“你好像还挺不服气的,你到底属什么的?”
“啊?”
“我问你属相呢。”
苏童觉得话题有点偏:“我属猴的。”
顾川说:“是吗?我还以为你属螃蟹的。”
苏童这次真的服软了:“顾……顾记者,我没想把事搞这么大,我真的只是想问出一个答案而已。”
“那答案对你这么重要?”
苏童歪着头想了想:“我好奇。”
顾川实在有点哭笑不得:“这世界上那么多的不解之谜,你能好奇的太多了,何必要对这件不足挂齿的事牵肠挂肚?”
“不足挂齿?”苏童挑眉,“那你就说啊。”
顾川没空和她说废话,抬脚就走,苏童在后头一路跟着,说:“如果我有一天当了记者,你能不能告诉我答案?”
顾川冷嗤:“你当不当记者关我什么事?”
苏童紧赶了几步停下来,终于没再继续去追。顾川拐过走廊的时候,余光向后又瞄了一眼,她垂头站在走廊中,拿手狠狠抓了抓头发。
苏童后来果真去做了记者,虽然她大学四年成绩优异,但因为学历达不到要求还是没能直接进来社里。于是小丫头曲线救国,选择外驻埃及,呆满了一整年这才被召回国内。
校长和他提起来的时候既是惋惜又是夸赞,那样乱的地方,一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怎么待下来的?真以为转一圈回国就能直接去你们社?
顾川这个人忘性挺大,也不知道怎么的,这次看到苏童之后,就把那些细枝末节的小事都一一想了回来。
肩上忽然被人拍了拍,一个穿蓝褂子的护工从他身边走下来:“先生,你们不能坐在这儿的。”
顾川将烟扔到他手里拿着的簸箕里,说:“好。”他撑着膝盖站起来,抻了抻皱起的西服下摆,苏童还坐在台阶上一动没动。
顾川又拿鞋尖踢了踢她:“还没哭好?”
苏童抹了抹脸,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腿麻了。”
顾川把手伸到她面前,苏童瑟缩了一下,难为情地看着他:“我手上有……鼻涕。”
顾川叹出口气,弯腰一把扯住她的胳膊:“你话怎么这么多。”
苏童像个包袱似的被拉起来,背靠着墙一阵跺脚。顾川等她站稳了,就往楼上走。
苏童忽然在后头喊:“顾川!”
顾川脚步一顿,回头看她:“小丫头,你工作了一年,礼貌还是没学得会。”
苏童笑嘻嘻道:“你怎么知道我工作一年啦?”
顾川皱起眉,再要走的时候,又听见她说:“不如你给我个名片吧,带你电话的那种?”
“为什么?”
她支支吾吾,甩了甩手里的帕子:“等我把这个洗过……呃,干洗过,我还要还给你呢。”
顾川说:“没必要,你自己留着吧。”
苏童还是没死心,在后头喊他:“顾川!”
顾川实在烦了,已经准备要拿名片夹了,却听到她说:“那个问题的答案你什么时候告诉我?”
顾川狠狠瞪过去一眼,一溜烟跑了。
苏童站在楼下叉着腰,哈哈大笑。
进了套间,何正义还在摆弄他的摄像机,老夏坐在一边已经喝了半杯茶。顾川解了西装扣子,坐到沙发上:“刚刚烟瘾犯了,多抽了几支才过来。”
老夏表示理解,何正义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顾川心里纳罕:我解释个屁啊!
苏童这一天过得,又是哭又是笑,精彩得过了头。回程的路上,回归现实,被透支严重的情绪需要休整,歪在车上的时候,她终于安静地阖上眼睛。
下车付钱的时候,苏童给了张整钞没让找,司机心里高兴,话就说得漂亮:“姑娘,你慢点走,仔细看路。”
苏童正摸到腰包里写着夏子皓名字的那张卡片,心情一下子又阴郁起来,拿胳膊肘将车门带起来,说:“好的,谢谢你了。”
等车子走了,她站在原地翻出那卡片看了又看,这字写得笔走龙蛇,过于潇洒了一点,“夏子皓”三个字连成一串,她认了半天。心里有个声音讶异着,这才走了多久啊,就这么陌生了!
大学刚开学那会儿,夏子皓就向苏童表白,苏童起初以为他是纨绔子弟闲着无聊,压根就没理他。谁知道他一坚持就是四年,期间各种死缠烂打还着实挺让人意外的。
知道苏童崇拜顾川,他花了大价钱从他发小的邻居的朋友的女友那搞了两张票,其实自己一点不感兴趣,和她一起坐着听顾川演讲的时候,呼噜声打得能把房顶掀了。
她答辩刚一结束,拎着箱子就去了机场,他又不知道从哪儿得了消息,风尘仆仆地赶过来,二话没说就把她搂进怀里,怒斥“你这个人太没有良心了,来也不说一声,走也不说一声”。
大概是离国的愁绪影响了苏童,放平时腻都腻死的情节,在那一刻居然没有立刻推开他。她把头枕在这个年轻男孩的肩头,闻到他身上暖洋洋的薄荷气味。
夏子皓的声音沉闷:“我追了你那么久,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才行。”
“什么说法?”
“至少给我点希望,来日方长什么的啊!”
苏童噘着嘴从他怀抱里走出来,他脸上的失望都显而易见了。她不知道怎么的心里一动,说:“我这趟出去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你要是能等我回来,我就给你个来日方长。”
方才还垂头丧气的夏子皓一下子蹦了起来,像个小孩子一样又是跳又是笑,将她送进安检口的时候连连飞吻,大声说:“我会在这儿等你的,苏童,我会给你打电话的,给你寄好吃的,粽子行不行,你爱吃甜的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