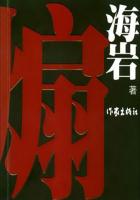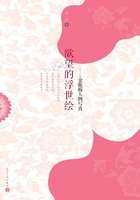获奖者:若泽·萨拉马戈(José Saramago,1922—2010),葡萄牙记者、作家。
获奖理由:由于他那极富想象力、同情心和颇有反讽意味的作品,我们得以反复重温那一段难以捉摸的历史。
获奖作品:《修道院纪事》(小说)。
诺贝尔文学奖是世界上至高无上的奖项,影响巨大,引起全世界的关注。每年10月第一个星期四下午1时多,是诺奖公布时刻,在这之前,各种有关该奖花落谁家的猜测纷纷扬扬。比如1997年,人们预测若泽·萨拉马戈最有希望,结果诺奖桂冠由达里奥·福摘走。这次萨拉马戈的呼声很高。但就在诺奖公布之前,正在参加法兰克福书展的萨拉马戈,不听出版商让他少安毋躁、在此静候的劝告,执意到机场打道回府。他把行李办了托运,偏偏机场的广播里传出他获诺奖的消息,出版商请他无论如何回到书展,那里已为他准备了一个盛大的记者招待会,香槟酒和玫瑰花正等待着他。听罢,这位七十六岁高龄的老人对这期待已久却不期而至的荣耀,还是有些吃惊。
他知道,瑞典文学院将此殊荣颁给第一位葡萄牙作家,不仅是自己的荣耀,也是葡萄牙国家和文学的荣耀,还是世界两亿多葡萄牙语人的荣耀。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萨拉马戈对此做了充分的表达。此刻,葡萄牙举国狂欢,葡萄牙语世界也是兴高采烈,连在政治上与其对立的总统和总理也都将他当成一位民族英雄来祝贺。
巴西报纸感慨良多地写道:“好不容易等了六百年,葡萄牙语终于得到了公正对待。”
为萨拉马戈带来如许荣耀的是他发表于1982年的长篇小说《修道院纪事》。
这部小说以1730年建在里斯本的著名大修道院为背景,通过两个虚构的人物巴尔塔萨尔和布里蒙达,将建造修道院和制作“大鸟”两个工程扭结在一起,描写人的理性和感情的冲突及人对不朽荣耀的追求,征服世界的欲望和幻想。
18世纪初,没有子嗣的葡萄牙国王若奥五世,向大主教许下诺言,倘若能让他生儿育女,他不惜斥巨资修建马芙拉修道院。天遂人愿,国王真的有了儿子。为了还愿,他不顾国库亏空,修造了规模比设想大了几倍的马芙拉修道院。
神父洛伦索,是一个梦想飞上天的飞行器设计者,有个助手叫巴尔塔萨尔,在战争中失去了左手。他离开军队回家的路上,目睹各地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对国王十分愤怒。后来,巴尔塔萨尔与有特异功能的女士布里蒙达邂逅,产生爱情。神父洛伦索帮助二人举行了婚礼,并邀二人帮助他制造飞行器。
制造飞行器在宗教裁判所看来,是非法的,于是派员将神父洛伦索抓去审讯。布里蒙达利用特异神功,助神父飞上天。扶摇天上,俯视大地,人世间种种灾难罪恶,尽收眼底。神父不知所终,巴尔塔萨尔继续修造飞行器,终于有一天,不小心触动机关,布翼飞行器竟带着他飞上了天。
布里蒙达不顾千辛万苦,千里寻找丈夫。结果她看到了让她肝肠寸断的一幕:宗教裁判所正在处死几个“罪犯”,巴尔塔萨尔正在其中。
巴尔塔萨尔的肉体被焚成灰烬,但其灵魂与布里蒙达紧密融合在一起。
《修道院纪事》通过魔幻现实主义艺术手法以及巴洛克式的奇幻瑰丽风格,充分展现作者的丰富想象能力,歌颂人类意志无坚不摧,揭露专制独裁政体对人的意志的残害。更深刻的是,小说暗示专制独裁压制下,虽然自由意志爆发出惊人的创造力,但这种创造力在特定条件下,会异化为专制意志的奴隶和帮凶。他的小说“说教而不乏同情,理性而充满想象”。
和上届(1997)的意大利剧作家达里奥·福相类似,萨拉马戈一直是个有争议的激进的左派政治作家。获得诺奖后,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毫不忌讳地宣称:“不要忘记,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我是为人民大众写作的。”葡共主席卡瓦拉斯得知其获诺奖时,说这是我们党大喜的日子。1989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但萨拉马戈坚持自己的信仰,不随波逐流,让人肃然起敬。其实,在哲学上,萨拉马戈是个悲剧主义者,在行动上,他又是一个愤世嫉俗的行动派。他曾率国际作家代表团访问巴勒斯坦的领袖阿拉法特,公开批评以色列,他以各种形式挑战国家机器,挑战教会,挑战传统道德。
总之,萨拉马戈是个有良知的进步作家。
若泽·萨拉马戈,降生在葡萄牙南部阿济尼亚加镇一个贫苦的农家,时间是1922年11月16日。后来,他随全家乔迁至首都墨尔本。萨拉马戈十七岁时因经济困难,从中学辍学,走上社会自谋生计,当过工人、绘画员等,直到1960年才在科尔出版社谋得编辑一职,后又到新闻日报社任副社长。
1947年,萨拉马戈发表第一篇小说《罪孽之地》。十九年后,他有诗集《可能的诗歌》出版,过四年又有诗集《或许是欢乐》出版。两部诗集,歌颂爱情、大海,表达对人生的热爱和追求,间或批评社会不公。但诗歌对萨拉马戈而言,只是对文学创作的一种摸索和尝试,他的目标是小说。1975年,他的长篇诗体小说《一九九三》出版,似是由诗过渡到小说的实验,充满寓言式的神秘、想象、荒诞。
1976年,萨拉马戈成为职业作家,住在西班牙加利群岛美丽的兰萨罗特岛。在岛上,他又出版了长篇小说《绘图与书法指南》(1977)、短篇小说集《几乎是物体》(1978)和《五种感觉俱全的作诗法》(1979)。接着,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从地上站起来》(1980)问世。可以说,《绘图与书法指南》和《从地上站起来》是萨拉马戈文学生命的真正开始。前者叙述一个人怎么成为艺术家及旅游葡萄牙的感受,后者通过一家祖孙三代人的命运,既表现了他们的勤奋勇敢和真挚的爱情、对劳动生活的热爱,又表现了劳动者悲惨的生活以及他们的觉醒与抗争。后者堪称葡萄牙一个家族的编年史,一部葡萄牙劳动人民斗争的史诗。
瑞典文学院评论这两篇作品时,认为都有明显的自传性成分,为研究者提供了作者本人的生活和思想的宝贵资料。相较而言,对历史反思和对社会不公抨击熔为一炉的《从地上站起来》,思想分量更重,艺术水平更成熟,实为作者小说创作道路上里程碑式的作品。
1984年,萨拉马戈创作了长篇小说《里卡多·雷伊斯死亡之年》。里卡多·雷伊斯是葡萄牙著名诗人帕索瓦诗中想象出的人物。萨拉马戈将这一虚构的雷伊斯放到现实生活中,描写他从巴西回到葡国,与两个姑娘生死之恋的故事,明显带有人类末日寓言色彩。
两年后,萨拉马戈又推出长篇小说《石筏》,讲述了伊比利斯半岛突然与欧洲大陆板块分离,漂向北美新大陆,丧失家园的葡萄牙人惊慌绝望的故事。这是一部具有黑色幽默的警世寓言作品。
1989年,萨拉马戈的长篇小说《里斯本围城记》出版,描写某出版社一名校对员故意大删大改一部关于葡萄牙建国史的书稿,以此与该社女主编调情。又讲述葡萄牙开国元勋阿封索·亨利克斯,怎样在耶稣和“十字军”的支持下,把穆斯林驱赶出境的故事。小说将庄与谐、严肃与轻松两个层面的故事扭结在一起,其风格独特、新鲜。
20世纪90年代以后,萨拉马戈创作仍活跃,先后出版《耶稣基督眼中的福音书》(1992)、《失明症漫画》(1995)、《所有的名字》(1997)和揭露某国右翼政府残暴统治的《透明》(2004)。
萨拉马戈对戏剧创作也有所涉猎,如《夜晚》(1974)、《我用这本书来做什么?》(1980)和《弗朗西斯科·德·阿西斯的第二次生命》(1987),皆表现平平。此外,他还将曾在各报刊发表的随笔、文学评论和时政评论,结集为《这个世界和另外的世界》(1971)、《旅行者的行李》(1973)、《〈里斯本日报〉曾这样认为》(1974)、《札记》(1976)等出版。
萨拉马戈于2010年6月18日,在旅居二十四年的西班牙家中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