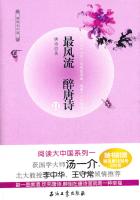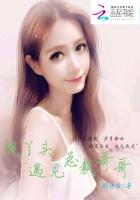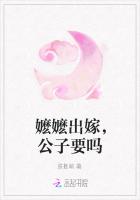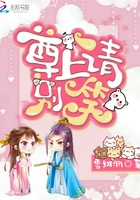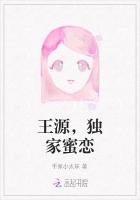20世纪30年代前期,戏曲家、版本学者傅芸子(1902—1948)曾经到日本东京参观过当地的宫廷和私家藏书,他对于静嘉堂文库的记载是:“文库位于岩崎氏之山庄中,乃西式建筑。嘉木繁荫,间以时花,尤饶胜致。库中所藏以吾国归安陆氏皕宋楼故物为主,近年又于其国善本古钞,致力搜求,网罗宏富,有海东‘天一’‘汲古’之目,故吾人来京观书尤不可不一观静嘉堂也。”(《东京观书记·静嘉堂文库》)时距1892年建立静嘉堂文库不到半个世纪。据说,静嘉堂成为日本收藏宋元古本数量最多的一座文库,就是在1907年夏间囊括到陆心源(1838—1894)皕宋楼旧藏以后。
又近半个世纪以后,复旦大学王水照教授在访问位于东京西郊的该文库时,得以一睹陆心源旧藏,且得知每部古籍都被配上了专门从台湾订做的“上等木料所制的书箱”,而“大慰平生渴望,深觉不虚此行”。王教授止不住感慨道:
历史有时真是一个解不开的结。这些珍品流出国外,作为中国人,自然深感痛惜。但当年的皕宋楼,到了陆心源儿子手里,据目击者说,已是“尘风之余,继以狼藉”,大批书籍“用以饱蠹鱼”,处于危殆的边缘了。想不到八十年后在日本却安然无恙,得到精心的保护。幸耶,祸耶?得乎,失乎?我不觉有些惘然起来。
幸祸得失的感慨间,所流露出来的是对日本民族能够珍视中华典籍的欣幸,而同时,也反映出他对皕宋楼遗书被出售时陆氏家族面临的窘境和其时社会背景的失望。“割取书城归舶载”“望赎文姬返汉关”,是当年王仪通为《皕宋楼藏书源流考》所题组诗中的名句,早已熟在人口,也对陆氏后裔构成了巨大的舆论冲击和精神压迫。顷读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潜园遗事——藏书家陆心源生平及其他》一书,深感该书有助于人们更加客观地求解当日“皕宋楼”藏书外售这一近代文化史上的重大公案。
《潜园遗事——藏书家陆心源生平及其他》凡12万字,繁体字排印,全书分为十个单元,卷首印有若干插页(陆心源遗像和时大来札影印件),附录有文献十则。难能可贵的是,该书著者是皕宋楼主人陆心源的玄外孙徐桢基先生。徐先生在《后记》中说:“由于本人非学史者,且对版本、目录、金石均非精通,因而只能以心源公一生学术及事业的业绩为主,兼及其收藏品的收集和变迁、皕宋楼事件,其族人及子孙情况以及潜园住主的演变等。这或许对于一个后裔来说更易落笔。由于写以心源公为主线的家庭情况,因而是书以‘藏书家陆心源生平及其他’为副题,而以心源公所建之潜园的遗事为其名,名曰‘潜园遗事’。”
因此《潜园遗事》并不是一部有关陆心源藏书的研究专著,而是湖州陆氏家族在遭时多故的近现代社会里的兴衰史。“一生简况”“宦海沉浮”“学术成就”“故旧好友”“潜园与戴季陶”“家族简史”“潜园及珍藏品之变迁”……从本书的标题上,即能窥知作者结撰该书的重点所在。
但另一方面,陆心源的垂名后世,毕竟是同他毕生艰苦而辉煌的藏书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作者还是以“建潜园与古物收藏”和“皕宋楼事件”等单元,对陆氏的收藏尤其是其藏书活动做了力所能及的探讨,其中关于震撼时人的“皕宋楼藏书售诸日本事件”的叙述,尤为学术界提供了值得重视的史料。
作者是从“售书前的家庭景况”“售书的经过”“售书过程中的一些活动”“售书后的评论”“八千卷楼藏书的保存——清廷态度的改变”“抗战中陆氏后裔的遭遇”以及“近年情况”等七个方面来加以叙述的。行文中间,不掩过,不溢美,既站在家族的立场,对事件的真相做出实事求是的追忆和必不可少的争辩;又站在民族文化的立场,“对于张元济竭力保存皕宋楼于国内的意愿”和“挽救此书不流入异国”的努力表示感佩,还站在陆氏后裔的立场,对其先辈无奈之下“将书售于日方,从而使我国大量珍贵文物流于异邦”之举,向国人表达了歉疚之意。
我在去年12月,曾经借参加在杭州大学召开的“中国古代藏书楼国际学术研讨会”之便,与同行们共同考察了位于湖州的潜园和历劫幸存的皕宋楼。如今位于月河街旁的居民杂处、楼屋歪斜的皕宋楼,内在格局尚存完好。我随后在《浙江教育报》和《文汇读书周报》上撰文提出,鉴于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的皕宋楼在海内外的广泛知名度和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特殊影响,由当地政府尽快出资修缮旧楼,迁移民户,即把此地建成一处教育子孙后代不忘国耻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又可以布置成为一个当地地方文献的收藏中心。修复后开放的皕宋楼遗址,将对当地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发生有益而久远的影响。而徐桢基先生的《潜园遗事——藏书家陆心源生平及其他》的出版,正可谓适值其时。
(1998年初夏于金陵鼓楼雁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