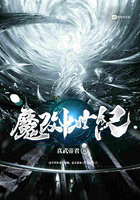沉重的监狱大门缓缓打开,明亮的光线锋利似剑,刺痛了甄惟一的双眼。
她眯起红肿的眼睛,卑微地看向监狱外面的新世界,不敢迈出一步。
“快走吧,门外的人都等不及了。”一位女狱警顺手把她推到门外,“出去以后别再买了,多可惜,你挺好一女孩儿,趁着姿色没卖完,赶紧好好活吧!”
她猛然回头,想对狱警辩解什么,牢门却重重地关闭了。
于是,她就面向牢门僵直地站着,捍卫仅剩的尊严。
倔强地身影久久矗立。
背后的两个人也陪她一起站着,一起等她转身。
她却迟迟不转,因为她也在等,等他们的原谅。
往日的光景恍如一梦,在等待醒来的时间里,变成了想忘也忘不了的记忆。
……
“你一旦在纸上按下手印,就是我的女朋友了,不能反悔!”他的声音尖锐似刀,直刺她的心底。
“嗯,我……已经没有退路了。”她怯生生地呢喃,翘翘的鼻尖渗出凉丝丝的汗珠。
他颤微微地在烙印着黑字的白纸边角处狠狠戳下一圈鲜红的指印。
空洞的眼眸呆呆凝视着这个血红的漩涡,彼此感觉自己正在被它一圈圈地卷进去,整个世界都在不停地旋转,时间仿佛就此沦陷。
“你放心吧,欠你的我加倍还。我的身心都符合处男的标准,没谈过恋爱没破过色戒。只要你不嫌弃,我无偿献身。”心事一平息,他的兴头立刻旺盛起来。
“贱货,你敢卖,我可不敢买。”她水灵灵的大眼睛在骂声之后溢出泪水。
“师姐,你怕了?你平时比我还爷们儿,关键时刻千万不能矫情,万一露馅了……”他见她掉下眼泪,急得像跳墙的狗一样,大声冲她汪汪。
“二小子,我就是被你骗了。我……我想回家。”
岳巍猛地惊醒——原来只是一场梦。
两滴汗珠从他鬓角惊慌坠落。
稍一回神儿,他猛地扭过头,看到肖晓欣正像小猪一样拱在车窗的帘布上憨睡,嘴角的口水摇摇欲坠。他这才放心地瘫靠在座位上,抹掉额头上的冷汗。
他斜着头看她,不禁发笑,嘴角泛出一对深深的酒窝,深得能盛下她酣睡的傻样儿。
火车的汽笛声忽然开始呜咽,疲惫地钻进了黑咕隆咚的山洞。
困乏得像柴草一样的乘客东倒西歪,睡相百出地杂乱成一团。人和物争抢着空间,拥挤着逃出山城的崇山峻岭,已经逃了千里。
乌黑的山洞中,车轮撞击铁轨的声音格外清晰。气流压迫耳膜,渐渐增强的压力仿佛要把耳道冲破。
车厢里冷冷清清,乘客们为翻山越岭的路途默哀许久之后,火车从山洞的嘴里呼啸而出。汽笛又一次高亢地轰鸣,像老马在长嘶,张扬着奔跑的快·感。
黎明前的车厢里温度偏低,空调却依然傻傻地呕吐冷气。
岳巍从包里翻出一件自己的灰色外套,小心翼翼地盖在肖晓欣的身上,轻轻地将衣领掩在她的肩头,顺便轻轻抹掉她嘴角的口水,碍于身边的乘客,他没有闻一闻指尖的口水味道。
在他们对面端坐着一位西装革履的老先生,一直用“媒婆目测姻缘的眼神”盯着岳巍琢磨:“老头儿我真的从现代的感情线上脱轨了?光棍这么多年,现在完全不能理解年轻人的搞对象方式。这小伙子帮这女孩儿提着行李箱坐到我面前,一个劲儿地给这女孩接热水,拿零食,看起来像一对儿娃嘛。他们的话咋就这么少嘞?女孩儿始终冷冰冰,嘿,这傻小子就是喜欢贴冷屁股!”
岳巍敏锐地察觉到老先生炯炯有神的眼睛中流露出嘲讽的光芒,他厚着脸皮挑起眉毛冲他笑笑,眉头的褶皱缝里挤满了稚气和忧愁。
此时此景,他没有心情和一个苍老的路人搭腔,谦和地别过头看向火车窗外退后的风景。
终于,铁轨上蜿蜒的长影晃晃荡荡地从黑夜穿行到黎明,远处驼背的山丘悄然露面。
夜色还未褪尽,行走之中的模糊景色让人浮想联翩。以往坐在千里归程的火车上,岳巍都会沉浸在这道富有幻想色彩的风景线上,带着享受的心情等待清晨第一缕阳光刺过窗帘落在眼底。一想到火车的终点就是熟悉又亲切的家乡,那股亲切的劲头让他的心情像沸腾的水一样翻涌。
但这次回家,他的心情只是一锅冷水,颠簸一路,怎么也沸腾不起来,是不是因为他这次回家多带了一个和自己一起说谎的人吗?良心回答他,或许是吧。
扎眼的阳光钻过车窗,落到肖晓辛的脸庞,明晃晃地流转在薄薄的绒毛上,暖暖的。
他却开始慌张起来。
阳光愈来愈亮,他摊开手掌,看着一团脏兮兮的纸巾,偷偷展开。褶皱纵横的纸面上浸染着血红的模糊字迹。纸上的两朵黑红指印像渐渐晕开的水墨画,打湿了他的双眼。
他侧眼看看沉睡的肖晓欣,然后小心翼翼地擦拭那两朵扎眼的指印,才知道刚刚的噩梦只是一场虚惊。
“你闲得蛋疼啊?看看看,走一路看一路,它是你新媳妇?”肖晓欣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嘶哑地训斥。
他吓得膀胱里憋了一夜的液体差点漏出来,没想到她从梦中惊醒的速度超乎常人,笑眯眯地搪塞:“我对女生的专用生活工具很好奇,总想看看。”
“二小子,你是傻,还是蠢呢?你手里的玩意儿是卫生纸,不是用来垫的。我警告你,别拿着我的纸当卖身契。你再让我见到,我……我立马把它塞进你嘴里!”她揭下身上的灰色外套随手甩到他脸上,忽地站起身,嘴里还在嘟囔“什么癖好”。
“可别呀,卫生纸吃了不卫生!”他慌忙把纸巾揣进怀里,一把钳住她的手腕说。
“你放手,我上厕所正缺卫生纸呢,不放手我就抢……”
他像弹簧一样瞬间从座位上弹起,恭恭敬敬地为她挤开一条如厕的缝隙。
在凌乱的车厢过道上,一位面色枯黄的女人抱着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席地而坐,抱孩子的那双瘦手像榆树皮一样粗糙。她背靠一个泛黄的白色编织袋仰着头张着嘴睡着了,怀里的小家伙也正呼呼地熟睡。
他们是在午夜以后上的火车。乘务人员告诉她,她的火车票是站票,接着就随便在过道上给她找了片空地算是把他们母子安置了。
肖晓欣踮起脚尖轻轻从这对母子身上迈过,生怕扰醒他们。
她艰难地挤过满地狼藉的车厢,钻进狭小的卫生间,从裤兜里掏出一团皱巴巴的卫生巾,解开汗津津的腰带,一边诅咒岳巍一边把可怜的卫生巾垫到底裤中央,再一寸一寸提起藏青色的铅笔裤,小嘴儿依然念叨“二小子,你这个缺货,你就是缺货……”。
不论再怎么埋怨,她还是选择陪他走上了这条路,陪他走到了这里。不论爱与不爱,既然选择了,就不能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