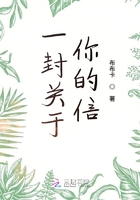现在时间2013年6月24日10:38:14
高考过后,我身上对时间的感觉已经明显钝化。
没有急需达成的目标,没有迫切要紧的任务,唯一要做的就是等待。坐在庭院里的躺椅上,在日光里悠悠的过上一整个下午,日子绵长······
有足够的时间去回忆我整个清透凉薄的学生时代。
————————
当我因为与老师发生口角而踹翻了他的椅子的时候,他指着我的脑门儿赐了我八个字字如针刺的评价“自命不凡,有才无德。”
我一直想不明白,即使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依旧还是想不通。面对一个仅仅十二岁的孩子。他怎么能,怎么能那么精准地看清我的本质。我的脑子里总是混杂着各种想法,以秋季洄游逆流而上的大马哈鱼的数量与之匹敌也绝不为过。
但想把自己的想法付诸与文字,却极为困难。就像你分明吃过这道菜,当别人叫你来做评价,你憋大了脑袋搜刮了整个肠胃,说的也只是不错或者糟糕,这样无聊透顶的文字。
犹如一只足够愚笨的棕熊,张着大嘴,却只能任鱼儿钻进河流,再不复见。
脑袋里分明有一个独立的区域,把好多事情或者经历以类似情绪这样虚无缥缈的形态储存着,任是谁来拿或者你想要去分享都是万万不可的。但要是安静的时候,你若闭上眼睛,那对事物的认知和感觉又慢慢的漫了上来。
姐姐把这一切的力不从心归咎于“没文化。”这我也并不是表示不赞同,某种程度上我也算上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但这里暂且用受过,单方面的输入。因为毕竟我自己也无法在我是否在此种教育中获益的这件事做出肯定的回答。
一段时间我发现自己痴迷于怀旧,因为只要我停止了这种做法,我便开始思考自己为什么活着,这种想法让人变得很焦虑。
小的时候只能从电视里窥探的整个世界,那些一切属于未来的娇嫩和美好,长大了才发现电视剧里并没有生活。
家里有个姐姐,年长我两岁。当我还没有脱离母体的时候,计划生育又查的厉害,若是个女孩就打掉,托了医生检查一下,我是个带把儿的。一出生,我的把儿没了,气的爷爷两天没有吃饭,但说也奇怪,出生了以后倒数爷爷最疼我。
幼儿时期,从车子上摔了下来,摔得是满脸紫红,口鼻流血。一路磕磕绊绊,也算的上是好歹活下来的人口。我与一些伟人本质上没什么区别,就像铅笔芯和钻石。我也只不过是万千俗人中最俗的一个,从小我的口头禅便是,等我长大了···往往后面都加着我的豪言壮语。
现在这口头禅再拿来讲就有些滑稽可笑了,我想是我长大的速度太快了,之后半句豪言壮语还没来得及跟上来。
报考专业和大学并非像选择哪个口味的冰淇淋一样简单草率,但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许是认为自己在那个领域都会大有作为!
只要是财经一类与数字金钱相关,或者磨练口舌,看似聪明人能做的活计全都一股脑儿的报了个遍。
生活从来都不会轻易让我满意。
我与自己理想的大学失之交臂,只能上离家比较近的建筑学校。
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慕达正拿着绿色的食品袋,站在离我不到5米的马路对面呕吐不休。
从他家到我住的镇上,半小时不到的车程,他总能晕车吐个死去活来,恨不得把去年吃进肚子的饭也拿出来呕个便。
6月的焦阳炙烤着地面,蒸发掉空气中的所有水分。
或许,人就是天生优秀,慕达以优异的成绩提前考取了日本的大学。
每一个班级都会有这样的同学,他门门功课优秀,又聪明绝顶。各种奖项拿到手软,老师们对他更是给予厚望。这种普遍性就相当于小学或是初中总是会有一个把校服裤子夹到屁股里的男同学。
从小就自诩聪明绝顶的我,遇到了他也只能退居第二,就连课上睡觉考试也能拿到将近满分,就是这般神仙级出类拔萃的能人,无可挑剔的精英。
长相嘛,大概也就只能在见第一眼的时候,做出“噢噢,原来这神童还能长成这副好模样”这样的评价。
慕达有着所有需要的配置。挺拔的身材,姣好的长相,出类拔萃的能力标配一款天才的脑子。
他出生于本地小有名气的书香门第,母亲是位日本人,长相不祥,年龄更是不得而知,慕达白皙的皮肤就是来源于他的母亲。有听人胡说,这位长辈生前是位艺伎,结交了还是留学生的慕达父亲产下幼子,遭到家人反对,只能一个人留在日本。在相当年轻的时候被客人切了腹,各种稀奇古怪的谣言胡乱造作。
慕达对于身世绝口不提,他从不与人交谈打趣,看人的眼神也寡淡轻薄。
但作为我,他的一切秘密我都抱有一种近乎疯狂的激情,极尽疯狂到越发的模糊不清。他的新奇和陌生感渗透着最原始的渴望,与自我,与他人。像平静生活中的刺点,极度满足了我对世界所寻求的温差,扩大了我生命的维度。
像读一本未译文的书,角角落落里发现奥秘,像翻越一座座陡峭的山峰,荒野。
而对他的感情却只限于探索事物,而并非他本人。
如若将对世间万物的喜爱的程度,付诸于实物,就像是小时候牙膏外壳包装上的牙齿颜色色卡,在固定的范围内,总是有着轻微的变动,有梯度的攀升,从低端到达巅峰。
就像这样说,靠近喜欢的几厘米处,是比较喜欢。靠近不喜欢的几厘米是将就。
但长久以来我发现自己,喜欢和不喜欢的界限变得越来越强烈,以至于中间的过度变成了空白,径直的从这头跳到那头。世界变成了非黑既白,没了任何灰度介于之间的。
慕达处于何种定位,我却不得而知。事物的探索,并非感情的寄托。
他,是我的恋人。
—————————
“离家近些也好。”慕达一见我面就开口说道。
“真好?”我看向他。
对方紧闭嘴唇,点头。
我明显的感觉到我与慕达今后的生活方向会从此刻分开,朝着不同的方向奋力向前。沙在脚下发出干涩的声响,像陷入淤泥,痛苦不堪。
他走路的神情,俨然端坐在神社里的雕像。
眼前一只蜻蜓,如同纸屑一样忽上忽下的飘着。
“去吃饭?”
“嗯。”我点点头。
饭馆的天花板高高挂起,墙上挂着现实主义景致的静物画。每个餐位都被隔成了独立的隔间。
鼻子像童话书女巫一样又尖又大的女侍者抓着一大块面包,一口面包要拿去整整咬二十下才肯吞下。右脸那颗酱紫色的肉痣,似乎跟随着她每一次咀嚼而凭添了一纳米。
一切都如此。
惹人厌烦。
午后,风扇吹拂过的凉爽会转瞬间变为灼热。总觉得日渐笨拙的手脚迟迟跟不上敏捷转瞬即逝的思想。
慕达点了常点的传统套餐,用口哨吹着《卡农》的旋律。向着东南角推开门,清香和鸟鸣便随风吹来。
鸟鸣,此起彼伏……
慕达起身示意要去洗手,门在他身后“喳”的一声关上,旋即一切,悄无声息。
我所能感知的一切,一股脑儿的都被吹到了地球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