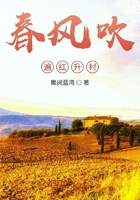其实在这个时空点上说爱情,似乎显得不伦不类,但事实却是如此令人匪夷所思!俞香兰那张粉嫩的小脸蛋,倾刻间幻化成奇异的烙印,深深地嵌在俞大明的脑海里。
那一年俞大明仅十三岁!
当然,对于三岁的俞香兰而言,尚不懂得展示“梨花带雨春带泪“的娇媚泣相,十三岁的年龄亦不足以可解风情,却毫不影响那份执拗而美好的情愫在俞大明的心中播下了种子!
俞大明在许多年后对俞香兰说:“那一天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是我的女人,不管我走出去多远,我一定会回来娶你,而我也一直相信你一定会在等我!“
这种老套的剧情在当代人的眼里,必定是个笑不起来的笑话。但俞大明在说这话的时候真的是倾注了满腔的柔情和斩钉截铁的决心。俞香兰不敢相信地瞪大了她那双妩媚的眼晴,像是受了莫大的惊吓,无比诧异于他的自信,更无比诧异于他俨然文化人的口吻,以及他那不可思议的近似文化人的浪漫!
无意的“艳遇“成了俞大明的青春期里成熟的催发剂。放下可爱又娇美的小俞香兰后,他远远地看了看哥哥和自己的土垒屋,打消了进家门的念头,毅然决然地又回到了他的革命队伍。俞大明这次更为笃定地相信,只要勇往向前,他的生命就会有不一样的际遇。
紧接着的日子对俞香兰来说,却有着许多模糊的悲伤。从父母沉重的叹息和压抑的啜泣声中,她清楚地明白自己的四个兄弟姐妹在年幼中夭折。成长的日子显得有些战战兢兢,但在她逐渐长成的岁月中,又的的确确比同龄人幸福一一一个乡村女娃上了学堂。
学堂就设在邻村,在通往学堂的乡野小路上,活蹦乱窜的田蛙和山蛇,不时地令她惊魂,但有了亲哥哥的保驾护航,这位村姑娘丢弃不了娇滴滴、羞却却的模样。邻家的丫头们提着裤腿踩泥土,扯着尖嗓子呼兄唤弟,甚至开口爆粗咒骂,都不是俞香兰干过的活儿。
母爱是那些密密麻麻的针脚,父爱是不曾遇见的喝斥。她的衣裳是母亲叶芙槿亲手裁剪的,颈边的盘扣精致而整齐,那些不离手的书册更是点缀了她身上特别的味道。
如果说俞香兰称不上大家闺秀,但一定是人见羡钦的小家碧玉。只是隔着袅袅的水烟枪喷出的烟雾,父母的脸庞却显得有些陌生和神秘。她有时极度渴望被父母拥在怀中呵护和逗趣,但这是一种奢望。即使叶芙槿一直是个温柔的母亲,可留在俞香兰童年的记忆里,很难拼凑出几张母女亲昵的片段。
在外人羡慕称道的家庭里,俞香兰却是一枝独自生长独自绽放的花朵。在花季年华之际,俞香兰出落成了邻近几个村落里公认的第一美女。
而俞大明做为一名通讯员,此时已踏上了那个时代的革命解放征程!
福宁县在迎来新中国的革命史上,有过屈指可数的几场小战役,死伤了一些人,永没有长江流域和东北大地上的国共两党百万雄师激战的那种轰轰烈烈的悲壮。
但这也是俞大明的幸运!
国共两党相争,华夏兄弟相残,是整个民族之痛,无情的战火使得同胞的尸骨遍野、家庭破碎,并不是每个中国人都愿意直面的惨状。
俞大明做为一名通讯员,没有机会亲自手刃过敌对那一方的任何一员,但他自己倒是挂了点彩。
在猫着身沿着低矮的渠坝匆匆疾行时,一颗流弹擦过他的耳旁,顺便削掉了他的半个耳垂。俞大明分不清这颗子弹是否就来自自己的革命队伍,但他不能将这种事轻易说出口。在捂着淌血的耳朵狂奔了几里路后,终于把福宁人民革命政府的文件送到了目的地。同一时间,也因失血过多瘫软在地上。
俞大明光荣地成为一名活着的英雄!
但他的革命生涯引领者何胥陶却真的死了。
早在海上归隐回来没多久,他就被保安队逮捕,并被枪杀于福宁县城南门外利桥尾,头颅被割下挂在县坪脚下的“久乐天”菜馆楼角。
俞大明在听闻何胥陶死去的那天,特地买了几块光饼,对着长空献祭完后,就着泪,一口一口地啃完了它们。然后对自己说:“这辈子我只忠诚于您的共产主义革命事业!”
1949年新政权诞生的时刻来临时,俞大明虽然年龄不大,但由于经历了抗日和解放战争,最重要的是有过流血的英雄史,理所当然地成为一名革命资历不浅的共产党员,在当地新政府的政府机构组织部中担任了干事一职,是新中国地方政府部门里的最年轻的一名国家干部。他正儿八经地吃上了公家饭。
俞大明没有进过一天学堂,但他拥有足够的学习劲头,可他的文化知识水平依然有限,而一口普通话绝对操出了福宁人特有的水准,不仅仅让人嗅到了浓浓的蕃薯味,更直接混杂着一些可爱的福宁地方话。
最初的福宁县人民政府各部门中,不乏有许多南征北战之士,他们大部份都是来自异乡的革命同志,其中一部份是迄今依然受到敬仰的“南下干部“。俞大明跟这些老前辈们的工作交流,有时就显得颇为吃力。
但我们的新政权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成果,当家做主的也是一群无产者,这么些忙于革命的无产者哪有机会学习文化,俞大明在政府部门里并不是没有文化者的全部,不过只是其一,而他凭着最年轻的优势,独得老干部们的偏爱,他在职场中亦如鱼得水般的酣畅。
????一九五零年的时候,福宁县土改工作全面展开。
俞香兰父亲俞细命的名字赫然出现在被改造的名单之列。
昔日南洋客归来时,用大洋买了十几亩田地,虽然家中平时不请长工,只是农忙时雇佣一两个短工,更多的时候只是他自己一人光着膀子,从日出干到日落。但他还是这个村里少有的家里拥有黄牛耕地的户主之一。
村里那几个长年贫穷得只剩光棍一竿的汉子,红着眼跑到他家里,先把他的黄牛牵了出来,在村里泥巴路上游了几圈,再猴急急地等待用大白纸糊成长长的高帽子,巴着眼等着土改工作组干部将糊好的白高帽戴在俞细命的头上,最好再让他全身蒙上大白纸,让他看起来活像传说中的冥间勾魂使者白无常,顺便还要将他的小脚女人赶着去游大街。
别的村落里已经有人在轰轰烈烈地进行这一场人畜共舞、普天同庆的改革运动。凡是有田地的,全都是剥削贫苦百姓的地主大恶霸,应该得到残酷的批斗和整治。?令这些人失望的是,土改工作组很快地改写了名单,不仅撤掉了俞细命的名字,而且工作组成员还住进了俞细命的家中。
那几个想借机造反的汉子被工作组领导训得迷蒙了方向,一时间找不着东南西北。谁让这些人本就是没有文化的痞子,工作组随便走出一个人,随便说几句话,就能将他们从天上一脚踢进地里。
工作组大干部训话说:“闹什么闹!我们政府是按人头平均分田地的,按俞细命家人头数,他家也要分不少份额的嘛,多出的部份嘛,人家也愿意归公的,他是归侨,知道吗?是爱国归侨,为了我们新中国建立而特地归国的华侨,是替你们这些人先积累田地的爱国华侨!他跟那些地主恶霸不一样,我们政府是有政策保护的!”
那几位想生事的汉子诺诺地不敢再多话。他们本就是孬种,怂得比一般人快。何况同族的叔伯们私下也对他们多多地叮嘱和教诲:分了田地就该及时地欢天喜地,多出的时间和精力要高呼“共产党万岁,新中国万岁!”何苦要去为难同一村里的乡邻?
族里的老人们更说了,天理不容缺德人!这道理就连女人们都知道,落井下石的事可不能多干,干多了小心生儿没屁股眼。
教诲听多了,不管落不落在心里,那些个汉子自是不敢再造次生事。
一夜间,俞细命被传颂为爱国归侨,村里的人也一夜间知道了,原来他的思想进步得让工作组革命人士都表示折服。
村里没有人知道,俞大明与工作组的主要负责人有着过硬的交情,他们曾经是抗日支队的战友,那可是用革命热血铸成的生死友谊。
村里的人更不知道,俞大明是在他的战友前辈跟前,认了俞香兰的父亲是自己的二叔。他憋红着脸先往自己的脸打了俩嘴巴子,然后提出了对二叔进行格外保护的要求。他那张还略显稚嫩的脸蛋充溢的执着和坚韧让他的革命同事震惊不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