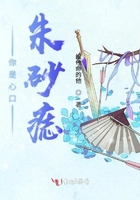俞大明听说俞敏佳仨人回来,忙走了出来,目光一一扫过他们,呆呆地停留在他们的身后。
俞敏俪不敢与他对视,沉默着靠近他。
俞敏涛疚歉地说:“爸,妈没跟我们回来。”
俞大明缓缓地说:“我就知道她不会回来了,只要是她认准的事,她总要一路坚持!”
俞敏俪忍着泪说:“爸,妈为了灵魂而活,为了她以为的不可知世界。她的世界本应慈爱,可她却不知道自己的狠心,她只爱她自己,可她又在虐待自我。”
俞大明:“不!她是爱你的!”
俞敏俪:“不是!她如果爱我,她就不会在大雪天里赶我出门。”
俞大明:“你刚出国的那一年,基金会倒闭了,我们告了状也不管用,你的钱分文都拿不回来。怕你在新西兰那边受苦,她把所有值钱的珠宝首饰都变卖了。她是个要强爱面子的人,可为了凑钱,她把面子舍了,也只有她才干得出来。”
俞敏俪惊怔了许久,一时间追悔莫及,嗑嗑巴巴地说:“我这次又害妈生气了。”
俞大明神情凄迷,:“大家以为我在意失窃的事,别说那首饰盒里没剩什么值钱的东西了,即使有,我也并不心疼东西,我心痛的不过是人情如纸,人心难测。”
俞大明又说:“我只是不习惯了没有她在身边的感觉。你们刚出国时,我也曾经有过一样的不习惯,但这种感觉慢慢地就好了。每个人的一生都要试着学会习惯曾经的不习惯。俪俪以后多打电话回来,给爸讲国外有趣的故事,不许哭鼻子!”
俞敏俪小声说:“爸,我以后就天天给您讲故事,听得您耳朵发腻为止。我已经雕了好多个玉娃娃,我还要雕更多,下次给您带回来,让她们永远陪着您!”
俞大明慈爱地抚了抚她的头,:“我这一生本可以过得无悔无怨,但有一件事却让我怨恨了我自己。当年我不应该怂恿你去书轩的老家奔丧。爸最爱你,却也害了你!”
俞敏俪流着泪水猛摇头,将父亲抱得更紧,:“不是您的错,那是一场意外!”
俞大明努力地挤出笑容,:“我这一辈子认真工作,爱护家庭,最后要学着自己一个人生活。”
俞敏涛等人低头无言。
俞大明示意俞敏俪放开他,然后在沙发上坐了下来,用手指了指,示意俞敏洪几个人也坐下,沉着声说:“今天除了海海外,你们几个都在,有些话我要说给你们听。有位老朋友建议不能说,怕说早了不吉利,但我觉得还是应该尽早跟你们说一说。”
俞大明突然间呼吸急促,发出连串咳嗽声。
俞敏俪连忙为他抚背。
俞敏佳凑往他身边坐下,:“爸,您慢慢说!我们都在认真听!”
俞大明尽力平缓心情后说:“我今天说得认真,以后不再说起,但你们都得给我记牢!我不强求夫妻一起白头到老,更不强求死后共穴。可咱们福宁人不仅讲究名声,还讲究风水。这几年只要混得有点样子的都爱给祖宗造大坟。老家附近的山头上,死人墓造得比活人宅还讲究,但我不喜欢。如果有一天我去了,你们一定要将我火化成灰,再找个僻静的地方撒了它。我是个唯物主义者,只相信一个人断了气就该灰飞烟灭。你们的母亲反正也不会回来了,没有了坟,也就无所谓扫墓,省了你们飞来飞去的麻烦。你们都各自安好吧,记得我今天说的这些话,我死后不占活人的地方,骨灰当肥料最好。”
俞敏洪和俞敏涛顿觉喉头发紧,俞敏佳和俞敏俪又抹起泪来。
外面门铃声突响起,俞敏洪去开了大门,俞建华领了个老汉进来。
俞建华的腋下照旧夹了个公文包,一进屋先朝各位点了点头,再连咳两声,清清嗓子后开口说话:“这是我们村的老汉俞光明,村里的人都叫他三叔。儿子去了英国,女儿一家子在广东开了家补轮胎的店,老婆子也去了广东帮忙带孩子。他家里现在不缺钱,孩子不让他种田,闷憋得难受。我看他是个老实人就领他来了。”
俞敏洪解释说:“大姐和涛涛走时,爸就说妈是断定不会回来的,我就叫建华表哥再帮忙找个人来。”
俞敏涛忙张口叫了几声“三叔”,万分热情招呼他坐下。
俞建华站在厅中央,大声说:“我姑想得开,她潇洒得很,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姑爹想不开,找保姆还得非男的不可,换了别人,不得趁机找个年轻女的侍候着,又不缺这个钱。”
俞敏涛:“一则我爸真在意我妈的感受,二则他本来也是个传统保守的人。其实我们是一心只希望他过得安康快乐,请个人做陪,我们不用为他提心吊胆。”
俞敏洪也说:“是这个意思,我们在国外有工作有家小,回来几天的时间压根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俞敏涛诚恳地说:“我们平时不在国内,总是给亲戚们添了麻烦。”
俞建华摆摆手说:“一家人何必要说俩家话。”
俞敏涛问起俞光明:“三叔,您的儿子常回来吗?英国比日本远得太多,路上要耽搁不少时间。”
俞光明:“他哪里有得回来?几年前偷渡去的,到今天还是个黑户。他头几年忙着赚钱还债,现在状况好了,可也回不来。”
俞建华抢声说:“他平安无事算是造化大,那一年我们福宁人在英国丢了58条人命。”
俞光明心有余悸地说:“是啊,我一想起那种事,至今晚上还会做恶梦。他当时打电话回来哭得一塌糊涂,他说本来以为买一张机票就到了欧洲,然后再坐火车就能到英国。谁知到了那边,一切都由不得他,他只能听人家的,被当成货物那样塞进了货柜。他说他幸亏是早走的一批,迟了几天的那帮人都命丧黄泉。”
俞大明问说:“怎么就舍得让他去?”
俞建华:“三叔跟我一样办养鳖厂亏得精光,后来又大病了一场。他儿子还是个大学毕业生,迫不得已才出国去拼一拼。”
俞大明认真地看了看俞光明,:“你生过大病?看上去身体状态不错,我也没听说过。”
俞光明憨憨地笑了,:“村里那么多事,您哪能都知道。我那时养鳖,因为学艺不精,又时不济人,没赚到钱,但也不欠债。后来没事干就去了外地干上了苦力活。可才过一年多,人不舒服不得不回来,从镇医院医到县城医院,说是胃里长东西,再去了省城医院,最后还是得动手术,手术完还得化疗。老婆子不识字,在医院里侍候不了人,就苦了我儿子一个人。他那时才大学毕业两年,一个月赚三千多,可不够我一天的医药费。外资厂不允许他老请假,他就只好辞了职。我那时真想不开,老婆儿子就天天看着我,怕我寻短见,说我怎么着也才五十出头,阎罗王要是收了我,她们也跟着我去冥王府闹大殿。可我们那时真到了倾家荡产的份上了,想到了卖房卖地。因为我生病,儿子的工作没了,女朋友也没了,一听到有出国的门路,眼睛亮得跟挂了探照灯似的。跟他的姐姐一合计,姐姐就在外头帮他借了三十几万,他就连夜走了。我那时还在做化疗,他到了英国后我才知道。”
俞大明感慨说:“是病不得,一到医院就知道钱够不够。我们有单位的,生病住院还能报销一大部分。”
俞建华:“姑爹,说了您可别生气!我这人口直,也不故意说您!有单位的人还可以领退休金,可没单位的人呢?啥都没有!都是只有两只手两只脚的人,怎么从生到老同一路子,却被划分了三六九等。偷渡的哪几个不是农民的儿子?几个当官和有钱人的孩子去玩这种活?”
俞大明呵呵笑骂说:“你这脑瓜子又犯精了,不知道有贡献的人才有退休金?我当年要是不去供销社,今天的退休金拿得更多。”
俞建华却说得认真,:“阿爸一辈子只当农民,他就没做过贡献?老农民种菜种粮就不是贡献?没有了农民,大家就命好全吃进口的?农民老了不能干活了,他就不算退休?他就该天经地义没有退休金?哎呦喂,越说越生气!哪个官老爷要是能说给老农民退休金,我给他磕头去。”
俞敏涛:“现在没有,总有一天会有的。就像以前没有冰箱空调,可如今这些东西司空见惯一样。”
俞建华:“都有才好!”
他却又话锋一转:“村里的人都在说人这辈子就图养儿防老。老了老了,孩子却都不在身边,再本事又有什么用?人老了,不就希望有人在身边知冷知热,给再多的钱也是没用的,钱再多给也称不上孝顺。”
俞敏洪和俞敏涛等人尴尬得只能点头称是。
俞光明却说:“建华,你这话说过头了。我儿子在国外,靠他的努力,我不欠债了,这张老脸也算保住了。他总说我身体不行,他寄钱养我,体力活再也不让我干。可我不求他给我寄钱,只求他尽快拿到身份安个家,像涛涛他们这样可以正常地来来去去就好。”
俞敏佳端了茶水进来说,:“是我爸爸不想去日本,他要是愿意去的话,每年住上几个月也是好的,省得我们忧心。”
俞建华大眼一瞪,:“出国的人老了都想着要叶落归根,姑爹怎么可能老了反要出国?不如你回来好了。”
俞敏佳苦笑说:“我的爱佳是不需要人照顾了,可轮到给自己攒老本的时候,在东京当售货员比在福宁还是赚得多,我回不来了。”
俞大明忽然想起自己想说未说到的正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你们都听着,我刚刚的话还没交代完,我自己不要骨灰,不要坟地。但海海必须去南洋,好歹去问一问,他义父回唐山的愿望变过没有,因为那也是你们外公的遗愿。我不能不记得,做人要有交待。”
俞大明又开始激动气喘。
俞敏佳搀扶住父亲,心疼说:“爸,您何苦老记挂着这种事?”
俞大明莫名间有了怒意,用力甩开俞敏佳的手,:“你不要总顶撞我!你们都先顺了我,才有资格说孝顺二字!”
大家见他生气,不敢多话。
俞敏涛讨好般说:“爸,我上回参加了全球华人商会,照了一张大合影,我这里还有墨墨凯凯在美国的生活照,我去给您冲洗回来,您平时可以看看。”
俞敏涛下午就捧了许多相片回来,有一张特大尺寸的全球华人商会参与者合影,合影者足有千人,俞敏涛虽在其中,可若不仔细辩认,谁也认不出他来。但在密密麻麻的一堆人中,最前排有位中央领导的面容还是清楚可认。
俞大明捧着大照片看了又看,特意让俞敏涛又去买了大照框,将大合照挂在客厅墙上,就在原先悬挂俞细命和叶芙槿照片的地方。
俞大明坐在厅里,望着相片,笑容满意知足。
俞敏俪望着父亲,心里却酸涩凄楚。
俞光明留下来了,俞家兄弟姐妹们松了一口气。
相聚时短,离别情长。俞大明强颜欢笑地看着他们一个又一个再次离开。
所有人看见了他的假装坚强和快乐,但所有人都无法停下脚步,似乎远方才是他们选择的宿命和归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