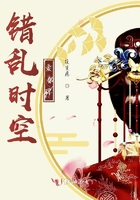俞大明和俞香兰与往常一样正坐在厅里看电视。俞敏俪红肿的双眼将他们震跳起半天高来!
从省城的医院一直到福宁家中,俞敏俪才开口说了第一句话:“爸,妈,我回来了。”随即直接折上楼去。
林书轩垂头丧气地坐回厅里。
俞香兰听完林书轩的述说,失神慌乱地不停在身边搜找她的那串念珠,在茶几上看到了它,一把捏了起来,闭上双眼,急速地捻了起来。
俞大明背着双手不停地来回踱着步,似乎又想在小小的客厅里完成他的万里长征。走了一大段的长征路程后,他开口说:“我们一定要去告那个私立医院,告那个庸医,要替俪俪维权!”
林书轩的心中乱麻成团。
俞大明定定地看向他,:“当时不是说医生的水平一流,医院的设备先进吗?这种资本家开的医院就是满手血淋淋的魔鬼,他们拿患者的健康开玩笑,全是资本主义搞的一套,我们不能纵容这种罪恶,要搜集资料告它!”
俞香兰睁开眼说:“你不要骂资本家了,谁就能保所有患者的安全?要怪就怪我们的话不如人家的话有份量,阿弥佗佛!”
林书轩又是悔恨又是尴尬,却又欲哭无泪。
俞大明又发狠说:“我们彼此间就不说气话了。不管它是阿公医院还是私立医院,都不能就这么算了!当不了妈妈比任何事都残忍。时间也就一年多,不算太久。我明天就跟书轩去那个医院,得找出那时的医疗记录,不能姑息了他们。”
俞香兰手上的佛珠转得更快了。
俞大明背着手依然走他的万里长征路,边走边又大声说:“不能因为熟人关系就放过这种害人不浅的东西。真悔呀!俪俪出了突发事件,又是熟人关系,那时一个字的纸片都没拿,真是愚蠢啊!”
林书轩低着头死命地握紧拳头,闷声说:“爸,明天我一个人去就行,我一定要讨一个公道!”
夜里,俞敏俪瞪着胀痛的双眼彻底失眠,身边的林书轩亦在辗转反侧无眠。
从楼下隐约飘来木鱼的敲打声,忽高忽低,飘浮不定,却声声敲碎夜的宁静。
风儿悄然无踪,霜露无声无息地降临,庭院里的茉莉花不再有纯净诱人的白色,显在枝头上的枯黄色更加风干无力,一缕幽香在露水滴落中渐消渐远。
秋季来了,冬天不会远了,而俞敏俪和林书轩的心情已经走进了严冬,寒冷而寂寥!
林书轩看向黑暗,声音低沉,:“对不起!我没保护好你!”
俞敏俪:“你不需要跟我说对不起,是我们没有保护好我们的孩子,我们对不起那个已经成形却来不及跟我们见面的孩子!”
林书轩弓起身子,将头窝在俞敏俪的身上,如一个受尽委屈的孩子好不容易听到安慰的话语,总算可以为所欲为地尽情抽泣,俞敏俪的泪水再次奔流出眼帘,双眼又一次刺疼。
秋夜里的露水打湿了地面,打湿了整个黑夜,打湿了林书轩和俞敏俪原本幸福的世界。
第二天一早,林书轩包了车直奔向慧星博爱医院,可他傻眼地发现三层楼还是那幢三层楼,广告牌还是那面广告牌,小楼却紧闭大门,外头一张大红纸上写着招租广告。
林书轩照红纸上的号码打了电话,对方大声地回答:“啊,你说那个医院啦?早搬走了,有一个月了吧,搬哪里我哪能知道?……啊?那个广告牌,我这几天就找人拆去。他们明明答应了拆走的,真该死!说话不算话,连里头卫生都不给我搞干净……”
林书轩不等房东说完,掐了电话,回奔去找他的二婶。
林振南的妻子睡眼惺忪,昨夜里麻将桌上输得惨,今早的心情依然不快。她披着宽松的睡袍,摇摆着身子,慵懒地说:“你关心那医院干嘛呢?在那个小破地方哪有什么生意,几个股东拆了伙,各干各的。现如今都要跟一些有点小名气的医院联营合作,直接租人家的科室才能玩得溜。”
“医院以前的病历记录不保存吗?”
“什么记录?你问这个干什么?”二婶孤疑地问。
“如果出了医疗事故,医院就不担责了吗?”
“能出什么事故呀?不都是不敢去阿公医院或是去了治不好的,才来私立医院的,私立医院治不了的再找回阿公医院去。就那几种病,一时半会儿又死不了人,能有什么事故?书轩,你到底问这些做什么?”
林书轩心想在她这里应是无望找寻证据,可又不甘心地问:“二婶,你能告诉我到底那医院只是搬了还是关门了?还有那几个股东,除了你的弟弟,都是些什么人?”
二婶不耐烦地说:“你今天怎么回事?为什么死揪着那医院干什么?关门大吉了!设备家什都拆分了,哪有什么股东?”
林书轩不再说话,铁青了脸色告辞,转而又去了工商局和卫生局,希望能有慧星博爱医院的相关资料,却也一无所获,那不过是一家无照经营而被取缔的私营医院。
俞敏俪刚迈进学校大门,一位同事就紧凑近她,义愤填膺地说:“俞老师,你说气人不?我昨晚督修时间在厕所里跟年段长吵了起来,他竟然搞串联拉人头投票,谁都知道‘先进工作者’就是一张纸,可那张纸对评职称有很关健的加分作用。”
俞敏俪一愣,:“厕所里?”这位同事是位中年女人,而那年段长却是个中年男人。
“没错!我在女厕所听到他们在男厕所里商量投票的事,忍不住就骂了过去,有这么卑鄙的人吗?先进工作者不按业绩和工作态度评分,哪可以拉关系搞小群体?”
一个中年女教师和一个中年男教师在厕所里隔着一堵墙吵架原本是件多么滑稽可笑的事情,可俞敏俪却笑不出来,她正为自己的不幸而伤痛。
女教师又说:“教师评职称又不是驾驶员上马路要礼让三先。”
见俞敏俪不言不语地无反应,她悻悻然地另走一侧。
俞敏俪去到教师办公室里,已有三四位同事在候着上课,可也正交头接耳,她们见她进来并不避嫌,继续愤慨地议论不休。
“有人亲眼见他往领导家送礼,谁都知道他的水平在哪里。”
“哎呀,你没见那个谁最近眉来眼去地尽讨好主任,有人都见他们……,哎呀,大家心里都明白的。”
“写教案照书抄,讲课照本宣科,送个礼就照评职称,认真干嘛呢?”
……
职场是个大舞台,人人都渴望着本色出演,可又有几个不装模作样?利益当前,藏不住的闲言碎语让团结友爱显得虚假龌龊。
上课铃响,大家各归各位。
俞敏俪强打起精神上完课,她无法照本宣科,她也无法参与明争暗斗,不再想回到办公室,踌躇着直接回家。
林书轩正站在校门口等她,俞敏俪见他愤懑而又绝望的样子,小声问:“是不是无法讨公道?”
“医院凭空消失了,所有的东西都没留下。我也找律师问了,被告不存在,想诉讼也告不了。”
俞敏俪悲哀难言,只顾踉跄前行。
偏向西下的太阳将她的身影拉得又细又长,俞敏俪似乎看见前面地上的影子,随她的脚步移动,一路写满了黑暗的讥讽,那一场青春的理想如七彩的泡影无情破灭,曾经叩不开法院的职场大门,难道也该失却一个公民追索公允的基本权利?
林书轩惊恐地看见汗珠如黄豆般大小从俞敏俪的额边莫名地冒出,她的脸色却越来越苍白,上下牙碰撞得咯咯声响。
林书轩紧紧拥住大汗淋漓却又冰冷颤抖的俞敏俪,俩人相偎着回到家中。
俞大明已等得急切,听了林书轩几句话后即破口大骂:“这帮人昧了良心,湮灭了天理,我怎么就不能亲眼看他们的下场?”
俞香兰一见俞敏俪的样子,泪水已直落:“要是妈能代你受这种苦就好了。事实既然无法逆转,不看开也得看开,有几个孩子是来报恩的?”
俞大明又骂了许多难听的话后,只得劝慰说:“海海今天打了电话回来,数他最务实,他让我先取几千块钱给你,说让你去买能让你快乐的一切,钱要是不够再跟他说。我把他的话咀嚼了一遍又一遍,真受了启迪,心里亮堂了许多。养儿不就为了防老吗,你们就去抱养一个吧,以后老了也有人照应!”
林书轩沉吟片刻,:“我今天想了许多,如果我是命中注定无儿无女,那我就认命吧!抱养的是别人家的孩子,不是自己亲生的,我的心里怕也亲不起来,想想就算了吧。妈说得对,想开点,孩子都是讨债的主,当父母的要付出多少心力才能培养好一个孩子,我们把这个心省了,也干脆了当!”
俞大明瞪大眼睛,怀疑地问:“你真有这么高的觉悟吗?”
林书轩斩钉截铁地回答:“我想开了!俪俪才是我一生最重要的人,孩子大了也要离开我们,相伴走到最后的终究只是我们俩个人。”
俞香兰擦干了泪。
俞大明却泪光闪烁,:“想开就好,想开就好,你想开了,你就一定会让俪俪跟着想开,只要她能开心地笑,我和她妈妈就无所求了。”
林书轩一直紧握着俞敏俪的双手,俞敏俪却挣脱开来,一言不发地上楼,拿起了雕刻刀,她突然间宁愿在每一寸光阴都能选择只与寿山石为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