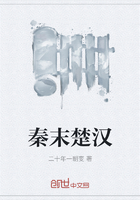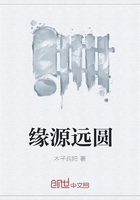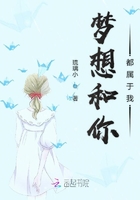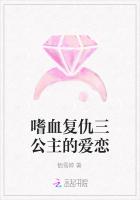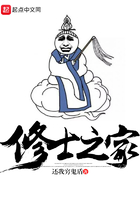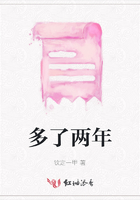饭桌上,缪顺垚已经喝了不少烈酒,脸上通红。
叶锦蓉还有缪梓烟何雨婷三人喝不得酒,喝的是茶水,所以她们倒还好。
反倒是俞冰,虽然酒量还不错,也懂得喝酒,可是才喝了一碗就已经快醉过去了,现如今正趴在桌子上呼呼大睡着,惹得缪梓烟一阵白眼。
“乡试只剩下最后一场了,朝廷现在十分重视策论,你虽然前面两门取得了双榜第一,但是若是策论这关还需重视!”缪顺垚说道。
一般的商人只知道一味追求利益,高级的商人除了追求利益,还要知道当今的政事趋向,避开朝廷所嫌恶的。
像缪顺垚就是高级商人的一份子,虽然是一届商人,但是他对当今朝政以及时事还是有一些了解。
乡试第三场的成绩不仅仅是第三场的成绩,也是一个总成绩,因此在评估的时候,还会考虑到前面两场考试考生的成绩。
若是在策论上存在评价相似的,那么就看前面两门考生成绩如何,又或者是若是策论一般,但是前面两门尚好的,也会予以加分。
但如果是策论一般,前面两门也一般的,那么要么垫底要么直接淘汰。
历年的乡试有着一个铁则,基本在前面两门乡试同时取得甲榜第一的,在策论上基本不会差,能一直笑到最后。
可是杨起却是例外,虽然学习策论有些时日了,也照着抄了许多的策论,可是真要说的话,他的策论水平刚刚入门,又怎么经得起乡试的考核呢。
因此,对于自己第三场策论的考核,他可谓是忧心忡忡,倒不是怕考不上被淘汰,考不上被淘汰倒也还好。
他最担忧的是,自己已经双榜第一,第三场骤然失利甚至没上榜的话,怕是会被贻笑大方,届时怕是整个丰州都会知道自己的嗅名。
没错,是嗅名不是大名。
虽然还有两天时间的准备,但是他不觉得自己还能有什么突破。
现在唯一的希望是,策论的自由之处。
看过超过这么多策论,他也了解到了其中一点。
策论是自由的,哪怕你贬低朝廷斥责天子也不会受到太大的惩罚。
但是若是贬低朝廷斥责天子时若不能给出精彩绝伦的策论观点,那么你的策论成绩可想而知。
因此,最稳妥的办法是,以自己的观点指出其中稍有不足,然后扯出几句古人所言,借此歌颂朝廷,表彰天子,再表现出自己一心为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
说的简单点,就是多拍拍上面的马屁。
如此一来,但凡你的策论还能过眼,有那么几分道理,最终成绩还是会有的,总不至于会被淘汰。
看过这么多的书,杨起自然知道有哪些拍马屁的话可以写,在接下来两天时间里,他一心窝在房间,以过往策论题目为题,写着大量溜须拍马的“策论”!
……
乡试的最后一天还是来了,这一次,缪梓烟,何雨婷,俞冰三人不顾杨起的推辞,还是送他到了贡院外。
看着杨起走入到贡院内,何雨婷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眼中含泪。
“起子哥终于走到了最后一步了!”
俞冰想了想,“对了,如果他在这一场也考了个甲榜第一,那么他会成为什么来着?”
“解元!”缪梓烟道。
其实也未必要考上第一才能成为解元,有前面两场优异的成绩在先,这一场只要发挥的中规中矩就行。
只是,她的脸上满是担忧之色,有点不大乐观。
她是知情人,知道前面两关杨起能过的这么轻松的原因,一来是因为他记性好,学得快,二来他本来就擅长诗词此道。
然而,策论这关是杨起的弱项,她替杨起看过不少他写的策论,要么策论观点过于一般,要么就是差强人意,而且在文章撰写上,很多文笔也把握的不是很好。
想要在策论这关表现良好,最终成为解元,这期间的希望实在是太过于渺茫了。
考场自然还是不变,杨起所在的考场还算不错,还有四十余人。
仅剩四百人余人的考生,十二个考场,少的最可怜的考场只剩下十几人。
等到时间差不多了,考官们就把卷子们分发了下来。
最后一关的策论一共有三道题,每道题的题目在三五个字以内,要围绕这三道题写出一篇文章。
这有点像是写作文,围绕给出的题目写出文章,但是难度比起写作文更加大,也更加严谨。
卷子共有三张,每张一道题。
第一张卷子上的题目是治蝗灾!
蝗灾是古时的最大的自然灾害之一,其恐怖程度堪比洪灾,旱灾等。
洪灾一至,田间大地一片汪洋,农作物都会被淹死;
旱灾一来,地表则是会皲裂开来,作物得不到水源的灌溉,会因干枯而死。
而蝗灾的话,漫天蝗虫所经过之处,寸草不生,别说农作物了,就连一根草都不会给你留下。
至于这三大灾害以外的其他自然灾害,例如什么地震,瘟疫,泥石流之类的,虽然也很恐怖,但是不是很多见。
蝗灾,旱灾,洪灾则不然,每年基本都会发生,而且每次发生的规模都相当的大,其每一次出现,都会威胁到数十万,上百万百姓的生命。
在蝗灾,洪灾,旱灾这三者之中,上至天子高官,下至黎明百姓,最怕的当属蝗灾。
旱灾的话,就算苍天不下雨,也可以事先挖掘出一道沟渠进行人为灌溉,至少能减轻一些压力。
洪灾的话,可以通过休整河道,引流入海,来避免大水淹城,流离失所。
而蝗灾呢,却是很难控制的,蝗虫一到,遮天蔽日,所到之处寸草不生,而且它们数目众多,杀不光,灭不尽。
因此,治蝗灾这一题可以说是相当的难。
一方面如果真有人写出了办法,能够给朝廷分担很大的压力,另一方面就算没有写出办法,也可以通过集思广益,说不定因此能给治蝗灾带来灵感。
现代的话倒是很少发生蝗灾,杨起倒是几乎没有接触过这个问题,不过他倒是看过一些相关的书籍,上面倒是有一些预防蝗灾和处理蝗灾的办法。
说起蝗虫,它们一般喜欢干燥的地方,产卵也是选择干燥裸露的土壤,因此在南方一些多山多水的地方,是没有蝗灾发生的。
北方的话就不一样了,北方大多是是平原地带,水系并不发达,因此基本上年年都有蝗虫为祸。
虽然所处的位面不同,地理位置也大有差异,但是在蝗灾方面上,周国时常发生蝗灾的地方也确实是在北方,南方少有。
杨起整理了一下脑中的记忆,开始在卷子上写了起来。
蝗虫之灾,非不可解,而蝗一出,是灭不之,故惟于蝗,不为祸先将其解决灭杀。欲解决蝗,先知蝗虫之性,蝗虫喜燥,故蝗之时,往往随旱,其卵者也,多在干燥,发露之地……
(蝗虫之灾,并非不可解决,但蝗虫一出,是消灭不了的,因此只有在蝗虫没有为祸之前将其解决灭杀。
想要解决蝗灾,首先要了解蝗虫的习性,蝗虫喜干燥,因此蝗虫出现之时,往往伴随着干旱,其产卵的地方,多在干燥,裸露的地面上。)
写的文章自然是文言文,而不是白话文,为此杨起在写的时候还要先进行转变,费了些时间。
蝗虫喜燥,故北方岁蝗,而南方,如乃无见过何蝗,故解蝗之一也,即为兴修水利。
然光兴修水利亦可,毕竟北源不多,能灌溉所至亦不多,且兴修水利须耗费之力,非一朝一夕可办之。
蝗自喜干燥之地外,犹喜谷,凡小麦,稻米,黍稷之属,如此,可于乏水处不植之,种大豆,果树。
(蝗虫喜干燥,因此北方年年有蝗灾,而南方便没有出现过什么蝗灾,因此解决蝗灾的第一个办法,便是兴修水利。
光兴修水利还是不行,毕竟很多地方都缺水,能灌溉到的地方也不多,而且兴修水利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不是一朝一夕能办好的。
蝗虫除了喜干燥之地外,还喜食谷物,小麦,稻米,高粱之类,如此,可在缺水的地方不种植这些作物,改种大豆,果树。)
写到这,杨起停了停,而后继续往下写。
蝗之虫卵生于燥露之地,北方之地必于冬日将地新,以地中虫卵与死。
然此非能尽灭之,鸡鸭,蝗之甲,使民多养鸡鸭,放于田中,鸡鸭食之地中之虫卵更肥肉重,鸡鸭粪亦可肥地,一举而两得。
此外,非田,而虚燥者,亦当多木,此亦治蝗,非特如此,尚可防沙,及水土失。
(蝗虫产卵于干燥裸露之地,北方之地要在冬日将土地翻新,将土地之中虫卵给冻死。
不过这并不能彻底灭绝它们,鸡鸭是蝗虫的天敌,让百姓多养鸡鸭,放于田中,鸡鸭吃了土地之中的虫卵变得膘肥体重,鸡鸭粪便亦可肥沃土地,一举两得。
除此之外,不是农田,却空旷干燥的地方,也当多种树木,如此也可防治蝗虫,不仅如此,还可以预防风沙,以及水土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