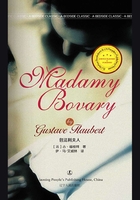一
只见这柄长剑乌色剑鞘,紫铜吞口,黑铁剑身厚重宽大,刃身宽逾两寸。一股苍凉悲壮的逼人杀气,已从剑身之上逼迫出来。
宋江终于也吃了一惊,动容道:“慕容彦达所佩之剑?”
徽宗注视着他,沉声道:“不错。”
他右臂微曲,横握剑柄,缓缓接道:“此剑长四尺五寸,重三十七斤,铸造之时所用的铁中精英来自九州十六府。铸剑师经过千锤百炼,方才炼成了这柄重剑。”
宋江凝视着剑身,轻叹道:“若非如此,它击下之时又怎会如同千柄铁锤同时砸下,凌厉威猛,万夫莫当!”
徽宗目光闪动,亦抚剑叹道:“即便如此,‘重剑慕容’却还是败在你的掌下。”
宋江道:“不错,慕容彦达确为我所杀……陛下自然已得知。”
徽宗鼻中重重地哼了一声,愠道:“慕容彦达身为青州知府,竟自甘堕落去做了高俅手下,也是咎由自取!”
宋江道:“陛下明鉴。”
徽宗的脸色忽已变得说不出的忧虑,缓缓道:“现今高俅身边的‘四使三剑’中,‘追风使’展童、‘落花使’李玉婉与‘飞雪使’许洋都已为你所击败,只剩‘明月使’一人还未曾与你交手……”
他轻轻抚摩着冰冷的剑身,续道:“而林冲也除掉了‘残剑独孤’。那逆臣身边的左膀右臂已去七中之五,只怕再也等不下去,即刻便要发难。他散出‘《九天玄女经》在皇宫艮岳山’的谣言,只怕正是企图制造混乱,乘机图谋……”
宋江微微动容道:“陛下也知《九天玄女经》?”
徽宗扼腕叹道:“朕虽已处处受胁,但耳目却非闭塞。高俅之所以处心积虑隐忍多年,只为获得经书中的宝藏与地图,侵吞天下——朕又怎能让他得逞?”
宋江微喟道:“汴梁此刻群豪聚集,皆为此经而去。陛下虽以郊天为名远离高俅,但只怕皇宫之内现已一片混乱了。”
徽宗切齿道:“那逆臣害朕不浅,只盼公子能助朕一臂之力!”
宋江凝视着他的双眼,一字字道:“陛下自然知道,在下与‘水泊山庄’中的众位兄弟,必定不会坐视其祸国殃民。”
徽宗听他如此一说,面上的欣喜之色已荡漾开来,大声道:“朕在此谢过公子!”
他以天子之尊,要在口中说出一个“谢”字是何等之难,单此一字,已可看出如今他为解决心腹大患,求贤若渴之心实是急不可耐。
宋江谦逊了几句,却见他眉宇间的喜色渐褪,目光中却反倒渐渐露出了一种无法压抑的恐惧之色,不禁问道:“陛下莫非还有担忧之事?”
但见徽宗沉默半晌,终于仰天叹道:“高俅虽险毒,但还有一人却更胜其十倍。此人若不除,我大宋江山必遭灭顶之灾!”
宋江悚然动容道:“此人真有如此厉害……”
他目光闪动,似乎忽然想到什么,双瞳之中渐渐射出逼人的光芒,一字字道:“莫非他就是‘天尊’?”
“天尊”这个两字,仿佛本身已带有一种邪恶的魔力,徽宗听它从宋江口中说出来,脸上立刻就如同被涂了一层死灰色的石膏,就连眼中的神采也变得黯淡而痛苦。
他似连呼吸都已停顿,内心之中的惊惧之意实已无以复加。良久,方才长长吁了一口气,道:“不错……”
他不觉连声音也变得嘶哑而颤抖,说道:“‘天尊’本名方腊,于半年前在浙江青溪突然崛起,其势力之强,扩展速度之快,简直更胜当年魔教百倍……此人座下,竟已网罗了武林中要价最高的刺客、杀手,甚至是不少名门正派的第一把好手。而他的武功更是深不可测,直如妖魔……”
宋江静静地听着,一阵刺骨的寒意不觉也自心底升了起来。只听徽宗又颤声道:“方腊现已在青溪境内造起宝殿宫阙,名为‘欢喜阁’,在睦州、歙州也建有奢侈行宫,连同杭、苏、常、湖、宣、润总共八州,以及嘉兴、松江、海宁等二十五县皆一并暗中侵占。江南八郡实已落在他的手上,其势力飞速扩张,已有独霸天下之势……”
宋江悚然道:“即便陛下无力对抗他的扩张,但高俅的实力也是不容忽视。难道方腊之强,竟然连他也束手无策么?”
徽宗摇首长叹道:“据朕获知,高俅曾多次派座下高手前往青溪行刺,但之后皆是音信全无,生死未卜。直到第十名刺客派出后七天,高俅府内却忽然收到十颗浸泡在酒缸中的头颅。”
宋江击掌叹道:“这十颗头颅,自然便是那十名刺客的。”
徽宗面色如土,低声道:“自此之后,高俅日夜提防,生怕方腊有一天会来取自己的项上人头,就连朕自己,也是,也是……”
他一连说了两个“也是”,竟再也无法说下去,那种深深的恐惧已似一双无形的魔手,将他的咽喉紧紧扼住。
徽宗的神经此刻已如一根绷得太紧太久的弦,若是稍稍再触动一下,只怕立刻就会崩断。宋江凝视着他,忽又展颜一笑道:“如此一来,方腊对高俅却又是一种牵制。高俅之所以迟迟未动,除了还未找到《九天玄女经》之外,这也是一大原因……”
他的笑容中已有了明朗之意:“此二人都欲争夺天下,不论谁强谁弱,相互间也必有重大损伤,陛下却得了渔人之利!”
这番话正是最好的镇静剂,听他如此一讲,徽宗的脸色果然已稍见缓和。
他沉默半晌,心志稍定,缓缓从龙袍袖中抽出一轴纸卷,低声道:“这封密卷……记载的便是有关方腊的片段资料。朕耗银十万,牵动百人,千辛万苦方才搜集得来这一鳞半爪。你……你可要认真看看?”
他的目光眨也不眨地盯着宋江,其中神色含着千钧重任。常人若在这两道沉重目光的注视下,再想起方腊之狠毒,只怕早就吓垮了。
但宋江面上却又已渐渐泛起了那种自信的、永不会屈服的笑容。他霍然道:“好!”
徽宗也不禁微微一愣,沉声道:“你可知:这一看便是接受了铲除方腊之重任?”
宋江含笑道:“在下自然知道。”
二
徽宗脸上终于再次露出喜色,道:“那你是应允了?”
宋江正色道:“是的。”
徽宗大喜道:“多谢!”
宋江淡淡道:“陛下不必道谢——只因在下这一举,并非为陛下而做的。”
徽宗微微一怔,道:“那你是……”
宋江正色截口道:“陛下与在下三次相遇,品茶赋词;弈棋论武;杯酒赏剑,每每以心相交。陛下以天子之尊礼贤下士,确是十分难得……但这些,却还不足以使在下答应陛下的一切要求。”
他眼见徽宗满脸疑惑,沉声续道:“陛下此番更对在下有洞中援手之恩——只不过此情虽重,仍旧不足令在下听命于陛下。”
徽宗脸色阴晴不定,闷声道:“是么?”
宋江正色道:“只因个人之恩情,对于天下大义来说实是微不足道。在下若是为了报恩,便要昧着良心去做伤天害理之事,虽是成全了自己的信义,却会害了无辜的人,实为‘因小节而失大义’。当今世上,这种为了报恩义气而不顾一切行事之人确也不少,在下虽不才,却要将这种愚昧的做法改上一改!”
他以手踞案,复又朗声道:“我之所以答应陛下,只因陛下之要求正是合了天下苍生之大义。若方、高二人反军一起,势必掀起一场浩劫,芸芸百姓受尽涂炭。在下实不愿看到这种情形发生,所以在下答应的其实是我大宋百姓,而并非陛下……”
1
宋江凛然道:“昔日许多忠臣良将明知君主圣旨有误,却依旧不敢有半点违背——只因他们将‘忠于君主’与‘忠于国家’的观念混淆了。须知民大于君,百姓的疾苦、国家的兴旺才最重要。单单一个皇帝,绝不能代表整个国家之利益。所谓‘君受命于天’的说法,正是历代君主为了维护自身统治而编造的谎言!”
他目光灼灼,一字字道:“‘忠君与忠国’的区别,也正在于此。”
徽宗脸色不豫,沉默半晌,终于低声道:“你的说法虽是大逆皇道,但也确有你的道理。朕……记下了。”
宋江站起身来,整容揖了一揖道:“以昔日之作为而言,陛下虽非明君,但却远强于高、方之残忍卑鄙之辈。但愿陛下此后能够痛定思痛,一整朝纲,救民于水火——在下这一揖,正是替天下百姓向陛下作的!”
徽宗沉吟片刻,朗声道:“好,朕答应你。”
宋江缓缓接过那轴宗卷,并不展开,却放入怀中道:“方腊之资料,在下改日必定仔细阅读。”
徽宗道:“朕知你不愿在朝为官,但落雁峰中之珠宝黄金你尽可随便支取。须知对付方、高二人,必须有雄厚财富。”
宋江目光闪动道:“这笔财宝不妨先存于陛下处,待在下真正需要之时,再动用不迟。”
徽宗吃惊道:“你没有财力,行事只怕举步维艰!”
宋江微微一笑道:“在下这里倒还有五千万两银子,想必也可做些事情……”
徽宗脱口道:“五千万两?朕如何不知道?”
宋江含笑道:“陛下对宋江的底细,都是一清二楚的么?”
徽宗自觉失言,脸上微微一窘,沉吟半晌方自缓缓道:“自浔阳江上与公子偶遇,朕已觉你正是所能托付重任之人,故暗中派人多方查访,将你的作为品行记录成册……朕身处险境,凡事不得不多方考虑,公子莫怪。”
宋江微笑道:“在下怎会介意?若换了在下身处陛下之境,也是一样会这么做的。”
他淡淡笑道:“陛下若非对宋江之为人已了解透彻,又怎会以万金之躯犯险,与在下独坐对饮?陛下身处虎狼之境尚能努力周旋,实是不易。”
徽宗听他如此一讲,不觉松了口气,道:“只是朕虽已清楚你的所为志向,但对于你的身世背景却仍旧是一团疑云。关于你的秘密,只怕比那方腊还多……”
他凝视着宋江双眼,缓缓续道:“你自两年前始出江湖,接连击败数名绝世高手,名声鹊起,但江湖中却始终无一人知晓你的师承来历、父母家世。”
宋江微微一笑,淡淡道:“陛下只要知道在下确能相助,岂非就够了么?”
徽宗如若未闻,仍旧续道:“但朕却曾留心一事——十五年前山东商河一带突发百年大旱,绵延数百里,四万百姓陷于饥荒,先帝哲宗救之不及。适逢鲁北‘中原大侠’宋青锋英年早逝,其后人竟散尽万金家产用于救济灾民,之后便孤身一人浪迹天涯,四海为家,再也不知所踪。当时那小公子正是刚满十龄的垂髫童子,竟有这般胸襟气魄,实在是可敬可赞……”
宋江面色如常,淡淡道:“陛下所言,在下似也听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