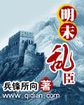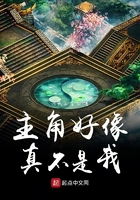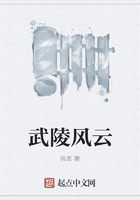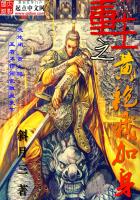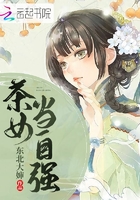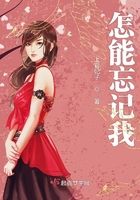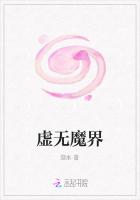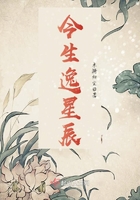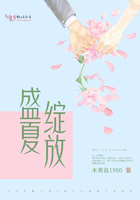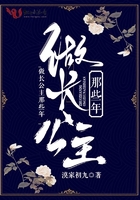吃罢了晚饭,林婉儿又喝下了林大娘熬制的参汤,气色好了不少,只是那点参须,还远远不够治疗她那双腿上的寒毒,不过总算是聊胜于无,多少让林寿微微放了点心。
林婉儿躺在床上,临睡前还不忘多叮嘱了自家哥哥两句,让他多读书,别为灯省油,林寿温言劝了两句,她才缩在被窝里沉沉地睡去。
油灯下,《四书五经》早被林大娘整整齐齐地堆在了桌上,笔墨纸砚也已全部摆好,这是林书生生前唯一仅存下的文房四宝,一直被林婉儿视若珍宝藏在被褥底下,直到今日才让林大娘重新翻出来。
书桌上,笔头上墨汁已经干枯,纸张已经微微泛黄,墨条和砚台也有些陈旧,林寿端坐在竹凳上,背对着林婉儿,循着脑中的记忆,先在砚台中倒了些清水,拿起墨条轻轻地研了一点浓墨。
然后,铺平了纸,添饱了笔,林寿丹田深吸一口气,执笔,提腕,在这泛黄的大纸上笔走龙蛇,挥笔泼墨。
少卿过后,一行大字,犹如狗爬一般出现在纸上,林寿握着毛笔,一脸的失败,果然,他写出来的毛笔字连他自己都认不全……
就这技术,只怕进了秋闱的考场,纵然能凑合写出一篇八股文来,主考老师瞅着这一笔臭字,也得当面把文章撕碎了扔在他的脸上。
林寿随手将毛笔扔在了砚台里,摇了摇头叹了口气:看来,这大明朝的科举考试,恐怕他有生之年注定就甭想了,他要想当官,只能另辟蹊径才行!
……
在大明朝,国朝选官,三途并举,除了科举考试外,还有举荐和吏员升迁两途。
所谓举荐,兴起于明初洪武年间,在洪武四年未行科举之前及洪武六年至十七年停止科举之间,曾是明政府选拔官吏和人才最重要的途径,俗称“荐举制”。
这个泥瓦匠出身的朱皇帝,深深懂得“人才是国家发展的硬道理”,视贤能为国宝,为帝之初就责令各级政府举荐人才,还曾派遣大量官员到各地访求贤能,一时全国各地很多才华横溢的学子纷纷入朝为官,直到“天顺”之后,科举日重,举荐日轻,荐举制才亦趋废弛。
而入仕第三途就是吏员升迁了,又称“吏员制”。
这是明代选拔人才和官员的另一种方式,也是明人入仕的一个最快的途径,所谓吏员,指的是在各级政府机构中办事的公职人员,比如在县衙内从事文书和勤杂工作的六房司吏,皆属吏员。
明代吏员三年一考绩,六年再考,九年考满,再经吏部考试,合格者就可以授予官职,所授官职,最好的当为一县的佐贰官,比如正八品的县丞、正九品的主簿或是从九品的巡检司,这都属于大明朝有品级的官员。
此外还有未入流,既无品级的县衙属官,包括典史,驿丞,闸官,课司大使,仓大使,河泊所大使,医学训科,阴阳学训术,僧会司僧会,道会司道会等。
这些佐贰官和属官,再经九年“考满”和不定时“考察”后,按功过又分为称职、平常、不称职上中下三等,称职者又可提升,平常者则只能维持原职,不称职者则降职。
这便是大明朝的吏员制了,与科举制和荐举制,同为明人可入仕为官的三条途径!
若林寿不能通过科举而入仕,则只能选择“举荐”或是“吏员升迁”两条途径了,不过貌似他穿越的太晚了点,当今万历皇帝自登基以来,终日沉迷于后宫佳丽中,都不曾下旨令地方州府举荐过一次,远不如他老祖宗朱元璋在位时那么开明。
其实,自书生得了秀才的功名后,就已经算是进入了这个朝代的统治阶层,在这个士、农、工、商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当一个腰缠万贯的商贾,远不如当一个一贫如洗的秀才更受人尊敬些。
所以林寿穿越后的第一想法,不是当一个富可敌国的富商,而是先当一个官吏,哪怕是从一个芝麻绿豆的小官做起。
。
翌日清晨。
当银丰县的里正来林大娘家中寻林寿时,林寿正坐在小院中的石台上读书,一口“之乎者也”读得摇头晃脑,没办法,东厢房中妹子还在竖着耳朵监督呢,再有半年就到秋闱了,林婉儿认为她有义务监督自家哥哥要好好温书。
里正相当于现在的乡长,专门为寻林寿而来,远远的就冲林寿喊:“林秀才,林秀才,刚刚衙门派人来寻你,因不知你住在哪里便找到了我,托我跟你说一声,让你马上去王家老宅一趟。”
“请我?”林寿刚放下书本,东厢房里就传出来林妹子不满的咳嗽声,赶紧解释道:“丫头啊,保正来说衙门差人来寻我,好像有事儿。”
“啊,那就先歇歇吧。”东厢房里林婉儿有些不高兴,干巴巴地道:“好端端的衙门寻你何事儿?”
林寿又向那里正高声问道:“敢问保正大哥,衙差说寻我何事儿吗?”
遗孀家的门他一个大男人是不好随便进入的,里正只好站在门口道:“这我哪里知道,见那衙差来的匆忙,走得也匆忙,只是让我来寻林秀才,让你现在马上赶往王家老宅,至于究竟是何事,他们也未说啊!”
林寿暗暗蹙紧了眉头:莫非昨日王家窃案另有纰漏?
知书达理的林婉儿也知轻重缓急,温言道:“如此来说定是要紧事寻哥哥,哥哥还是快些去吧,衙门的事儿耽误不得,这书,等回来温习也不迟。”
“好,丫头在家等着,哥哥去去看看,接着便回来。”
于是林寿也不再磨蹭,收好四书五经,重新换上了昨日所穿的蓝色澜衫和方头布鞋,冲林婉儿道了别后,跟着里正向银丰县城赶。
当林寿赶到银丰县城时,城门依然紧闭着,只在旁边开了一个窄窄的侧门,旁边有三五队巡检司的官兵来回巡逻,两个青衣皂帽的衙差挡在门口充当着检查员,对出入城门的百姓们仔细盘查。
这是王家老宅发生窃案后,官府为捉拿窃贼特别设下的门禁,凡出入城门者需要出示衙门下发的通关凭证,或是有城内乡绅和保人的保据,才方可出入城池。
因为检查严格,所以在城门口排起了一排长龙,有挑着菜篮的小贩,有推着独轮车的木工,也有赶着牛车送碳的老翁。
那老翁林寿还认得,与他还是本家也姓林,他第一天入城时便是花了两文钱坐的他的顺风车,最记忆犹新的是还花一文钱跟他买了两个野菜窝窝头,里面野葱的味道熏得他直流泪。
众人都在三三两两地簇在一起,一边排队等候一边跟相熟的朋友侃着大山,其中尤数卖炭的林老翁最为健谈,声调也高,跟几个卖菜的生瓜蛋子吹嘘他年轻时的光荣事迹,有时也会顺便点评一番银丰县衙刚刚颁布的几项民政措施,特别是对于现在日渐增长的物价,林老翁有他自己独特的见解。
他捋着花白的胡须,有感而发地道:“自前几年大旱开始,这街市上的东西是越来越贵,铜钱也越发不能叫钱了,想我年轻那会儿,二枚大钱,可以在衙前街买上十个肉包子,一瓶好酒,两只肥鸡,临走时还能再拿上一根猪肘子在路上吃,现在,可不行喽。”
周围的听客咽着口水是一脸的惊叹,瞅着林老翁那竖起的两根手指头,都恨不得能早生三十年,也能拿着二枚大钱去衙前街上大吃一顿。
现在这年景,得有好多人一年不曾闻过肉味啦。
林寿站在一旁,听着林老翁的胡诌忍不住嘿嘿一笑,接话道:“那是,现在肯定不行喽,衙前街上的衙差跑得越来越快啦,谁还敢在衙前街上偷东西啊。”
“额……”林老翁微微一怔,老脸随后一红,似乎真是被林寿一言给戳破了牛皮。
林寿哈哈一笑,不再戏耍这个老小孩,小心翼翼地避开拥挤的人群走至银丰县城的城门下,那守门的巡检司,一眼便认得昨日在王家老宅内大显威风的林顾问,赶紧满脸堆笑的让他进城。
“呔,你这兵士,那书生没出示任何凭据,你咋就让他进城了!”山东多莽汉,一看林寿插队进城,也未出示县衙开具的通关凭证,登时就恼了。
那巡检司小兵脸色一板,指着林寿的背影傲然道:“你这刁民哪里可知,刚刚过去的那书生,乃是县衙内专管稽案追凶的林顾问,破案如神,昨日王家老宅内的窃案,就是他破的!”
“啊,这么厉害!”那莽汉登时就哑口无言,惊叹道,“不是听说那窃案是一神偷所为吗,只一日之间就被他给破了?”
后面一路人甲插嘴道:“这位老哥,你可千万别不信,昨日晚上我也听我那在县衙内服役的堂弟说起,别看那林顾问骨瘦如柴,还是个书生,但破起案子来,整座县衙里所有衙差加起来都没他厉害,连大老爷都这么说!”
“吓,那不得说来,比戏曲里的包龙图都厉害?”
“那可不!”
……
林寿可是完全没有听到百姓的议论,更加不会想到,这才仅仅是过了一天,他林顾问破案如神的威名,就已经在百姓中口耳相传了。
当天破案的细节,更是一度成为百姓们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比如,人之足印长度乘以七为人之身高,这简直是让所有人耳目一新的稽案理论!
来到王家老宅,这座硕大的府宅已被巡检司围得水泄不通,府宅大门口两个抱鼓石前,光衙差就站了四个,手持着黑红相间的水火棍,严厉把守着朱门,严禁任何闲散人等出入。
那四个衙差见到林寿前来,登时喜上眉头,其中一人赶紧迎过来,急声道:“林顾问啊林顾问,您老可算来了,咱家大老爷可是在里面等了您一上午了。”
“这么着急。”林寿脚步一停,奇问道:“里面又发生了何事?”
“唉,别提了。”另一衙差叹了口气,道:“还不是那王公公闹得,今儿清早不知是怎了,突然派人去县衙寻来大老爷,然后是劈头盖脸一顿臭骂,到现在还没住嘴呢,大老爷让小的们专门在此等着林顾问,说是只要您来了,立刻请您去见王公公。”
“啊,怎么会这样?”林寿眉头一皱,有些诧异,“莫非昨夜窃案又有变化?”
按说昨日他已将窃案调查的水落石出,偷窃圣旨的窃贼也已缩小至王家内部人员,王公公又快马加鞭去济南府请来善于逼供的东厂番子,经过这一夜审讯,那窃贼应是被招供了出来,怎么那王公公今儿又大发雷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