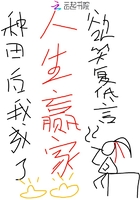安抚吃醋躁动的男人,从来只有一种途径,安抚的结果立竿见影,安家大老爷从内院出来的时候,跟刚才回府简直判若两人,刚那一张黑脸,谁瞧见心里都哆嗦,如今却精神奕奕满面生辉。
刘喜儿这心也才方下来。
安嘉慕本来是想陪着小媳妇儿歇午觉,不想刘喜儿叫人传话说宫里的林公公来了,说要见大老爷。
安嘉慕倒真有些意外,说起这林兴,如今可是皇上跟前最得宠的太监,别看就是个奴才,可得了皇上的意,那就比朝中的一品大员还有用,毕竟,这天天在皇上跟前伺候着,只要这奴才嘴歪一歪,抽冷子使个绊子,弄不好头上的乌纱帽就保不住了。
所以,如今这位林公公不止是皇上跟前的红人,也是满朝文武,地方官吏,争相送礼上好儿的一位,风头都盖过了********张德跟司膳太监柳海。
而且,别看这位才得宠没几个月,却最是大胆的,敢明目张胆的要好处收贿赂,稍不如意,立马就给你个样儿看看。
好些吃了亏的大臣,私下都骂这奴才狡猾奸诈,心肠歹毒,可骂也没用,人家照样混的风生水起,弄得好些大臣都说皇上糊涂了,宠这么个奸诈歹毒的奴才,不知多少臣子要遭殃呢。
安嘉慕是不信这种传言的,当今皇上可不是个善茬儿,当年端敬太后早丧,先帝立了王氏之女为新后,且诞下宁王,如此不利的形势下,皇上依然保住了储君之位,并在先帝薨逝之后顺利登基为新帝,并能使大燕保有如今的盛世,岂会是个崇信奸佞的昏君。
所以,这林兴之所以得势肯定是有原因的,或者可以说,林兴干的这事儿都是皇上默许的,也或者,皇上就忽然有了兴致,想宠这么个奴才。
毕竟皇上也是人,是人总有喜好,尤其皇上虽贵为天子,九五之尊,仔细想想,却异常苦闷,数不清的朝政要务要处理,只能天天关在皇宫里,稍微有点儿出格,言官御史就会跳出来,就连晚上招哪位嫔妃侍寝,都得左右衡量。
如此周而复始,给自己找点儿乐子有什么新鲜的,宠个奴才就如同养了条狗,平常逗弄逗弄,看谁不顺眼了,放出去咬上几口,也能解解气。
这是安嘉慕给林兴的定位,以安嘉慕看来,林兴这样的人最好对付,跟这些朝廷大员们打交道,安嘉慕最不怕就是贪官,反而油盐不进的所谓清官,是个麻烦,就像他兄弟这种。
这人要是没了喜好,也就没了缺点,就难对付了,安嘉慕倒是喜欢林兴这种,说穿了,不就是银子吗,他安家最不缺的就是银子。
京里安记的大掌柜说是照顾着买卖,其实就是为了打通上下关系,才安排在京里的,以保证最快的得到上头发下的消息政令,这做买卖虽不是官场,可跟官场却扯不开,只有耳目聪灵,才能保证自家的买卖长久做下去。
尤其,宫里这些太监是最有用的,林兴一得宠,就得了安家不少好处,为了厨艺大比,安嘉慕又叫大掌柜照着林兴的喜好,给他送了一份厚礼。
虽说私下里有这样的来往,可林兴找上门来,可是大忌,有心不见,却想起林兴如今正得宠,又是御厨比试的要紧时刻,得罪了这个奴才,他要是起了坏心,可是麻烦。
在安嘉慕想来,只要干系自己的媳妇儿,那都是了不得大事,需要事事周全,万无一失才成,故此,还是决定见这林兴一见,看看他到底来做什么,莫不是看中了自己是个大头,来索要好处的。
可一进客厅,瞧见这位林公公,还真让安嘉慕颇为意外,这位公公长得实在清秀,个头也不算高,太监吗都有些娘们,这不算什么,可这林公公身上,硬是有种说不出的味道,且极为大胆,眼睛上下打量了自己几遭,那目光让安嘉慕有种自己是待价而沽的错觉。
不免微微皱了皱眉,一拱手:“不知林公公光临寒舍,有失远迎,还望见谅。”
这小太监倒也算讲礼数:“大老爷客气了,林兴冒昧来府上,是想见见夫人。”
安嘉慕脸色一沉,冷声道:“内子身体不适,恐不能出来招待林公公。”
安嘉慕这话已经说得极明白,不想这小太监却不上道:“如此正好,在下精通医术。”见安嘉慕要怒,却笑了一声:“大老爷千万别误会,林兴并无他意,只因听说安大厨的名声,颇像在下一位同乡,故此才寻了来。”
同乡?安嘉慕心里一震,安然的来历始终是一个解不开的迷,他知道她不是自己府里那个丫头,却又不知她是谁,之前为了这个,好些日子都睡不好,生怕一觉醒来,这丫头就没了,如今忽然蹦出来个同乡,怎能不让他震惊。
安嘉慕定了定神,深深看向他:“你说你是我夫人的同乡?”
林兴点点头:“不错。”心里却说,只要她是自己认识的那个死丫头,就绝对是同乡。
安嘉慕沉默良久:“在下能否知道林公公的家乡是哪里?”
林兴如今倒越发确定这位安夫人就是那忽然消失无踪的死丫头了,瞧这男人掩饰不住的紧张,就能看出来,是真把安然当成宝贝疙瘩了。
而且,对于安然的来历即使不甚清楚,心里也隐约明白,如此倒好办多了,不过,安然既然都不跟他说明白,自然有道理,他们的来历的确是不好说。
想到此,眨了眨眼:“这个,我自己也忘了。”
安嘉慕却陡然站了起来:“想来林公公找错了人,内子是地道的冀州人,只要林公公稍一扫听就知道,内子的出身来历,并非公公所寻同乡,府里还有旁事,就不陪公公了,刘喜儿送客。”
刘喜儿忙进来:“林公公请。”
林兴愕然半晌儿,却见安嘉慕那把黑锅底一般的脸色,估计这位是把自己跟安然的关系想歪了,这男人的醋劲儿一上来,简直不可理喻。
而且,这家伙偏偏是安然的男人,自己还不能下手收拾他,只能压了压火气,估计自己只能另外想法子见安然了,指望这男人是绝无可能的。
反正过不几天,就是御厨大比,到时就不信他还能拦着自己见那丫头,男人了不起啊,自己跟安然睡得的时候,他还不知在哪儿呢,站起来气哼哼的走了,简直是相看两厌不欢而散。
刘喜儿送着林兴儿出了府还道:“公公您真找错人了,我家夫人真是冀州人,底根儿起就是我们安府的。”
林兴翻了个白眼,这不废话吗,自己底根儿起还是太监呢,找谁说理去啊,哼了一声,没好气的道:“你们安府再厉害,怕也出不来安然这样的大厨,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你还有我了解那丫头不成,回去跟你们大老爷说,他把安然看的再紧也没用,我跟安然好的时候,你们家大老爷还不知在哪儿转筋呢,就算嫁了他,只要我不答应,也非让安然跟你们大老爷和离不可。”撂下话走了。
刘喜儿愣了半天,一拍大腿,哎呦,这可不好,眼瞅着老爷夫人和美恩爱,这怎么忽然蹦出来个搅局的了,要是别人还罢了,偏偏是皇上跟前的红人,这要是真使个坏,可麻烦了,忙跑回去报信。
安嘉慕这会儿还坐在椅子上生气呢,一想到刚这死太监暧昧的德行,心里就冒酸气,加上刘喜儿进来把林兴撂的话一说,更是气的七窍生烟,那脸色黑里透着青,咬牙切齿的,瞧着甚为怕人。
刘喜儿忍不住后退了一步,磕磕巴巴的道:“那个,大老爷,我瞧着这小子就是胡说八道的,夫人从未离开过冀州安府,何曾有什么老乡……”
不等刘喜儿说完,安嘉慕已经出了客厅,往后院去了。
安然实在佩服他,体力太好了,安嘉慕意识到自己在盛怒之中,力道过大,生怕小媳妇儿着恼,要跟自己冷战,立马低姿态的伺候媳妇儿沐浴更衣,外加按摩,擦头发,一边儿还暗暗度量着安然的神色。
这副明显做贼心虚的德行,看在安然眼里颇有些好笑,虽然不知为什么,但刚才安然也感觉到了他的怒意,做的格外用力,想忽视都不可能,这会儿安然还觉得自己的腰一阵阵麻酥酥的酸疼,仿佛快不是自己的了。
安然疑惑的看着他:“出了什么事儿吗?”
安嘉慕才不会提那死太监呢,把她抱在自己怀里摇摇头:“没什么。”半晌儿才道:“跟我说说你家的事儿好不好,我记得你说过你爷爷,还有你父母,除了他们还有谁?”
安然愣了愣,不想他会提起这个,自从苏州那次说开了之后,他几乎没在提过,或许是因为这件事的不定性,两人不约而同的选择回避,而安嘉慕这会儿问出来,倒勾起了安然对于好友的思念。
在安然三十年的人生中,林杏儿是异常重要的存在,两人从小一起长大,经历家庭都极为类似,林杏儿比自己更不幸一些,她的父母并不是早丧,而是离异,两人各自组织了新家庭,却把林杏儿抛在了老宅,跟着林爷爷一起长大,甚至从不来看林杏儿。
林杏儿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往自己家跑,吃妈妈做的菜,哪怕妈妈做的菜,远不如林家厨子的手艺,她也吃的津津有味,更喜欢在安家待着,后来干脆搬到了安家,跟自己同居一屋,一直到她出国留学,两人从未分开过。
他们是朋友,更是姐妹,也是家人,他们彼此了解,彼此珍惜,最难过最孤单的时候,都有彼此在身边,可现在却不知她在哪儿?自己莫名消失,林杏不知多着急呢。
安嘉慕见她出神,心里的酸水又冒了出来,不满的道:“想什么呢?”
安然:“想我的一个朋友,不,应该说是姐妹,也是我的亲人。”
姐妹?亲人?安嘉慕目光闪了闪,眼前划过林兴儿那张讨厌的脸,他媳妇儿说的不是那个死太监吧:“你说的朋友是女的?”
安然奇怪的看了他一眼:“姐妹自然是女的了,你不知道,她的医术可厉害了,要是她在这里就好了,师傅的手肯定能治好。”
安嘉慕:“你说她是个郎中?”
安然点点头异常骄傲的道:“是医术最高明的郎中。”
安嘉慕迟疑的道:“就像你的厨艺一般高明吗?”
安然笑了:“是有人这么说过,称我们是绝代双骄。”
安嘉慕心里的震惊无以复加,没人比他更清楚安然的厨艺,如果照着安然说的,那死太监真是她那个姐妹的话,岂不是天下最牛的神医,怎么想怎么不像,那死太监一脸奸相,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而且,小媳妇儿明明说是女的,那小子可是太监,这也对不上啊,即便真是一个人,自己也不想让小媳妇儿跟个死太监走的太近。
只不过,怎么瞒住小媳妇儿真是个问题,那死太监想来不会善罢甘休,猛然想起最近宫里的传闻,都说林兴之所以得宠,是因皇上腻歪了后宫的娘娘们,好上了男风,这林风虽是个太监,却长得格外清秀,这才入了皇上的眼。
若这事是真的就好了,皇上稀罕的人自然不会随便放出来,回头自己的好好扫听扫听,真要是有苗头,自己就想个法子推波助澜一下,成了好事儿,那死太监这辈子都别想离开皇宫了,也就甭想惦记自己媳妇儿了。
想的太过得意,不想落进安然眼里,安然忍不住打了寒战:“你这笑的太歹毒了,琢磨什么呢?”
安嘉慕自然不会跟她说,笑着摇摇头:“没想什么,就是想晚上吃什么?”
安然想了想:“嘉言喜欢吃鱼,晌午的时候瞧见厨房里有新鲜的花鲢胖头,老大的个儿,一会儿叫嘉言过来,我做给他吃,想来他会喜欢。”
安嘉慕不禁道:“你倒是想着嘉言。”这话说的有些酸。
安然忍不住笑了起来,这男人有时比孩子还幼稚,便开口哄了他一句:“若不是嫁了你,说不得你兄弟这辈子也吃不上我做的菜。”
这句话说的安嘉慕高兴起来:“我知道你对嘉言嘉树好是为了我,为夫领情。”说着,凑上来亲了安然一口。
两口子正再调笑,忽听外头仆妇道:“老爷夫人,谢氏夫人带着皓思皓玉两位小少爷来了。”
安嘉慕眉头一皱:“这不晌不午的,她来作甚?”
安然:“这话说的,她是你弟媳妇,来串门子还能赶出去不成,更何况,还有皓思皓玉。”
两口子收拾立整,便出来了,安然倒是想看看谢氏还会耍什么把戏,可大人如何,怎么也不能牵连孩子,更何况,这俩孩子是安家的骨血,便叫安嘉慕带着孩子去书房玩。
不想,安嘉慕还没动呢,谢氏却先一步道:“大嫂,之前都是一娘的不是,未约束好下人,平白为难了大嫂,都是一娘的错,一娘这给大嫂赔礼了,长嫂如母,大嫂虽年纪小,嫁了大伯也相当于一娘的长辈,您要是还生气,打我骂我都成,就是别憋在心里,回头若是气出病来,叫一娘心里怎么过的去,一娘这儿给大嫂跪下了。”说着就要下跪。
安然一把拉住她:“这是做什么,当着孩子呢,这么着叫两个侄儿瞧了,不定还以为我欺负他们娘亲了呢,心里若恨上我,可怎么好。”
安然这话说的安嘉慕脸色略沉,牵着皓思皓玉出去了。
谢一娘却打蛇上棍:“大嫂就看在皓思皓玉的份上,就别跟一娘计较了。”
安然目光闪了闪:“你这话倒说的我越发迷糊了,你我妯娌之间,有什么可气的,更不要说,自打我来了,你处处周到,那婆子的事儿跟你什么干系,不过是瞧着我出身低,心里不忿罢了,嫂子心里明白。”
谢一娘愣了愣,怎么也没想到安然会这个反应,本想好的一大篇子话,倒不好开口了,不免瞄了自己的丫头一眼。
春巧忙道:“大夫人是不知道,这两天我们夫人都没怎么吃饭呢,睡觉也不踏实,就惦记着来给大夫人赔不是,却想到大夫人得跟那些名厨比试,怕搅扰了大夫人,这才耽搁到了今儿。”
安然倒是瞧了这丫头几眼,上回也见过,是谢氏跟前伺候的丫头,没什么姿色,那眼珠子却滴溜溜的转,一看就是个有心眼子的。
听说谢氏跟前那个婆子被嘉言发落了出去,想来这丫头借机就成了谢氏的心腹,倒是会见缝插针。
谢氏假意喝了一声:“还不退下,我跟嫂子之间,哪有你说话的份儿。”那丫头忙低下头退了两步。
安然笑道:“弟妹何必如此,到底我嫁过来的日子短,咱们妯娌之间还有些生疏,等以后日子长了,你就知道我的性子了,是个最大咧的,也就会做菜,旁的事从不放在心上,便多大的事儿,转过头就丢开了。”
谢氏倒也聪明,并不再纠缠此事,而是笑着跟安然说起来了家常,选择的话题也相当安全,都是围着皓思皓玉转。
说了半天话儿,方才站起来告辞,却把春巧手里的盒子拿了过来,放到桌子上:“当初我嫁过来的时候,家里陪送了个香料铺子,亏了大伯照顾,才能支撑着,在家的时候也学过调香,虽不是高手,却也过得去,这是一娘亲手调的香,嫂子莫要嫌弃。”
“如此那嫂子就收下了。”谢氏这才带着孩子回去了。
安然送着她出了院,回来却不见了桌上的香盒,不禁道:“那个盒子呢?”
安嘉慕:“叫人收起来了。”
安然知道他的心思,不禁笑了一声:“你却是多心了,便她真有心害我,又哪会如此明目张胆,更何况,多大的事儿也不值当如此啊。”
安嘉慕:“这妇人的心思可难说,尤其她是谢家门里出来的,别听外头说什么大家世族,门里尽是龌龊事。”
正说着,岳锦堂风风火火的跑了来,一屁股坐下,灌了一盏茶下去,才道:“发财了,发财了,今年可真是财神显灵,这发财的道儿一个接着一个,不过,这回还得指望你这丫头。”
安嘉慕脸色颇有些不好看:“你有本事发你的财,扯上安然做什么?”
岳锦堂:“你这话可不对,没有安然,本王有什么本事发财啊,说起来,还亏了皇上跟前那死太监提的醒,本王坐庄设了个赌局。”
安嘉慕皱了皱眉:“你不会赌的是安然跟韩子章吧。”
岳锦堂嘿嘿笑道:“不愧是安大老爷,一猜就能猜中。”
安嘉慕目光闪了闪:“压谁的多?”
说起这个,岳锦堂就更喜形于色了,贼眉鼠眼的道:“本王就知道哪些朝廷大员没眼光,琢磨着韩子章顶着天下第一厨的名头,都压了韩子章赢,安然这边儿下注的,是些知道底细的,不过比起那些皇亲宗室,就算不得什么了。”
安嘉慕眼睛一亮:“的确是个发财的机会,不过,那些皇亲宗室你这么坑他们,就不怕过后他们找你算账啊。”
岳锦堂撇撇嘴:“愿赌服输,哪有找庄家算账的,还有没有赌品啊,更何况本王还压了一万两银子进去呢。”
安然不禁道:“你就不怕我输了,到时你可血本无归。”
岳锦堂摇摇头:“你要是输了,那肯定有猫腻,就韩子章那两下子,哪是你的对手啊,本王信你。”说着,看了看窗外:“那个,时候不早了,是不是该吃饭了啊。”
安嘉慕没好气的道:“知道该吃饭了,还不回你的郡王府。”
岳锦堂嘿嘿一笑:“要是你舍得安然去我哪儿当厨子,我保证再不进你安府的门。”
岳锦堂就这德行,是一块蒸不熟煮不烂的滚刀肉,两口子一贯拿他没辙,反正多个他,也就多双筷子的事儿。
安然让安平去侍郎府请安嘉言过来,自己去厨房掂量着做菜,狗子跟顺子早睡醒了,刘喜儿说两个小子一睡醒就跑了出去,说是要逛逛京城。
他们头一次来,难免新鲜,这俩小子机灵,不是惹是生非的主儿,便也不担心,倒是高炳义老实,留下来给安然打下手。
安然一边儿做菜,一边问他齐州的事,高炳义一一道来,说起梅先生,高炳义笑道:“先生如今可不敢见姑娘,天天叨念着,怕姑娘一气之下拿厨刀砍了他。”
安然不觉莞尔,当日刚知道梅大就是安嘉慕的时候,别说,还真有这种心思,若不是梅先生这么一位德高望重的大儒作保,自己怎会实心眼儿的信了梅大。
何曾想过梅先生这样的人也会帮着人扯谎,还扯了这么个弥天大谎,骗的她嫁给了安嘉慕,不是上官瑶嫉恨自己,揭开此事,如今自己还糊涂着呢。
只不过,如今事情过去了,心里却真有些感谢梅先生,不是先生,以自己对安嘉慕的憎恶,又怎会嫁他,不嫁他,两人岂不是错过了。
安然也是到现在才明白,这人跟人的缘分颇为难得,既然有缘就该珍惜,若错过了,便是一辈子的憾事了。
安然有时总想,如果没有安嘉慕,怕也没有如今的安大厨了,自己总以为能靠自己活的很好,却忘了,这里毕竟不是现代社会,如果不是安嘉慕明里暗里护着自己,齐州那一把火,就让自己死于非命。
更何况,还有个心肠歹毒的韩子章,这厨行跟官场搅合在一起,没有相当的势力背景,怕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想到此,开口道:“其实我早就不怨先生了。”
高炳义高兴的道:“先生要是知道,不定明儿就跑京城来了。”
安然也笑了起来:“不是明儿也快了,太后寿诞之日,便是御厨大比,先生怎会错过这个热闹。”
见高炳义已经把鱼处理好了,安然便接了过来,因这条花莲胖头鱼大,足有十来斤,安然便做了一鱼四吃的创意版。
鱼头做剁椒鱼头,鱼骨鱼尾剔出来熬汤,鱼肉做了一个水煮鱼,又做了一道安嘉言爱吃的珍珠鱼丸,炒了一个素合菜,配上一盘炒肉丝。
炒好了肉丝,安然盯着那锅愣了一会儿,忽然想起当初自己正是因为做这道炒肉丝,才穿到这儿来的。
说起来,她也没什么牵挂,除了林杏儿,不知她如今怎么样了,更不知,此生还能不能见上一面,安然忽然觉得,自己有好多话忘了跟林杏儿说,也没真切的叫她一声姐姐。
她其实就是自己的姐姐,虽然毒舌,却也是最护着自己,心疼自己的人,可惜,再也没机会了吧。
不管谢氏怎么折腾,嘉言永远都是安嘉慕的兄弟,这一点儿谁也改变不了,而且,因父母早丧的关系,安家兄弟之间格外亲厚,别的宅门兄弟为了家产你死我活的事情,在安家绝不可能出现。
尤其在嘉言嘉树心里,安嘉慕不仅是大哥,还代替了父亲的角色,撑起了安家,拉拔了幼弟,所以分家是三兄弟都不想。
,嘉言之所以提出来,也是看出谢氏不是省油的灯,怕以安嘉慕的性子到时候左右为难,倒不如咬牙分家,如此,谢氏再有什么心思也不得不歇了。
安嘉言提出分家,心里已是难过愧疚已极,而谢氏那句慌乱中问出的话,却彻底凉了安嘉言的心,也让安嘉言看清了自己所谓的贤妻,不过就是个名声罢了,心里比谁都贪婪。
因为谢氏,嘉言如今面对哥嫂,总不觉愧疚,听说谢氏今儿来过,忙问:“她来作甚?”
安然倒笑了:“一家子人,弟妹来串个门子有什么新鲜的,吃鱼,知道你吃不得辣,这个鱼丸是嫂子特意给你做的,尝尝好不好?”说着给他装了一小碗递给他。
安嘉言心里一热,虽说安然这大嫂年纪小,却让他想起了死去的娘,爹娘没去世之前,安家虽没如今这般富裕,却也吃穿不愁,家里也有厨子下人。
可他们娘却喜欢下厨做菜,并且,把他们兄弟的喜好都记得异常清楚,自然比不上大嫂的厨艺,但这份心是一样的,这才是家。
当初谢氏没过门的时候,自己听大哥说她贤惠,且善厨艺,心里其实颇为期待,盼着谢氏能跟娘一样,时常下厨,却不想,自打谢氏过门,从未做过一道菜,她总是拿着当家夫人的架子,在乎名声,在乎排场,却从不知道自己这个丈夫在乎的是什么。
从这边儿吃了饭回到侍郎府,忽觉冷清,即便只是一墙之隔,且,大哥哪儿的下人仆从,远远少于侍郎府,可一进到那边儿就觉得舒服,像个家,而这里就是冷冰冰的侍郎府,叹了口气往书房走去。
谢氏这两日,天天都去寻安然说话儿,两个妯娌至少在外人看来,甚是和睦,可安远两口子一过来,谢氏便急了起来,自己要是连管家的权利都交出去,那自己这个侍郎夫人岂不成了摆设。
本来还以为丈夫来正房,是回心转意了呢,不想却是说这件事,忙道:“这管家本就是当家夫人的本份,哪有交给外人的理儿。”
外人?安嘉言冷冷看着她:“谁是外人?安远两口子是安府的老人,我爹娘活着的时候,他们两口子就管着府里的事儿,况且,你是不是忘了,侍郎府的开销用度,如今都归在公里呢,你若是想当家,也不是不能,从此不再用公里一分银子,这方是你当家夫人的本事。”
谢氏:“老爷那点儿俸禄如何支应的起府里的开销用度。”
“你也知道支应不开,你也知道,咱们这个侍郎府使的是我大哥挣来的银子,既如此,你当的哪门子家?不瞒你,这是大哥的话,不叫你管家,都交给安远夫妻,日后侍郎府的人情来往,各项用度,都不用你操心了,省的生出许多事儿来。”
谢氏脸色难看非常:“老爷就这般不念夫妻情份不成,便不为一娘的体面,难道也不想想皓思皓玉。”
安嘉言:“大哥若不是念着皓思皓玉,哪还会如此麻烦,你只管放心,大哥是绝不会亏待皓思皓玉。”撂下话,不等谢氏再说什么转身决然而去。
谢氏一个踉跄险些栽在地上,咬了咬牙:“都是那个贱丫头,贱丫头……”
春巧忙道:“夫人您可得想开了,别气坏了身子。”
“想开?我怎么想开,这当家夫人却连家都管不了,处处受个下人所制,这传出去,别人便嘴上不说,心里不定怎么笑话我呢,还有,我爹娘那边儿,可是指望着我这里接济呢,如今怎么办?”
春巧道:“夫人您都嫁了,怎么还总顾念着娘家呢,就算安家银子再多,若是老爷知道夫人接济了娘家,怕也不高兴,不过,夫人也别着急,您总归是侍郎夫人,还有两位少爷傍身,那边儿大夫人可是什么都没有,论功劳,夫人还是安家头一份的功臣,只要那边儿生不出孩子,安家的家产再多,最终也会落到两位少爷手里,不就等于归了夫人吗,到那时,夫人还不想怎么使怎么使,谁管得着。”
谢氏心里活动了,况且,自己如今除了忍也没别的法子。
安远的手段自然不一般,可也没想到会如此棘手,这一插手管才知道,一个侍郎府每月的开销,竟是冀州安府的两倍,且账目不清,问了账房,只说是夫人支走了。
安远只得来回大老爷,安嘉慕早就料到如此,这谢氏如此贪婪,自然不会放过到手的银子,若她不是想难为安然,自己也不在乎这点儿银子,如今却不会便宜她,挥挥手:“之前的不用查了,从今儿开始立账,把账房的人都换了。”
安远这才领命而去,岂止账房,整个侍郎府除了谢氏跟前的人没换,其余的下人换了大半,这才算把侍郎府理顺了。
安远本来就是刘喜儿的师傅,如今师傅师娘过来管着侍郎府,可把刘喜儿高兴坏了,两边跑得越发勤快。
如今两府的大管家是师徒,比起谢氏管家的时候,才真正成了一家儿。
两府里的下人如今也明白了,谢氏夫人再不甘心,再动心眼子也没用,别管人家是什么出身,大老爷三媒六聘的娶了进来,就是安家的大夫人。
更何况人大夫人虽出身不如谢氏,却是一个有名的大厨,不说别的,能跟天下第一的御厨比试,可想而知,大夫人的厨艺有多厉害,这一琢磨,谁还敢不老实。
没人敢再生事,两府终于真正安生了下来。
太后的寿辰也到了,前一天梅先生跟师傅来了。
安然两口子迎了出去,梅先生还躲在车上不下来,简直跟老小孩一般,白等安然过去,亲自请他,梅先生才下来。
见了安然仍有些忐忑:“你这丫头真不怪老夫了?”
“不怪,安然还得谢梅先生的大媒呢,不然,上哪儿找这样的如意郎君去。”
梅先生倒吓着了:“你这丫头莫不是诓老夫进你府里,再拿厨刀吧。”
安然点点头:“是得拿刀。”
见梅先生脸色大变,高炳义忙道:“姑娘拿刀是要给先生和老爷子做菜接风呢,可不是要剁人。”众人忍不住哈哈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