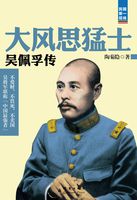两个衙役立刻抬出一块小门扇似的东西。由于红绸遮得严实,大家一时弄不清县太爷耍的什么把戏。看着那东西很多人记起,那年在县衙大堂董善仁就弄出个和这样子差不多的东西——假造的万民匾。见众人疑惑瞩目,扈龙有点得意,想抖个“包袱”,故意指着说:“这是特意送给刘更新的,谁能猜出这是什么?”
那会是什么呢?万民匾?不可能,那东西只有百姓给父母官送的,哪有当官的给百姓送的。不是匾额,一定是家里常用的物件儿。乡村百姓凭着自身的见识和一颗平常的心端详着思量着猜测:
“风箱盖儿!”老南瓜看出了门道,抢先说。
“擀面板子!”一个中年妇女凭自己的经验发表意见,女人们跟着附和。
“我咋瞅也是块条桌面儿!”辛先生说出的话带有权威性。想想很有道理,刘更新是读书人,送块桌面儿最合情理。
老石匠直眼瞅着先点头又摇头,“不对吧,看样子分量不轻,如果是桌面儿也不是木头的,一定是块花岗岩!”
……
大家不着边际的猜测议论,使县太爷大为扫兴。他也不说话,上前一把两把扯去裹着的红绸,众人不觉张大了嘴巴——啊呀,还真是一块明黄色的匾额!那匾金灿灿亮闪闪灼人目耀人眼,像面板赛条桌齐边齐沿纤尘不染!难怪大家不着边际地胡猜乱想,这里不是大堂也不是打官司,送给刘更新做啥使呢?……哦,会不会还是当年董善仁弄的那一块?现在拿来转送给更新是什么意思?……村民们又是惊诧又是疑惑,揉揉眼小心地细瞅那匾额,情知中间凸起的横竖道道是字却不认得,多亏辛先生惊得发颤的嘶哑嗓子读出声来:
“解——元——第!”
众人愈是这样县太爷愈感到匾额的意义,心里头就愈感得意。“没有想到吧!”他看着惊愕的人们继续说道:“这字是请任村集上曾任三品京官的苏大学士题的,匾是黄华山上的黄梨木做的。刘更新是林县第一解元,这匾额也堪称林县第一匾!”说着嗓子一亮,挥手喝令:“挂到刘解元大门上去!”
村民们疑惑尽去完全明白过来——这里不是官堂但是刘更新的家。刘更新做了官也就成了官府,官府门上都有匾额——立刻表现出少有的热情。这样的金色大匾除了县衙大堂全林县谁家挂过?县官除了亲自来给刘更新送匾挂匾还给谁送过?没有了,肯定没有了!这荣耀是刘更新独有的,也是下川村独有的!人们高兴地喊着叫着朝刘家大门涌去。
衙役们抬着匾额,在村里人导引下朝村里走。扈龙带着侍从也跟着走。刘继基高兴激动紧张得心里慌慌的,紧紧拉着儿子跟在县太爷身后。
山村街道不比县城大街,石头瓦块凸凹不平,扈龙身肥腿短走得艰难趔趔趄趄。官靴蹭在石子上打个跄踉,多亏两旁有侍从搀扶着,没有跌倒脚尖却被跄得生疼,弄得他又是咧嘴又是吸溜鼻子。刘继基看得胆战心惊捏着一把汗;更新看着开心只是想笑。好在从村头到刘家门口不过几步路,挪脚就到。
幸亏刘继基翻修过的磨砖门楼还算巍峨高大,硕大匾额挂上去不显得寒碜还算般配,只是把原来门楣上的“凝瑞气”三个吉祥的黑色大字遮严实了。一块金匾,光彩耀眼,刘家门楣发光,整个山村仿佛也一下亮堂了许多。
大家看着叫好。刘更新看着那匾额,仿佛看到了众多抱着一线希望一颗愚心拼命苦读的莘莘士子;看到道貌岸然的海学政、金巡抚、呼主考的狰狞面目;看到了卑恶龌龊弄权营私挂羊头卖狗肉的应试科场!……胸中五味杂陈搅拌翻腾。
刘继基受宠若惊,又是高兴又是感激趴地上给县太爷叩着头说:“谢县太爷看重,抬举我们刘家。”
扈龙把他扶起说:“更新步入仕途,就成一家人了,不必见外。”说着面向更新,“听说刘解元将要赴府就任,本官还特地备了一顶官轿,随时听候差遣。另外家中还有什么困难,本县一定鼎力相助。”
更新不冷不热地说:“谢谢关心,大人不愧父母官的称谓,为更新想得如此周到妥帖!”
“不用谢不用谢,这是本县分内之事。”
“但是,大人不只是刘更新一人的父母官,治下子民成千上万,关心他们的安危冷暖,饥馁急难,也是分内之事呵!”
“说的是,一听就是个干大事当大任的口气!”扈县令望着更新缺乏表情的脸色,听出话带揶揄可只是一笑,侃侃言道,“父母官父母官就是要像父母一样,时刻把子民百姓的安危冷暖挂在心头,全县有多少百姓,心里就要装多少,一户也不能缺,一个也不能少!本官自到任以来,宵衣旰食,不敢稍有懈怠,只是这里山高沟深,水缺如油,十年九旱,地瘠民贫,林县的官做起来格外艰难,格外忧心啊!”
更新笑了,“不吃那份药,不知那份苦。百姓饿肚子的滋味当官的不知道,当官的辛劳草民更体验不了。对老百姓来说,有没有饭吃才是最实在的问题。年成如何,赋税轻重才是大伙最关心的。”
“刘解元一语中的,所见深刻!”扈龙油脸上镀上一层晚秋的阳光,显得神气十足,他鼓了两下掌说,“所以本县轻税薄赋,就是要让民众休养生息。”
更新摇摇头说:“可惜山乡林县赋税却比平原县份还重,百姓不要说吃饱肚子,一遇旱年灾荒不饿死就是万幸了!”
“这是朝廷立下的规矩,皇粮国税,谁敢不交?”扈龙两手一摊,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为这事我专门向皇上写过折子,没有回应。”他说着眼珠一转,“后来听说林县一县的赋税是紫禁城里娘娘妃嫔宫娥们一年的粉黛胭脂开销。娘娘们的用度不减,赋税怎么能少?”
扈龙见刘更新一哂,想要开口,怕他再说出什么令自己吃咽不下的话来,所以吸溜一下鼻子又接着说道,“本官只是个七品芝麻小吏,知府巡抚道台哪个抬抬腿都比我的头高,心有百姓而力不能及。还望刘解元见到上宪,上达下情,为林县百姓多多呼吁,削减赋税,那就是为一方百姓办了天大好事呵!”
更新知道扈龙在给自己戴高帽子堵自己的嘴,情知再与这种官场油子磨嘴皮子没有用处,便说:“更新本为百姓一员,百姓的事就是自己的事,更新力所能及,尽力而为。不知大人大老远地赶来,还有什么公务要办?”
作为一县的父母官,俯身屈驾亲自把天大的脸面至高的荣耀亲自送上门来,这是多大人情!搁谁都会感激涕零怀恩重谢的,刘更新怎么就体会不到呢?就算是过去结着疙瘩我这一来也该解了;冰见火没有不化的,我这样烧火难道还化不开小子心头的那块冰么?不用说锣鼓喧天,杀猪宰羊的欢迎了,连句“请到寒舍小叙”的话也没有,就要撵自己走,扈县令一阵丧气恼火,心里暗骂得势狸猫强似虎,小子还没到任就端架子!肚子里的气一鼓一鼓的,真想破口大骂,可他忍住了:别说骂,只要不中听的话出口,这次就白来了,连表面人情也一风吹干净了!都说宰相肚里能撑船,扈龙虽然只是个小县令,可肚量也不算小。只见他面色红了又白,眼珠子骨碌几下,吸溜一下鼻子,伸伸脖子强咽一口唾沫,缓缓说道:“本官公务烦杂,不便久留,你何时起身赴任,知会一声。”
更新仍然不冷不热,“去不去彰德府我还没拿定主意,就是去,骑驴步行均可,也不会去惊动县太爷的。”
县太爷走了,却为山村留下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解元第。
拆墙记
一晃又是半月,更新在街坊邻里亲朋好友的劝说下,终于要去赴任了。
他下这个决心,最重要的不是众口一词的世俗劝导,而是反复思量在汴梁时易先生教诲的结果。易先生认为当今官场黑暗,百姓横遭蹂躏,有冤难伸之时,有识之士隐匿不仕只求自身高洁并非上策,出仕做官,做好官,反倒能使一方风正气清,百姓获益,不枉十年寒窗。更新抱着到浊水潭中撞一撞闹一闹,纵然不能使整潭水变清,也要澄出些污垢来的心情打点上路。
刘继基见儿子回心转意,喜不自胜,特备两匹高头大马,要亲自相送。小石头自愿当随从伺候。更新不骑马,也不要父亲送行,只要一头小毛驴驮着行李,让小石头赶着就上了路。父亲拗不过,只好作罢。
两个一块长大的伙伴一路谈笑玩耍,走了两天来到府城。更新去过府衙几次,不用问路,从小西门进去穿街过巷径直走去。正走着见一堆砖头瓦砾石灰沙子乱七八糟掩了半道街,瓦砾后面两座富丽堂皇深宅大院。东边一家靠西边的房子已经扒了半拉,看样子是要翻修。更新心里说,看架势也是大户人家,做事却不地道,自家修房展屋图方便也不管众人走路方便不方便,霸道!
“路人心里有杆秤,这家人就是霸道,还不是仗着朝里有人么!”
更新也不知道是否心里想着嘟囔出了口,旁边有人好像接着他的话说。说话的是两个中年汉子,一高一矮,脸上露出不平之色。
“可也是,既是公巷,凭什么说占就占?”
“这回老虎碰见豹子啦,谁斗过谁还不一定呢!”
更新天性好奇,听他们这么说便驻了足,上前拱拱手道:“二位大哥,你们也是从这里过路的吧,这是两户什么样人家?”高个子大哥也礼貌地朝更新举手一揖,反问:“我说小兄弟,彰德城里秦王两家显赫大族你没听说过?”矮个子大哥笑了,说:“你没听人家是林县口音!”高个子醒悟过来也笑着点头。接着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地说了前因后果。原来东边住着秦家,西边住着王家,两家边墙之间隔着三尺宽的间隙。现在秦家翻修旧屋,要向外扩展三尺,王家不许,说中间隙地为两家共有。为此两家各不相让,纷争已经好长时间了。更新待要细问,小石头却不耐烦,说因宅基纷争生气打架的事多啦,有什么新鲜。天快晌午了赶紧到地方吃饭是正办,说着牵着毛驴踏着砖块瓦砾只管走,更新不好再问什么。
知府鱼登水在城南门题字时就已见识了刘更新的才华。这次乡试刘更新又一举夺魁,文章受到皇上褒赏,巡抚大人亲自举荐,更是不敢怠慢。知事虽然只是末等小吏,在知府眼里也就是个衙役头儿,大跟班的。鱼登水却对更新另眼相看,安排他住到衙内离后堂最近的东偏院。院内修竹花树,曲径浅廊;室内满架书籍字画,翰墨飘香,清静高雅。知府说政事愿意管就管,不愿意管就甭管,可以专心读书,以备会试。更新言谢,鱼登水却对更新说,你绝非久居人下之人,等你进士及第,跃居高位,不忘下官就行了。见上司虑得如此深远,更新暗笑,也就不说什么,由他殷勤。
当天晚上知府又设宴为更新接风。席间鱼知府说到为官不易,竟连连叹气。更新问他有什么难事,知府说这几天遇到一个难缠的案子。他说的就是更新来时看到的秦王两家为三尺地皮争执不下的事。要说案子并不难断,空口无凭,要拿出字据,两家均无。视为公有,可秦家非占不可。更新说那秦家不是蛮不讲理么,知府大人主持公道才是。
“问题没那么简单!”鱼知府头一仰把杯里的酒灌进肚里,眨巴眨巴月牙眼,晃晃白团脸无奈地说,“秦家可不是普通人家。秦家老二就是当朝翰林院的侍读学士秦望日,虽然是个四品官,可是皇帝近臣,得罪不起呀!”
更新不善酒,举起杯来只是抿了抿便放下了,说:“官再大也大不过一个理字,大人只管秉公断案就行!”
鱼知府头摇得拨浪鼓似的,“我的小兄弟呀,你初入官场,不解内中奥秘。那样丢掉头上顶戴事小,恐怕连脑袋也难保住!”
更新不以为然地笑笑,“也太危言耸听了吧!”
“绝非虚言!”鱼知府瞪着月牙眼盯着这位不谙官场的新下属,谆谆言道:“有一位同僚,原任大名知府,为人耿直,官声很好,年终考语优良,吏部票议升迁,偏在这时候出了一个奸杀案子。证据确凿,事实清白,当事者供认不讳,按照大清律应把案犯就地正法。你说,这案办得不错吧?”
“当然不错,杀人偿命,案犯罪有应得!”
鱼知府看着更新微微一笑,又摇摇头。
“怎么,是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