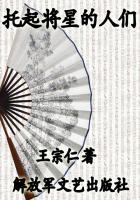一、电报
接到母亲的电报后,我对电报内容产生了严重的怀疑。电报上只有五个字:“父病重速归!”
半年前夏天时,我回家休假一个月,帮家里收割好水稻、播了种才归队。归队前说好明年夏天我还回来夏收。部队一年只有一次探亲假,家里知道这个规定,仅隔半年又让我回家,我猜,要么父亲真病了,要么另有原因。归队前父亲的身子骨还是那么硬朗,他还和我一块儿下地收割水稻,还坚持要挑一百多斤的稻谷,怎么会说病就病了呢?我猜想定是另有原因。
我清楚自己被家人牵挂的原因,已经是大龄剩男了,谁家父母不操心,难说这次把我诳回家不是为这事。夏天农忙那么忙,父母还想见缝插针地张罗这事。农村平时没几个人在家,过年时就热闹了,男男女女都回家过年,赶上以前的庙会,很多年轻人都在这相逢时节成就了好事。我怀着复杂的心情向部队请假回家。
一到家,我就接受了父亲病倒的现实。我前脚一迈进家门,看到父亲那瘦如柴杆的手正掀开蚊帐朝家门张望,见我向他走来,一滴浊泪就顺着床沿边滑落,砸在地板上,砸在儿子的心坎上。怎么会是这样呢?半年前父亲还那么硬朗,他还挑得动一百多斤担子,归队前,他送我到村口时说“别挂念,家中有我呢!”如今一下变成一个垂危的病人,在等他的儿子归来。
见父亲病成这样,我立马要送父亲去医院,却遭到母亲的反对。母亲说过几天就过年了,再怎么说也要全家围个炉,过了正月初四才好出门。乡下人规矩多,过年,就图一家人能团聚,一起吃团圆饭,一年到头,乡下人就奔这个彩头。
我不好过分反对,这时大哥和小弟还在广州因讨不到工钱而回不了家,如果他们此时都没回来,我和父亲又滞留在医院里,扔下一个年迈的老母亲在家,这年怎么过呢?在农村,过年时只有那没了人的空家,门前没人贴对联,初一清晨没人起来开门放鞭炮,没人拜天、拜地、拜灶神,否则,这种不吉利的事是谁都不干的。
到了年三十那天,大哥一家子总算赶回来了,他们留下三弟继续和老板纠缠还没结清的血汗钱。尽管三弟不能回来,但我看得出,今天是我回来后父亲最开心的一天,他破天荒地,平生第一次答应让我帮他先擦洗身子,再剃胡子,然后颤巍巍站起来,在早已摆好的供桌前,父亲先拜了天公,再拜祖宗,拜他往年拜过的一切神仙。这种祭拜要是在往年,我会觉得父亲是按习俗在走过场,但这次,我发现他穿上只有节日里才舍得穿的那套黑色中山装,上下一排纽扣整整齐齐,连同风紧扣都扣得紧紧的。他站在供桌前,双手缓缓地团动神仙的银元,我看他的手在冷风中有点哆嗦,想上前帮他一把,他却示意我走开。他的目光是那样深邃,神情是那样肃穆,一脸凝重,分明是在心间进行一场心灵的仪式,进行他一生中最庄严的仪式,他以六十余载雨雪风霜,凝聚成此刻心灵的虔诚,长时间地默默地向时空作一场生命的对话。
该到一家人围炉吃年夜饭的时候,大嫂早早就把一炉炭火燃得正旺的红泥炉放到八仙桌下,母亲在桌上端端正正地摆了八副碗筷。父亲提醒我,多出来的那副碗筷,算是在广州三弟的份。在往年,这一份是算我的,我听了之后,赶紧朝那空位的碗里斟满酒。按老家规矩,年夜饭开席时,晚辈和长辈之间要互相道贺一声就算开始了,在父亲那场庄严肃穆的心灵仪式后开酒席,一家人不免觉得心情沉重。父亲用可乐代替米酒,他想站起来却又跌回竹椅上,他用杯子先向母亲敬了一下,说:“丽,这辈子辛苦你了,不过日子总会好起来的,你要是看着桌上的鱼呀、肉呀,觉得还吃得动就多吃点。”母亲堆着笑,她和父亲碰了一下杯就匆匆到厨房里盛菜,我转身看到母亲揉了一下眼睛。父亲指着她的身影对我们兄弟说:“她跟你爸苦了一辈子,你们以后要好好孝敬她,要记住她的胃不好,少让她吃剩菜饭,她的视力不好、记性也不好……”正说着,母亲已回到席间,父亲就从交代又变成祝福,他祝福大哥大嫂一家子永远福乐安康,祝福我们兄弟们要永远亲如手足。最后他非常郑重地对我说:“成家立业是一个男人一生中最大的事情,有家才有业,我已无力帮你,你自己多努力吧,不要觉得吃了皇粮就高人一等,以后还要多帮扶你的弟弟……”大嫂早已觉察到父亲跟往年吃年夜饭时的情形不一样,就不断地唆使她的两个孩子跟爷爷碰杯,调节气氛,一家人却都被父亲这似祝福又似交代的话压得直不起腰来。
二、心愿
这个年过得有点沉重,父亲的身子成了全家共同的隐讳。一家人忍到年初四,我就带父亲到县医院检查。父亲做了彩超后,大夫给刚年过花甲的父亲判了日期,少则三个月,多则半年。这个消息如一击重锤,狠狠地向我砸过来。来不及痛,我必须以最平常的表情告诉父亲都是坐骨神经和肺部轻微感染所致,需要先回家调养几天。
我轻描淡写地告诉父亲后,当天就带他回乡下。我另有打算,但此时不能告诉父亲,我必须把他先带回来,先和家人商量才能决定。一家人都无法接受县医院的检查结果,一家人都不甘心。大哥一家人需要到广东处理生意上的事,父亲的病也就委托我全权照看。一家人都筹不出钱给父亲看病,我卖了家中三头猪,又卖了一头耕牛,总算凑齐了4000元。正月初九,我又费尽口舌把父亲从150公里外的乡下,哄到漳州的一七五医院。
县医院大夫只告诉我,父亲是肺部占位性病变,但他没说父亲到底是早期、中期,还是晚期,没明确我就觉得有希望。我希望这4000元能查出一个更准确的结果,如果有希望,我和大哥各变卖一处乡下的新房子,不足部分可以贷款,这是大哥临去广东前和我商量好的事。父亲养育我们没讲代价,我们挽救他的命时也不能讲代价。
再去复查,父亲起初不同意,但说去漳州,他竟同意了。
1978年秋天,父亲被调到离家上百公里外的上峰修水库。父亲一走三个月都杳无音信,转眼三九寒冬,有同村人回来,母亲就托他给父亲捎冬衣,还有一捆咸菜。接到冬衣和咸菜,父亲赶紧到小河边洗咸菜,洗着洗着,他竟从一捆咸菜里洗出一张皱巴巴的、浸透卤水的伍圆钞票。这是一张米黄色的,上面印有产业工人手持钢钎生产画面的伍圆钞票。这张钞票被捻成一截小棍子模样,夹在咸菜芯里,又用菜叶密密包裹,只要不打开这捆咸菜,没有人知道其中的秘密。
父亲知道这张钞票的来历,这是他临走前交给母亲的那张伍圆钞票,这是他留给家里的油盐钱。当时,这是家里仅有的全部现金,够买上六七斤猪肉,可管家中半年油水。母亲竟原封不动地把它塞在咸菜里寄给父亲,她担心父亲整天重体力劳动吃不消,宁肯全家吃斋半年,也要省下这伍圆钱给父亲改善伙食,哪怕往饭盒里添几滴油水也是好的。
父亲不舍得把伍圆钱吃进肚子里,一直藏在身上不舍得花,却在一个闲暇的日子,揣上这伍圆钱,约上几个工友,到20多公里外的漳州城逛了一趟。谁承想,这趟漳州行,竟成了父亲一生的回忆。父亲从不跟我们说漳州城当年景象,却经常说起一对石狮子,那是牢牢镶嵌在他记忆深处的一对石狮子。他说那对石狮子真好看,大青石雕成的,威武生动。父亲没见过真的狮子,他认为真的狮子就该那个样子。最令他感到神奇的是含在石狮嘴里的石珠子,能自由滚动,又牢牢地含在嘴里。父亲说他几次伸手去掏,就是掏不出来。一晃20多年过去了,自己竟会拖着病怏怏的身子骨,被儿子带到漳州来故地重游。
当天,办妥父亲入院手续后,我看他精神头还好,就带他到街上走走。我想让父亲看看20多年后的漳州是如何一派繁华景象,见一次我们乡下人说的大世面。我们穿梭在车水马龙的商业大街上,去琳琅满目的大商场,从胜利路到延安路,再到新华西,九龙公园、中山公园……一路上,父亲像个怕走丢的孩子,像我小时候偎着他赶集一样,一路上紧紧地偎在我的身旁。一辆辆疾驰而过的汽车,一排排拔地而起的高楼,还有光怪陆离的霓虹灯,父亲看得眼花缭乱。他眼里闪出一种陌生与困惑,步子越来越慢,只是不愿停下来。我发现他一直在寻找着一种东西,一直不知疲倦地寻找下去。我不知道他在寻找什么,内心被父亲这惊奇而又困惑的眼神给抽伤了。想想自己在杭州待了近十年,却从未把他和母亲接到杭州玩一趟,当时就建议父亲说:“我们干脆坐飞机去杭州,感受一下坐飞机的感觉,你还可以看看儿子的军营。”父亲经常在田间仰望天上的飞机,带他坐飞机,我想父亲平时做梦都不敢想,谁知父亲却摇摇头拒绝了。我想起父亲年轻时演过戏,他演过《白蛇传》的许仙,又对父亲说:“杭州有白娘子和许仙相会的西湖,正好可以去看看西湖,看是否和戏里演的一样。”父亲又摇摇头,再次拒绝我。我还想建议父亲到杭州治疗,也方便我照顾他,父亲拦住我的话头说:“我只想看看当年那对石狮子,不知它现在蹲在哪里?”走了一个晚上,父亲却只想找到当年那对石狮子,忙安慰父亲说:“那对石狮子一定还在,咱现在就去找它。”
父亲已忘记当年石狮子的具体位置,到底是在哪条街或哪个巷见了这对石狮子,父亲已说不清了,20多年前的事,早已物是人非,这满大街不会说话的石狮子,哪一对是被父亲亲手抚摸过呢?
于是,我雇上一辆人力三轮车,满大街寻找当年父亲抚摸过的石狮子。从元光南路到元光北路,再从胜利西走到胜利东,一条街一条巷去找,每看到和当年模样差不多的石狮子,父亲总要走上前去看个究竟,双手抚摸一番,然后再去掏动狮嘴里的那颗石珠子,最后是一次比一次失落地走开。看到父亲失落的神情,我心里一阵阵难过,就建议师傅带我们去老街区寻找,20多年前的景物如果还在的话,那它在老街区的可能性比较大。而师傅却说20多年后的漳州变化这么大,到哪里能寻到当年那对石狮子?在我百般的讨好中,这位好心的师傅又带我们去了香港路、台湾路等老街区寻找石狮子。一对又一对的石狮子再次朝我们走来,父亲就一次又一次地走上前去抚摸一番,最后一次比一次失落地离开。当晚,我们几乎走遍了这个城市的每一条大街小巷,怎么也找不到当年那对被父亲亲手抚摸过的石狮子。
三、远去的背影
入院第二天,父亲就再也不能出来转了,我和父亲陷入了包围圈一样,陷入了没完没了的检查,陷入了药物的包围,我们被包围在病房里,哪儿也去不成。一天到晚挂着点滴,父亲变得沉默,他只盯着天花板,盯着点滴瓶。头几天,还偶尔和我说说话,有时还会叫我出去买稀饭吃,他被折腾得一点胃口都没有。后来,他连稀饭都不想吃了。刚住院时父亲对我说,人就应该站着像棵树,不怕风,不怕雨;走起来像头牛,四平八稳,耕几亩地不气喘;一躺下来,真跟废物一样,越躺人越困,点滴越挂人越累。
父亲陷在医院已经七天,他什么时候出院大夫没明说,而我必须离开。前一天,我已通知姐夫来接我的班了,我必须离开,一天也不能再耽搁了。我和父亲面临一场人生的生死离别。
我要乘火车归队的那天清晨,姐夫搀扶着父亲,迎着寒风走到漳州一七五医院门口和我作别。我反对父亲送我,但他坚决要送。此时的父亲连站都站不稳,一个星期的化疗,让他彻底萎靡下去,他身上的正常细胞以十倍甚至百倍陪葬在癌细胞身上。只是父亲不知道,他只知道这叫治疗,他不知道自己确切的病因。
初春的早晨凉意阵阵,寒风中,父亲如一盏风中摇曳的油灯,随时都可能被风吹灭,我心中翻涌着酸楚的波涛,多少次都想扔下行装,上前紧紧拥住他,捂住那盏摇曳的枯灯,我心底多么清楚,这是最后一次的诀别了。
可是我不能留下来多陪他一刻,列车不会等我,我必须硬着心肠离去,因我兜里揣着“火速归队”的电报。我一手拎包,一手紧紧捂着隐隐作痛的胸口,硬着心肠正欲离去时,只见父亲正微倾着身子,似乎想挥手告别,嘴角还嚅动着想嘱咐点什么,我又迎上前去,他声音很低:“你安心归队,不用管我,以后要照顾好你的母亲,带好你的弟弟……”话未说完,他已老泪纵横,我更不忍细听下去,还没转身离去,泪水便打湿了我的衣襟。
我想起十年前那次他送我入伍时的情景,他似乎也说过类似的话。那时他的身子骨还非常硬朗,全家重担都挑在他一人肩上。那天,他拎着我的行装默默地跟在我身后,直到村头的大桥边临上车时,沉默的父亲说话了:“到部队要听话,好好干,别惦记着家里,家里有我呢!”说着就拥簇着我上车,看他眼圈一红,似有一根鱼刺梗在我喉咙里,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我是背着一家人去应征体检的,回想两个多月前家里的一系列变故,大姐刚出嫁,大哥刚分家,父亲刚把我们娘儿四人迁回祖籍地那个陌生的地方,母亲还在一次山上拾柴时不小心又摔断了腿。那时家中里里外外多么需要留下我这个帮手,而我却应征入伍了。还是父亲先接到的入伍通知书,那晚我看他在母亲的病床前抽了一整晚的烟,看我在窗前晃了一下,就把我叫进去,说:“男儿志在四方,你走吧!”说着朝我递来那张入伍通知书。在车子启动瞬间,只见两颗豆大热泪在父亲的腮帮子上滑落,一下砸在我的心上,瞬间,我的双眼也变得模糊,我用力朝他挥手,只见他前倾着身子,望着渐渐远去的车子,在努力地挥手,稀疏的额发在风中零散,像风中的芦苇。在一弯又一弯的山路上,我看父亲还朝着远方挥手,直到他身影一点点变小,没入那片松林的斜晖里。
如今的这次分别,他需要在女婿的搀扶下,才能迈着踉跄的步子送别即将归队的儿子。归队前一天晚上,在医院的病床前,我和父亲有过长谈,他说他最放心不下的是我和三弟、四弟三个未成家的孩子,这成了他一桩未了的心愿。
父亲最后说:“你们不说出来,我自己也知道自己的病情,反正我再也不愿花你们一分钱了,唯一遗憾的是我不能把你们兄弟仨拉扯成家。”话未说完,他便转过身去。父亲说完那句似分别又似最后嘱托的话,在晨光中迈着趔趄的步子,在女婿的搀扶下离去,再也没有回头看我一眼,在我的泪光中只留下渐远渐模糊的背影。
我归队四个多月后,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说父亲临走前还念叨着我和弟弟的名字。
2014-08-25于平和小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