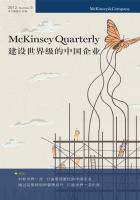营区很安静,静得只剩下几只鸟儿在树上叫唤。
这是前线轮训机场,跑道旁有一条平行的马路。顺着马路远眺,周边的村庄清晰可见。路旁有一排落叶桉,和路排得一样笔直,树上筑满过冬的鸟巢。南方多丘陵,这些高大的桉树是起伏丘陵上的哨兵,它守望着脚下四周大片大片的荔枝林、龙眼林和香蕉林。南国没有冬天,几场薄霜染不上冬的颜色,荔枝、龙眼依然翠绿;跑道旁那大片草坪上的矮草,正冒出淡黄色的嫩芽,空气中飘着青草味,到处都能闻到春的气息,只差几朵花儿就是春的模样了。
不上机场,休息的日子营区显得很安静。连长把大家圈定在营区足球场大小的范围内自由活动。分队长和几个战友正在棋盘上苦战,他们身边围着一堆人。******几位战士在南洋楹树下捉虫子、抽烟,拿着小树枝逗含羞草,看它的叶子一张一闭逗自己开心。我靠在床边看书,大家各干各的自寻乐事。
“当当当——当当当——”金属的撞击声由远及近,穿透了营区宁静的空气。大家纷纷从宿舍跑出来,从南洋楹树下围过来。一位姑娘骑单车朝营区直奔过来,一到我们营房前,她跳下车来,把后轮往上一提,架好车,开始叫卖。她驼来两大框甘蔗,立马成了眼前的风景。
大晴天,南国冬天的日头依旧灼人。姑娘戴着斗笠,头上还垂下一条毛巾遮住后颈窝及大半个脸。上身穿着细花黑白相间上衣,下身穿一条藏青色长裤,把自己穿成一件青花瓷的模样。这么严实的防护下,姑娘还是显得有些黑,双手很粗糙,看得出来,她是长年叫卖的小贩。战士们围上前来不断地和她搭话,从天气、龙眼、荔枝、香蕉,一直聊到甘蔗。战士们的话题很多,且不着边际。
营区一下闹腾起来,指导员和连长也从宿舍走出来,他俩走上前看了一会,返回宿舍。王吉军和几名干部没好意思围上前来搭腔,他们站在走廊上看。几十名战士一块“瓜分”姑娘的两框甘蔗,显得有些僧多粥少,张毅、彭茅几位战士,他们一人就要了六七截甘蔗,姑娘有些忙不过来,她不断地为大家削甘蔗皮,一把小刀在她手中舞得飞快。她的两框甘蔗很快就卖光了,姑娘骑着单车走了。
姑娘一走,营区一下又安静下来,张毅、彭茅他们脸上现出落寞的神情。我们来轮训半个多月了,头回见到一个卖甘蔗的姑娘,这是多新鲜的事呀。可是甘蔗卖光了,姑娘就走了,地上只剩下一堆堆甘蔗渣,营区一下又安静下来,大家又开始干自己的事,下棋、捉虫、看书。
“当当当,当当当——卖甘蔗喽——”才一会儿工夫,这位姑娘又拉两框甘蔗折回来了。这次,她的框里还多了香蕉和菠萝。
战士们和上次一样热情地围上前来。这次大家显得有些谦让,不像上回争先恐后地买她的甘蔗,大家啃完一截甘蔗才买下一截。大家约好似的,只买甘蔗,不买香蕉和菠萝。我们是姑娘眼前的一个个小型榨糖机,一口一口地榨,虽慢,但不停歇。营区里到处弥漫着甘蔗的味道,甜滋滋的。
姑娘卖甘蔗的节奏明显不如前次欢畅。话茬儿却多了起来,聊的还是天气、龙眼、荔枝和香蕉这些不着边际的老话题。其实什么话题都不重要,它只是一个道具,语言的道具。和陌生人接触需要这个道具,战士们不一定明白,却善于运用这个道具。它可以是块帷幔,让人温情脉脉不难为情;还可以是肓人手中一根探路的棍子,敲一敲就能听出对方的反应;它还是一根疏通的导管,能排出身上的毒素。战士们需要足够的时间来巧妙地运用语言这道具排毒。姑娘框里的甘蔗就是他们的时间,他们要放慢框里甘蔗消失的节奏,让语言有更大的施展空间。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和姑娘交谈,用语言拓展出一个大舞台来。
“当当当——当当当——”又有一位姑娘从远处飞驰而来,她也来营区卖甘蔗,她和先来的姑娘打个照面,就在一旁停下来,静静地等着,并不急于叫卖。
两位姑娘都很窈窕。后来的这位姑娘也截斗笠,几乎是一样的打扮,只是没有先来的那位姑娘好看,牙也不齐整,朝外凸,她的脸上有不少粉刺,战士们私下称她粉刺或粉刺姑娘。十几位战士围上前去搭了一会儿腔,却没人买她的甘蔗,一会儿又回到先来那位姑娘身旁继续拉呱儿。粉刺姑娘也不生气,她似乎乐得清闲,笑吟吟很有耐心地在一旁看着。既不吆喝,也不压价,很有耐心地看着、等着。她很有智慧,既能认清现状,还知道属于自己的时机还没到来。先后只是顺序问题,她不争先后,她能把握自己,她知道留下来就是最好的选择。
果然,先来的那位姑娘卖光了甘蔗就走了,她还朝粉刺姑娘看了一眼,带着框里香蕉和菠萝走了。她一走,粉刺姑娘就忙活起来了,战士们无可选择地围在她的身旁,继续拉呱儿天气、龙眼、荔枝还有甘蔗,买她的甘蔗,也买她的香蕉和菠萝,她的生意比先来的那位姑娘还要火。战士们和粉刺姑娘拉呱儿更随便,不局限于天气和水果,他们还谈她俩的村庄,谈先来的那位姑娘。粉刺姑娘不腼腆,很大方地告诉战士们,先来的那位姑娘是她们村的村花。
战士们一阵欢呼,大家有理由欢呼,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能近距离地见到这个村最美的姑娘——村花,多有眼福呀!我不认同什么非礼勿视这一套,好看是给人看的,看了才知道好,还是不好。每个人都有多个符号。内心智慧是一个符号,外观好看也是一个符号。这个符号每个人都可以把它放大或缩小,甚至隐藏。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家都喜欢看好看的。正好,村花每天都来卖甘蔗,还带来了食堂没有的香蕉和菠萝,大家能不喜欢么。粉刺姑娘不来卖甘蔗时,我觉得村花卖的是甘蔗;粉刺到来之后,我觉得她卖的是花,粉刺姑娘卖的才是甘蔗。
从此,村花和粉刺姑娘每天都来营区叫卖,她俩总是一前一后地来。若赶上待命或休息的日子,她俩一天来两三次;若是我们上机场,她们午时、晚时分来,每天都非常准时。战士们谈论最多的还是村花,还总把她和粉刺姑娘相比较,说她的甘蔗、香蕉、菠萝,一直说到她的眉毛、眼睛、鼻子、嘴巴还有她的手。在战士们的嘴里,这些俨然都是村花花冠上的每一瓣,活脱脱跳在眼前,从机场说到宿舍,又从宿舍说到梦乡。张毅、彭茅几位战士俨然成了村花的“粉丝”,他们无时无刻地说村花。村花不但出现在白天,还不断出现在他们晚上的梦境里。村花打破了营区的平静。
几周后,村花就不见了,连粉刺姑娘也不见了。部队不许有人来叫卖,营区内见不到一个叫卖的身影。大家又开始干自己的事,上机场,去食堂,下棋、捉虫、看书,营区又是一片寂静!
2014-03-13于鲁院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