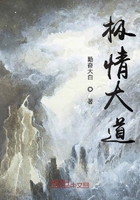已经是四月了,春意盎然,护城河两岸花红柳绿,河岸边妇女们在洗衣服,小孩子放风筝,顾老悠闲地钓鱼赏春。而对宁家来说,劫难过后,满目疮痍。
冬天那场雪灾的后遗症正在显现,据说城外乡下田里的庄稼全都死了,农户忧心忡忡,灾后饿三年,那些精明的商家已经开始囤积粮食,准备在后半年颗粒无收时大发一笔财,一切都表明,眼前的繁花只是暂时,更大的灾难还在后面。
卖了田,宁家真正一无所有了,从前宁放好歹算个小地主,现在只有这座破院了。
这场牢狱之灾让宁放遍体鳞伤,需要一段时间将养,李冶虽然在宁放面前欢喜地笑,背地里偷偷抹眼泪。
宁家现在一无所有,家里用度,治病都需要钱,宁放回来的第三天,李冶就去给大户人家洗衣服去了。
宁放身上最严重的地方是双手,被夹棍折磨得不成样子,动一下就疼,别说拿东西,吃饭都要把碗放在桌子上,嘴凑近吸。
他回家后,第二天就让李冶去府司西狱给邓大打点,贿赂狱卒,邓大身上背着几条人命,想洗脱是不可能,只能让他在牢里少受点罪。
李冶一句怨言也没有,拿着卖田剩下的银子贿赂狱卒,给邓大送去好酒好肉。
如果不是邓大,也许宁放这条命就没有了。顾老那句话说的对,这世上自有一股气,看不见摸不着,却在平衡着世间万物。
过了几日,吴安世让人又送来了几幅中药,还有医书,宁放躺在床上养伤无聊,索性翻阅起来。
舅舅赵秀才不知是不是良心发现,居然破天荒地来看宁放,留下一蓝鸡蛋在宁放鄙视的目光下,狼狈而去。
宁放不是君子,无法忘记赵秀才给姚五当说客买宁家田的事。
转眼半个月过去了,这日午后宁放挣扎着起来,在床上实在太闷了,他搬了张凳子,坐在院子里看书。
春日的阳光暖暖地照着院子,风和日丽,胡同外面菜农和小贩忙碌地路过,认识的就跟宁放打声招呼。
郑秀才提着一壶酒走进院子,自从宁放回来后,他隔三差五就买酒来看宁放。
“郑先生,又让你破费了。”宁放有点过意不去。
“宁公子,说些干啥”郑秀才摇摇头:“都是街坊邻居,令尊在世时没少帮过大伙,唉。”一声叹息。
两人默默喝酒,对坐无言。
赫老夫子自从染上伤感,几个月一直不好,他年岁大了,棋院所有人都为他担心,也在为自己担心。白山棋院之所以能维持下去,全靠赫老夫子的名望,一旦赫老不在了,棋院前途未卜。
郑秀才,范五爷,沈姑姑等人都是无家可归的可怜人,一旦棋院解散,他们只能流落街头了。正所谓一家不知一家难。
大概感到气氛过于凝重,郑先生咧开嘴无声地笑了笑:“宁公子,昨日有件事你听说了吗?”
“先生请讲。”
“听说昨日无痕公子为苏园才女朝云赎身了。”
“哦,无痕公子为朝云赎身,这倒是趣事啊。”宁放放声笑道。
无痕公子和朝云在世人眼里就是一对不通世故的才子才女。两人都是俊秀妖魅,一个痴迷音律,一个痴迷赋曲填词,日日耽迷。无痕公子本是富二代家财万贯,却被家人卷款逃走,经受如此打击,这位公子丝毫没有触动,继续我行我素,只痴迷填词作赋。
这种事在普通人眼里就是茶余饭后的消遣话题,才子佳人,这也算是好结果了。
宁放父母在世时,也是富家公子,常去苏园听曲,四大才女的曲儿都听过,听到这个消息,一时触动,默然良久。
古时青楼女子多数悲惨,但像苏园四大才女这样有名气的姑娘,基本上都能有个不错的归宿。
聊了一会,两人对弈了几局,自然都是宁放输了,输了便不厌其烦地给宁放讲解,哪里走错了,也不管宁放想不想听,旧时秀才的迂腐可见一斑。
宁放就耐着性子听,心里一万个曹尼玛奔腾,难怪渡口的瘸子老段会和郑秀才闹翻脸,谁能受到了这份说教。但在郑秀才心里却认为自己是好心。
宁放双手都缠着纱布,懒得说话,郑秀才讲了几遍,突然想起了什么,回头说道:“宁公子,棋院最近举报培训班,讲解棋道,有空来看看。”
“改日一定。”
宁放平日吃喝嫖赌,斗斗蛐蛐,对下棋兴趣不大,不过自从泼皮无赖姚五的黑背蛐蛐横扫齐州蛐蛐圈后,蛐蛐圈一片惨淡,已经很久没有活动了。反正养病无聊,心想改日去看看热闹。
郑秀才走后,太阳慢慢落下,外面冷了。宁放回到屋里,躺在床上无聊看书。
古代能看的书不多,像什么四书五经,圣人之道宁放从不感兴趣。以前看斗蛐蛐方面的书,现在更多是看吴安世送来的医书。
一个公子哥儿出身,他也没想过去学医,纯属躺着无聊翻看。
晚上李冶回来,在院子里喊:“公子,我买了食为天的馄饨,你下来吃吧。”
“知道了”
食为天的馄饨,清风楼的羊羔酒,徐记茶楼的茶,这是宁放之前最爱的。适合小资家庭,实惠不贵,又体面。
这段时间,白天李冶出去干活,晚上回来都要给他带点吃的喝的。
宁放走进厨房,看见桌上热腾腾的一碗馄饨,馋水流了下来,他往李冶屋里看了一眼,李冶已经关灯睡了。
他想了想,倒了一点出来,吃了一半,另一半用碗盖好,出来说了一声:“这馄饨没有以前的好吃,我有点反胃,不吃了。”
……………
晃眼一月过去了,宁放的身体恢复的很快,保安堂开的中药材效果很好,加上年轻力壮,蹭蹭见好。已经能走出院子了,他在屋里憋长了,闷得慌,这日一早起来信步向河边走去。
春日清早,空气清新,万物生长,菜农们在田里忙碌着,鸟儿在头顶叽叽喳喳。
远处的护城河两岸,草色青青,这是宁放劫后第一次去河边,眼前的一切都让他感到亲切。
河边渡口,范五爷正在和上次那个教私塾的老先生聊天。
瘸子老段懒洋洋地坐在旁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半天插句话,眼睛却瞄着两岸,看有没有过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