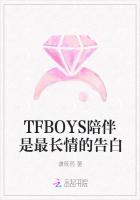李定国说着朝刘文秀笑道:“奇怪了,哥哥我本以为就我痛恨孙可望。但瞧四弟先前声音,似乎比我还要痛恨。”
顿了顿,疑惑问道:
“孙可望平日里虽然压着四弟,但也只是给四弟穿穿小鞋罢了,不像那孙可望曾三番四次想置哥哥我于死地,怎得心里如此痛恨他?”
“孙可望给文秀穿小鞋,处处打压,那不过是小恶罢了,”刘文秀的语气突然严肃起来,道:“但他如今不顾大局,意图谋反,乱我大明朝局,这是罪不可赦的大恶。”
猛地双目直视着李定国,大声问道:“这孙可望的家眷,晋王准备怎么处置?”
原来,李定国和刘文秀将朱由榔救到昆明后,孙可望的眷属仍然住在昆明。永历帝和李定国等人对孙可望对其仁义,一直对他们很是客气,并未将他们视作叛乱家属。
前几日,孙可望还派程万里赴昆明,要求把秦王旧标人马遣还贵州。此事朝廷议论纷纷,各有不同意见。
刘文秀既然如此提问,自然是李定国有此念头。
“原来四弟已经听到风声了,这事哥哥我也是犹豫不决,”李定国笑了笑,道:“黔国公和哥哥我的想法是,孙可望虽然不顾大局,但我们却不能如此,我们要善待孙可望的家眷,要让天下人瞧瞧陛下的仁慈,以争取更多的名声。”
却听到刘文秀突然加重了语气,道:“晋王可曾想过,如果我们将孙可望的眷属羁留作人质,他不免有所顾忌。倘若晋王以礼送往贵阳,那孙可望定然没了内顾之忧,必定会进兵云南。”
李定国道:“四弟的担忧,黔国公和哥哥我都有想过,但若是不送回去,那孙可望就师出有名了。”
他转向朱慈煊,笑着问道:“此事,殿下怎么看?”
朱慈煊谦虚道:“军国大事,学生未得到父王恩准,不便参与。”
刘文秀正想游说,
李定国抢话道:“殿下是未来的皇帝,有什么不可说的?”
朱慈煊望了望刘文秀,见他朝自己点了点头,才笑道:“两位老师是在考学生吗?那学生就胡说了。”
刘文秀笑道:“殿下聪颖,兴许有不一样的观点。”
他虽然知道历史,孙可望会很快叛乱,但他乃是朱由榔的儿子,自然还是需为自己父皇脸上涂金,于是含糊其辞说道:
“学生听父皇说过,秦王虽然对他有不敬之意,但如今我大明最大敌人是建奴,如果可能的话,还是希望秦王能顾全大局。
父皇对于之前的事情也不会追究。”
“陛下仁慈,乃是大明之福,“刘文秀接了朱慈煊的话,夸了朱由榔一句,又忧心忡忡道:”只是孙可望早已经习惯以盟主号令众人,对陛下也早有取代之心,如何甘愿屈居?”
李定国脸色痛心疾首,惋惜道:“昔日义父留下遗嘱,让我们大西军归属大明,共同对抗清军,想不到不过数载,那孙可望便将义父的话忘得一干二净。”
朱慈煊心中一边钦佩李定国的大量(他和孙可望可有数次生死之仇,昔日他取得衡阳大捷,孙可望曾经想派人置他于死地),一边又暗暗叹息:
“都到这时候了,李定国心中还放不下妇人之仁,实在不够腹黑掌控政局。
怪不得击败孙可望后,南明的朝政一团糟,以至于发出呐喊刘文秀怒而道:南明败亡者,在定国。”
这时,刘文秀叹气道:“只怕多此一举,“识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秦王只怕不会回头了。”
朱慈煊问道:“老师,为什么?”
刘文秀反问道:“殿下可曾知道如今西南有多少兵马?”
朱慈煊想了一会儿,道:“以前听老师提起过,学生想着,三十万吧兵马总有的。”
刘文秀道:“若是加上川蜀周边的明军,殿下说得倒也没错。但西南之地,可调动的兵法不过二十来万,而其中孙可望能调动的兵马超过十五万。”
朱慈煊啊了一声,惊道:“孙可望能调动这么多兵马?”说着,眼光望向李定国。
李定国点了点头,沉声道:“孙可望不仅控制了贵州全境,而且在云南留守的将领中也有不少效忠于他。”
朱慈煊又啊了一声,低声道:“前些日子,听老师说,昆明的兵马不过三、四万人,怎得还有效忠孙可望的军队。”
忙追问道:“如今都有哪些将军听命孙可望的?”
李定国瞧了瞧刘文秀,道:“哥哥我初来昆明,对昆明的驻守将士也不熟悉,还是四弟来说说。”
刘文秀苦笑道:“殿下可知王尚礼将军。”
“保国公的大名,学生自然听过,”朱慈煊更加惊讶,诧异道:“学生听父皇提过,昔日接父皇他们入昆明的正是这位王尚礼将军,他也因此从固原侯升为保国公。学生实在不敢相信,保国公居然是孙可望的人。”
刘文秀笑着解释:“孙可望本来就是大西军四大将军之首,昔日大西军进入云贵,又得了御营提督王尚礼和艾能奇部将冯双礼的支持,自然登上了大西军‘盟主’的位置。大西军的将领听命于他,也在情理之中。”
说到这里,冷笑道:
“一直以来,孙可望是云贵之地的实际执政者,若是让他交出权力,听命陛下,他如何甘心?”
说着又苦笑道:
“何况孙可望和你的两位老师都有不同程度不同的隔阂;他以小人之心,自然觉得我们会嫉恨他。”
朱慈煊点了点头,道:“学生明白了。”
刘文秀朝李定国问道:“晋王以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