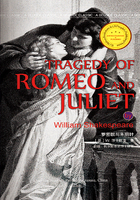海明威生平喜欢斗牛和打猎。在斗牛方面,他虽然只是个看客,但决不是个普通的看客,而是深谙其中三昧,并对其中表现出的人生哲理、美学价值具有深刻的理解,他的两部关于斗牛的专著《死在午后》和《危险的夏天》可为佐证。在打猎方面,他就更不满足于只做一个看客,而是要亲历亲为了。早在1926年,在《太阳照常升起》中,他就表示要“到东非去打猎”。1933年,完成了短篇小说集《赢家一无所得》之后,他开始履行多年前许下的诺言。
1933年8月7日,海明威与第二任妻子波琳·菲佛从哈瓦那坐船到达西班牙的桑坦德,两个月后,于暮秋季节抵达巴黎。11月22日坐“梅津格尔将军号”客轮从马赛出发,经苏伊士运河,入印度洋,分别在赛德港、吉布提港和亚丁港稍作逗留后,于12月8日到达肯尼亚的蒙巴萨港。在那里,他们与应邀前往的好友汤普森会合,雇用了专门陪人打猎的白人专业猎手、当地的导游、追猎手和脚夫等,组成了游猎队,正式开始了在东非的打猎经历。
1934年1月中旬,海明威在去东非的航行途中感染上的痢疾严重发作,大肠肿胀,露出体外达三英寸。根据波琳的回忆,他“每天都要流失近一夸脱的血”。最后,眼看他病得起不了床,白人职业猎手帕西瓦尔的助手订了一架私人飞机,把他送到内罗毕。他在那里得到了很好的治疗,一个星期内便告痊愈,返回猎区。而那架救了海明威一命的私人飞机则令他念念不忘,在他的短篇名作《乞力马扎罗的雪》中,主人公哈里因脚伤未及时处理,引起感染,被困在野外等待救援,乃至去世前的昏迷中,那架飞机又出现在他的梦里,只是这次飞机没能救主人公的命,而是载着他飞往乞力马扎罗山,让那里成了他的归宿。
根据杰弗里·迈耶斯所著《海明威传》(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85年)介绍,海明威此次东非之行共捕获三头狮子、一头水牛、二十七头别的动物(这与本书所记不符)。2月中旬,在肯尼亚雨季来临之前,他们返回蒙巴萨港以北的马林迪海岸,在那里钓了一星期鱼后,正式结束了第一次非洲之行,坐船回到法国,途中在当时属于巴勒斯坦的海法港与专程前往的汤普森的妻子会合,在那里稍作逗留,并游览了加利利海,随后便坐船回纽约,航行途中邂逅德国女明星玛琳·黛德丽,后来两人关系很密切,她尊称他为“爸爸”。
一回到在美国基韦斯特岛的老家,海明威就开始写作《非洲的青山》。写成后先在杂志上连载,后于1935年10月出版单行本,初版印数为10550册。在卷首语中,他开宗明义地宣布,“作者试图写出一本绝对真实的书,为的是看看一个地区的形态和一个月中的活动的格局,如果得到真实再现的话,能不能与一部虚构的作品媲美。”事实的确如此,根据迈耶斯所著《海明威传》的记载,本书所述多为真人真事。比如以陪人打猎为生的白人职业猎手菲利普·帕西瓦尔(即书中的杰克逊·菲利普先生,海明威称其为老爹),此人大有来头,曾陪同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美国总统泰迪·罗斯福打猎。罗斯福曾有专文提到他。在陪海明威打猎过程中,以其军人气质和高贵谈吐赢得波琳的崇敬,与海明威更是惺惺相惜。海明威称帕西瓦尔是他本人的更为高贵的翻版:“老爹是她(波琳)理想中的男人,勇敢,温柔,风趣,从来不发脾气,善解人意,知书达理,像个好男人应该的那样有点贪杯,而且,在她眼里非常帅。”帕西瓦尔也毫不吝啬其对海明威的赞美之词,对他的性格、枪法和记忆褒奖有加,认为“跟他在一起很有趣。他风趣,友好,枪法准。我喜欢他。他有惊人的记忆力,在他给我的信中和《非洲的青山》中把我几年前说的话复述得一字不错”。二十年之后,海明威第二次去东非打猎,又是帕西瓦尔作陪,此时海明威也已是半百老人,他与帕西瓦尔互以老爹相称,而帕西瓦尔更是被尊为“大家的老爹”。作为第二次打猎的成果之一,海明威写出了《曙光示真》,但是直到1999年海明威诞辰100周年之际,该书才由出版社整理出版。
海明威最早是邀他的另外两个朋友麦克莱什和斯特莱特一起去的,但是他们知道他好胜心强,会把原本是度假、娱乐性质的打猎活动变成日复一日的竞争,因此婉言拒绝了他的邀请。结果是汤普森(即书中的卡尔)接受了邀请。麦克莱什和斯特莱特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了:虽然海明威认为卡尔“不苟言笑,温文尔雅,善解人意”,但是,卡尔的运气和打猎技术却令他产生强烈的妒忌。卡尔打到的一头犀牛的小角比海明威打到的那头犀牛的大角还要长,为此海明威感到很不自在,说起话来“就像快要晕船的人或蒙受重大经济损失的人一样”。倒是波琳从中斡旋,劝海明威“请尽力表现得像个人样”。难得的是海明威并不掩饰自己的这种妒忌,而是将它如实写出,表现出一个男人的坦诚。但是卡尔似乎并没有原谅他,因为自从1935年之后,他就退出了海明威的生活圈子,而当波琳与海明威离婚时(1940年。同年海明威即与第三任妻子结婚),他坚决地站在了波琳一边。
海明威一生共娶过四位妻子,他的好友、与他齐名的作家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曾调侃说,海明威每创作一部重要作品都需要一个新的女人。比如,《永别了,武器》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他在意大利负伤后住在米兰医院时结识的护士艾格尼斯;《不固定的圣节》回忆他与首任妻子哈德莉在巴黎的往事;创作《丧钟为谁而鸣》时有第三任妻子玛莎·盖尔霍恩作伴。波琳·菲佛是他的第二任妻子,两人于1927年(海明威与第一任妻子离婚的同一年)结婚。波琳出生于美国的一个小康家庭,大学毕业后曾就职于《克里夫兰星报》、《纽约每日电讯报》等,后来去了巴黎,成为巴黎《时尚》月刊的编辑助理,时常出入时装展览会等高雅场所。难为她拖着矮小的身躯,踩着夹脚的新鞋,跟着海明威在非洲猎区里爬山越岭,寻踪觅迹。她那副楚楚可怜的样子深得当地土人及老爹的同情和敬重,大家称她为“可怜的老妈妈”,海明威干脆在书中将她简称为P.O.M.(即英文Poor Old Mama的首字母缩写),当时两人感情尚好,海明威在书中时时流露出对她的关心体贴之情。
有评家说,海明威对非洲的风景和动物有兴趣,以致还没离开非洲就已经开始怀念它们,并有二十年之后的第二次非洲之行;但是对非洲的风俗和人则没有好感。所以他对非洲打猎的记述表达的只是在接近处于自然状态的野生动物时的那种兴奋心情,而缺乏《死在午后》与《危险的夏天》中描写西班牙斗牛时表现出来的艺术与文化内涵。的确,海明威出于其白人的优越感,对陪他打猎的黑人们缺乏尊重,尤其是那个爱表演的他戏称为加利克的土人,更是成为他极力嘲讽的对象。不过,海明威的这种偏见也不是针对所有的黑人,对于那个叫“垂眼皮”的黑人追猎手,海明威的描写就很客观,甚至带有某种崇敬。而当他们没有当面向为他们带了很大一段路的“罗马人”告辞时,海明威觉得挺不是滋味,并且两次提到这一点。
前面说过,海明威开始东非之行前,刚刚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赢家一无所得》,但是该书得到了许多评论家的批评,为此,海明威憋了一肚子火。在这次非洲之行中他遇到了一个叫康迪斯基的奥地利人,此人自称爱好文学,并称读过海明威早期的诗作,于是海明威就产生了一种他乡遇知音的感觉,与他大谈文学,并对当时世界文坛上的一些知名作家发表了褒贬互见的看法。当然这仅是他的一家之言,我们今天臧否这些作家时,完全不必受他的影响。不过他在分析作家写不出更多的好作品的原因时的一段话,倒是一针见血的:
我们从很多方面毁了他们。首先是经济上。他们赚到了钱。作家只该碰巧才能赚到钱,尽管好书最终总是能赚钱的。当我们的作家赚了点钱,提高了生活水平,他们就被束缚住了。为了保住家业、妻子等等,他们不得不写作,于是就写出了糟粕。这种糟粕并不是故意写出来的,而是因为仓促从事。因为他们明明无话可说或者没有素材却还是要写。……或者是因为他们读了评论文章。如果他们对说他们伟大的评论照单全收,那么看到说他们是垃圾的评论也必定全部吃进,于是就失去了信心……评论家们使他们变得无能了。
看起来这种现象的存在是不分地域和年代的,而且不只是在文学界,在体育界、演艺界乃至其他一些行业,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话扯远了,就此打住,请读者们还是跟随海明威深入到非洲的深山老林,去聆听非洲独特的狮吼捻叫,体验与野生动物斗智斗勇的惊险场面吧。
张建平
写于1999年7月21日
海明威诞辰100周年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