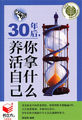带着寒意的春风轻轻吹拂女子素白色的道袍。
去侯府不多的下人们远远的看着张小泉竟生出看到去侯的错觉。
这些下人大部分都是韩国故里的老人,花费了一生追随着去侯。
这种错觉让老人们都不好受。
他们都在怀念曾经三位如龙如凤的小主人。
逝者已矣!
但,他们怕去侯这唯一的孙女重蹈覆辙。
那样去侯会成为世间最可怜的圣者。
院中倒挂着的垂柳在风中摇摆不定,撩拨着他们的心思。
去侯的心思就像那柳条千万根,他们猜了一辈子也没有真正猜懂。
但今天似乎有点不同了。
凭着多年来的感觉,今天的去侯有了细微的改变。
在不抱有期望的时日里待的太久的他们,很明白期望是一件多么弥足珍贵的东西。
此刻,明白了卓一刀话的张小泉也抱有了期望。
“真让人头疼,爷爷那里讳莫如深,又放任自流。就像小时候,他任我惹事闯祸,从来不觉得这天下有什么祸是我不能闯的。这次难道也是?”
她隐隐的感受到了爷爷去侯的改变,只是还不太明显。
但有一点是没错的,她还很年轻。
即便错了,她并不能代表她。
张小泉想到便做,已经着手安排。
“丫丫,去把太后娘娘赏给老太爷的那驾飞辇给牵出来,记得要显足太后的面子。”
张小泉吩咐下去。
不远处的呀呀收到命令如脱兔般开始行动。
这张飞辇去侯一次也没有坐过,从它来到去侯府就放在库房里,已蒙了深深的一层灰。
它更像刁太后对去侯的一次考验。
因为这张飞辇很奢华,用料以及佩饰都极为考究,配着这张飞辇的还有五匹火焰神驹。
天子驾六,诸侯驾五。
但这可是五匹火焰神驹,意义截然不同。
很快,那驾积压了厚厚的一层灰的飞辇被清理的光洁如新。
该准备的火焰神驹也准备好了,该找的马夫也找好了。
“走起!”年轻的马夫甩起鞭子朗声叫道。
张小泉斜躺于飞辇之上,追着卓一刀的方向就是出了侯府。
“年轻总是没有错的,太后娘娘,我今年才十八。”
张小泉自言自语。
…………
去侯府那座幽深且长的深宅老屋,有着春风都化不开的尘埃,日头难照进的高树。
上一次化开这些老旧尘埃的足印便是刁太后带着一碗饭的光临。
光阴荏苒,带着残刀的男子的到来,将这些尘埃再度化开一些。
所以这间深宅那化不开的腐朽的霉味变淡了些。
那么,终日辟谷绝食的老圣人的关于这个世界的看法会不会有些改变呢?
哪怕是一丁点改变,于世界,犹如江河易道,星辰更换。
暗中留意去侯府变化的人都在等待着答案。
他们等的很耐心。
毕竟已经等了这么多年。
终于,他们等到了五匹火焰神驹。
等到飞辇的招摇过市。
等到那个从前很爱闯祸惹事的张小泉斜躺于飞辇之上。
“去侯果然是去侯!”
暗中的赞叹声不断。
那些身居高位已经受够了刁太后主宰世界的人心中明了。
他们更倾向于神圣帝国姓文。
或者说他们更忠心于年轻的皇帝。
此刻,去侯眸子微张,看着帝都最高楼台上的那片天空。
仿佛在回应这些年刁太后的所作所为。
“娘娘,您已经老了,世界是属于年轻人的。”
…………
…………
和亲的队伍穿过极寒草原,抵达草原深处的风雪王庭。
信侯如愿再次见到了这位草原上最为伟大的大漠魔王。
这两位可言朋友也可言敌人的故人彼此对视,竟相互生起惺惺相惜之情。
从前,大漠魔王是一头闻到血肉味道就要拼命啃食猎物的魔狼。
现在,他变成了天空那头伺机而动的血鹰。
因为飞的更高,便看的更远,所以眼中的猎物便更多。
与他那位白痴般的魔王父亲相比,他是一位真正翱翔于天空、星辰大海的王者。
若是这样的王者早生几十年,那么天下大局就不是现在这样的,那场逐鹿天下的戏将会更加精彩,更加残酷。
“魔王陛下!”信侯对着大漠魔王虔诚施礼。
大漠魔王抢先一步,按住了信侯欲跪拜的身子,并将自己的袍子脱下披在他身上,还亲手为其整理。
大漠魔王满是希冀道:“信,上一次我们就约定过只以朋友相称,没有君臣之别。”
大漠魔王的动作很快,很自然,容不得信侯有反驳,魔王的袍子已经穿在信侯身上。
所有人都看在眼里,都对信侯投来羡慕的眼光。
大漠魔王亲自躬身为信侯引路:“信,你能来到风雪王庭,我就满心的高兴,只要你来,便是我最尊贵的客人。”
对于一名君临草原的王者来说,这种礼遇应该可以说是最高级别的吧!
但,信侯并不买账。
“魔王陛下,您的盛意信心领了,我们终是两个国度的君与臣。并且,在这个时候,信以为必须加强公主所住寝宫防范。”信侯正色道。
那些让他伤心欲绝之人还在这个世界上。
那些愚蠢的人还可能继续为那个强势的女人抛头颅洒热血。
风雪之城不全是魔族,还有相当多的人族。
他们还是有机会将这次和亲之旅给毁了。
“信,是我失言了。你一路旅途劳顿,先作休息,公主寝宫已安排妥当,确保无虞。”
从头到尾,大漠魔王对信侯礼遇有加到了极致。
极寒草原太缺像信侯这样的智者。
虽然隔着两个国度遥远的距离,但这位魔王依然想用真心以及诚意来打动对方。
哪怕现在还不能够。
但他相信付出了总能够有收获。
他相信未来的某一天就有可能打动他。
总之,他愿意去做,以及等待。
信侯告别大漠魔王走在风雪王庭的雪夜里,他不担心东胡与月氏安插在风雪之城的奸细。
他最为担心的是那位追随他十六年的副将。
雪很大。
这雪能不能熄了他的野心,是个未知之数。
于是,他走着,走着,来到了副将薛安之休息的房间。
“王庭这么大的风雪也熄灭不了你的野望吗?”
信侯出现在副将休息的房间。
房间的窗没有关,外头的风雪飘进,乱作一团。
薛安之在磨剑。
他的剑很亮。
在烛光的反射下似一道流星。
薛安之起身,收起剑与磨剑的石,一脸平静的的看着信侯。
“侯爷,我不得不提醒您,您这是在引狼入室。”
薛安之的眼尽是风雪是熄灭不了的野望。
“你觉得我会叛变?放弃自己的家与国。”信侯在烛火的倒影里反问。
“便是我死了,您在这里的一举一动,甚至是一言一语都会有模仿者在那位大人面前演绎。所以,‘我觉得’这是根本毫无意义的。”
“风雪可能让人迷了眼,但又怎么可能迷心?”信侯心明眼亮。
“天平从来都不会永远倒向某一方,只要砝码变动了,它倾倒的方向就会改变。”薛安之道。
他现在的心很平静。
因为他马上要去干一件大事。
每遇大事都要平心静气,才能处变不惊。
“当大漠魔王这边的砝码不断增加时,天平的趋势就会悄然发生改变。如果这个时候,帝都那边的砝码再减少,那结果将如何,侯爷您不会不知道吧!”
“的确有这个可能。可是,你不觉得正因为如此,帝都那边的砝码只会增加不会减少,不然就是活活的逼我走。”
目光稍微长远的人都会思虑到这层,不会轻易去猜忌。
也不会去做让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可是,侯爷您有没有静下心来想,您这样态度只会适得其反,让某些人反感。当然,我知道我的下场一定不会太好,我只是虔诚的希望您的下场也不会太过难看。”薛安之真诚的说道。
“这便是你给我的忠告?想告诉我,毕竟十六年的感情,不是一句话就能烟消云散。”信侯带着丝丝怒气说道。
“您视我如子,我亦视您如父。只是您老了。”
“你究竟想要得到什么?”
信侯望着薛安之的眼睛。
薛安之这个名字就是他起的。
安之,取之于,既来之,则安之。
于世界而言,我们既来之,则安之。
但他的野望太大,注定无法安之。
薛安之也看着信侯的眼睛。
他的眼睛里有光芒照耀。
“所有人都说神圣皇帝早年揭竿而起是个百花盛开的年代。”
“可惜的是,我错过了。”
“我是这么想的,那么,就让我所在的年代百花盛开。”
当薛安之说出这些话的时候,烛火映在他眼眸里,跳跃着。
“我的心就像这烛火,风雪再大,也覆灭不了它燃烧的欲望。”
薛安之将窗关好,整理思绪,带上佩剑。
就像从前他上校场那般,接着,对着信侯抱以虔诚的微笑,“我知道我在做什么,还请侯爷不要阻拦。”
他要去杀隐月公主。
薛安之熄不了野望,用年轻的身体投身风雪中。
信侯看着摇曳的烛火,回想起十六年年第一次见到那个孤苦无依的少年。
他看着他食不果腹,看着他的倔强,看着他十六年来点滴的成长。
信侯第一次觉得自己或许真的老了。
“年轻,就真的那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