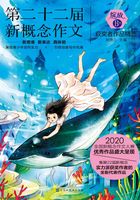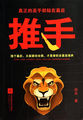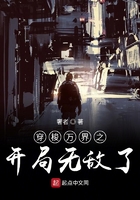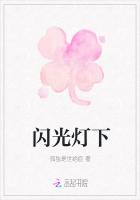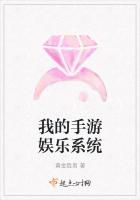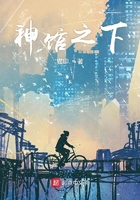赵守玉陈婧
小满半个月后就是芒种了。“芒种忙忙种”,在清原县,芒种又叫“安苗节”。人们用新麦面捏成五谷、六畜、瓜果蔬菜形状的“安苗包”,作为祭祀供品,祈求五谷丰登、家旺人和。这天,一切准备停当,百姓们照例推举年龄最大、威望最高的由敬民老汉牵头,带着几位乡亲去县衙,拜请知县刘玉柱大人和大家一起祭祀、安苗。
可当众人来到县衙,却见知县刘玉柱带着管家刘安急匆匆地走出来回话:“老人家,各位乡亲,今天安苗节,本县理应前往,义不容辞。可是非常不巧,刚才老家来人,说我老母病危,命我速速回去。我让管家刘安代替本县如何?”
众人只得答应下来,和管家刘安一起送刘知县出了东门,转身向设在西郊的安苗节拜祭台赶去。
刚刚走到一个街口的转弯处,人群后面突然一阵喧哗,一匹快马发疯般跑了过来。刘安眼尖,吃惊地喊道:“刘和,你怎么来了?”原来又是刘知县老家来人。
一见管家刘安,刘和急忙甩镫下马,一把拉住刘安说:“刘安,少爷在哪儿?老爷病危,老夫人命我专程赶来,叫他速速回乡。”
由老汉一愣:“刘大人不是说母亲有病吗?我们刚送走他,怎么又说是父亲病重,让他回去?”
刘和说:“老夫人好好的呀!家里就派出我一个人来……他既然回去了,我刚才怎么就没有碰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刘安的眼泪一下子淌了下来:“少爷……少爷他根本就没有回家……他,他怕百姓们为他担心,出了东门就绕道进京了……”
“绕道进京?进京干什么?”由老汉一把抓住刘安的胳膊:“刘管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刘安长叹一声,说起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半年前,清原县遭了百年不遇的大旱,颗粒无收。百姓忍饥挨饿,好不容易熬到了寒露节。小麦要下土了,可种子没有着落。眼看百姓们在死亡线上挣扎,刘知县早就心急如焚,他曾三次上奏朝廷,请求赈灾。谁知三份奏折如同泥牛入海,一直没有音讯。怎么办?刘知县决定向其他府县告急求援。几天后,一车一车麦子运到了清原。老天终于开了眼,这以后一直风调雨顺,可就在老百姓们喜庆丰收的时候,刘知县大难临头了!
说到这里,刘安已经是泣不成声了:“知县老爷哪里是回家探亲?他是奉旨进京领罪的啊!”
人们闻言无不吃惊:“进京领罪?知县老爷犯了什么罪?”
刘安摇摇头说:“你们哪里知道,那些麦种……哪里是借来的,全是库中官粮啊!私动官粮,是杀头之罪呀……当初为了遮人耳目,他让我们连夜悄悄把库里的官粮运出县境,然后拉回来分给大家。只想着粮食打下以后马上补足库存,谁知还没有来得及这样做,朝廷就得到了消息。”
晴空里一声炸雷!大家又感动又着急,流着泪,嚷着要把刘知县追回来。由敬民老汉一摆手,大声喊道:“千万不能追他回来!抗旨不遵,罪加一等,这不是害他吗?乡亲们,都听我的!”
好个由老汉,先是派人请来县里最好的郎中,和刘安、刘和一起赶回老家,为知县大人的老父亲诊病,而后带着大家急急来到安苗祭祀现场,当众宣布了刘知县的事,台下四乡八镇的百姓立刻沸腾了。由老汉当场写下“万民乞命书”,在场百姓全部签上名字。随后选出百姓百人作为代表,在由老汉带领下,昼夜赶往京城。
刘玉柱果然被判了斩立决。刑场上,他背插亡命牌,披头散发跪倒在地。户部尚书俞权亲自监斩,两名刽子手扛着鬼头刀严阵以待,只等午时三刻,便要行刑。
突然,围观的人群一阵骚动。一大群外乡的农民披麻戴孝,大喊大叫着挤进场子,正是清原县赶来的乞命百姓。他们抬着桌子,拿着香烛供品,在断头台对面摆好,一声吆喝,齐刷刷地跪下,向着刘知县磕起头来。
监斩官俞权大吃一惊,忙令旗牌官过来喝问。
由老汉抬头看了看他:“我们全是清原百姓!刘大人是为了救民饥荒,为了百姓活命才触犯刑律的。所以我们在此设台,为刘大人乞命求情!”
刘玉柱猛地抬起头来,睁开眼睛,热泪滚滚地说:“由老伯,众位乡亲,不可呀!你们请回,请回吧……”
由老汉高声回答:“皇上若不准情,我们决不离开!”
“反了,反了!”俞权勃然大怒,拍案叫道,“那些刁民速速离开,否则乱棍打散!”
这时,忽听场子外面一声高喊:“皇上驾到!”原来,早有人将刑场突变飞报进宫了。
皇上下了龙辇,在监斩棚里落座,向为首的由老汉问话:“你等为何如此,且向朕讲来。”
由老汉向上磕了一个头,声泪俱下地说:“每年的安苗节,我们的知县老爷刘大人都要和清原百姓们一起安苗,并吃下第一个安苗包。他与百姓情同鱼水,对待我们恩重如山。可是今年刘大人无法和我们一起安苗了。我们只好抬上供品,赶到京城,送他上路!”
皇上点了点头,起身离开座位,看了看桌子上那些供品,说道:“难得一个七品知县,竟能如此体恤民情,与民同甘共苦。拿来一个安苗包,朕也尝尝!”
“陛下不可!”监斩官俞权急忙抢上一步,说道,“此等山野刁民,万万不可轻信。先让微臣代万岁尝上一尝……”
“大人……你不能吃啊……”跪着的由老汉急忙摇手阻挡。
俞权用手一指,喝道:“放肆!小小的七品县令吃得,难道老夫吃不得?”说着,从供桌上抓起一个安苗包,三两口咽了下去。
皇上问道:“老爱卿,味道如何?”
“陛下……”俞权嘴巴张了张,忽然脸色大变,捂着肚子倒在地上,七窍流血而死!众人大惊失色,皇上龙颜震怒:“大胆刁民,竟敢包中藏毒,图谋不轨!给我拿下!”
御前侍卫如狼似虎扑上来,由老汉竭力挣扎:“万岁,草民死不足惜,肚里的话不能不说啊……”
皇上怒道:“死到临头,你还有何话讲?”
由老汉说道:“我清原百姓结队进京,早将生死置之度外。我们为刘大人乞命求情,哪里知道万岁要来法场,怎么会陷害万岁呢?实不相瞒,这桌上的安苗包,我们都是为自己准备的啊。除了中间那个春牛形状的之外,其余一百个,全都下了剧毒砒霜。只要入口,绝无生还之理。”
皇上大为吃惊,诧异地问:“这是为何?”
由老汉说:“清原去年大旱,颗粒无收。刘大人心急如焚,如牛负重,到处奔走,为百姓筹集粮种,才使我们种下了麦子,躲过了饥寒交迫的劫难。全县百姓感恩戴德,那头春牛就是献给刘大人的。倘若我们求情不准,刘大人含冤而死,我等就把其余的安苗包吃下去,心甘情愿陪着刘大人上路。”
皇上沉吟半晌,才说:“百姓能以死相随,可见这个刘玉柱是个爱民如子的好官了。刘玉柱,朕且问你,清原遭了如此严重的旱灾,你为何不上奏朝廷?”
刘玉柱缓缓抬起头来,伤心地说:“万岁,卑职连上三道奏折,请求拨粮赈济,可朝廷并无回音呀!”
皇上皱着眉头说:“拨付钱粮的奏折,该由户部转呈,朕为何从来没有见到过清原的折子?这就奇怪了。”又问,“刘玉柱,难道你和俞权有什么过节?”
刘玉柱回答:“刘玉柱官卑职微,从来没有见过俞大人。不过,本县去年出过一桩人命案子,案犯是富绅景盛源之子,俞大人曾经给卑职去过一道手谕说情,卑职不敢徇私,不曾理会……”
就在这个时候,人群外面突然一阵骚动,传来凄厉的哭喊:“刘大人,是我们害了你啊……”
“何人在此喧哗?”皇上正要派人查看,三个人已经从人群里挤了出来。
刘玉柱猛地一愣,其中一人竟然是他的管家刘安!
刘安趴在地上磕完头,擦了一把眼泪说:“小人刘安,是刘大人府上管家,这位是我在清原的拜把兄弟张丰,这位是张丰的儿子张庆,在景盛源府上做事。去年我家少爷私自动用官粮,全是小人带着几名衙役干的,做得极为隐秘,怎么会走漏了消息?我苦苦思索了两天,终于想起来了。一个多月前,我曾在张丰家,和他父子二人饮酒,酒醉之后口风不严,把这件事情泄露出去了。哪里想到景盛源早就在算计刘大人,他听说刘知县私动官粮的消息以后,如获至宝,马上修书一封,派人星夜赶到京城,送给了私交甚好的户部尚书俞权。我家少爷就这样大祸临头了……”
水落石出,真相大白,皇上拍案喝道:“大胆俞权,徇私枉法,不顾百姓生死,罪有应得,死有余辜!”随即命人赶奔清原县,捉拿景盛源到案严惩。刘玉柱私放官粮,但事出有因,功过相抵,封为安苗侯,进京供职。由敬民重情重义,赐号‘安苗翁’。上京百名百姓不顾生死,伸张正义,各赏银百两。
第二年的芒种,清原县又举行了隆重的安苗节。皇上亲率满朝文武前来,和百姓们一起安苗。祭罢,皇上拿着一个安苗包,语重心长地向文武百官们说:“自古民以食为天。百姓重稼穑,事农桑,无苗则心不稳,心不稳则民不安。百姓即国之苗,大家都吃一个安苗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