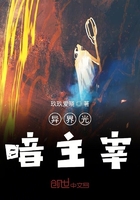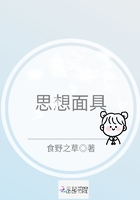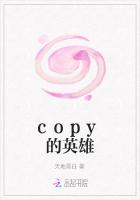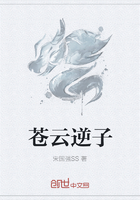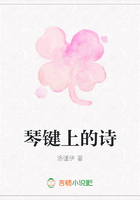江淮丘陵地区也是我国冬小麦的主产区之一,但面积和产量与黄淮平原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江淮之间以微丘为主,也有一些低山浅壑,像北宋欧阳修咏醉翁亭的滁州琅琊山,就不仅有山,而且有名了。
起伏的微丘使乡村的风景看上去富有层次和动感。从乡野的某些高点,也就是岗顶,放眼望去,田地都是小块的,因地势而成形、增减。因为今年春夏干旱,池塘里的水都干涸了,但蒲草之类长相旺盛,树林掩蔽的深渠里的水流也一线仅存,水渠尽头的排灌设备已经弃毁,空余了砖石水泥的机房在浓荫密叶之中。灌满了水的稻田里的水泥电线杆上的广播喇叭突然发出了声音,原来是镇广播站开始广播了,先是一段《东方红》音乐,接着反复宣读市环保局通知,不准就地焚烧秸秆。田原里的庄稼并不十分惹眼:黄熟的是冬小麦,这里半亩,那里三分的;可能因为品种的不同,有的地块已经收割了,有的地块正在黄熟,有的地块却还夹青带黄;油菜基本上收割结束了;真正青葱的地方是低洼地里正在发育的中季稻秧。过了淮河,粮食生产就由以冬小麦为主过渡到以水稻为主了,再往南一些,到沿江平原(长江圩区),那里还是冬小麦的生产区,但一定是副生产区了,对全国冬小麦产量的影响比较有限,气候也越来越不适宜冬小麦的生长。另外,从冬小麦冬季覆盖裸地以防大风掠土、耕地损失的功能看,沿江甚至江淮的冬小麦种植都不那么必需,因为这些地区降雨量较大,空气湿度相对较大,裸露的土壤不会那么轻易被风吹走,此外,还有油菜等农作物可以替代。
2011年5月22日上午雨水下得较紧之前,我走完了吴山镇镇西视野里看得清的麦田和岗地。今年从春天在河南南阳见到、摸到、拍到麦苗后,我还一直无缘近距离与小麦相对,这甚至成了我今春、今夏的一块心病,总好像有一种事情没有做到,有一种承诺没能兑现,有一种愿望没能完成。现在,我终于蹲在地头,触摸到了已经黄熟的小麦,细看它的麦穗、麦芒和麦秆,还观察了麦根处黑黄色的土壤,我立刻如释重负,变得坦然起来。这里小麦的长势似乎并不特别好,大面积宏观和具体微观地看都不像淮北平原那样麦浪翻滚、穗大粒沉。这也是预料之中的状况。谁叫黄淮地区既是丰厚坦荡的平原,又是北纬35度左右小麦最适生长区呢?中餐我吃了当地的烧饼和(中式)面条。这些汉文化区域的传统面食,应该都是中筋面粉生产出来的。但我不知道镇外我看到的那一块田地里,种的是做面包等西式面点的硬质高筋小麦,还是生产饼干等食品的软质低筋小麦。大多数消费者都不会,也没有兴趣去关注表层现象背后的专业和技术支撑。
我们在夏日的田野里面对的麦浪涌动,不仅仅是面对自然地理和农业地理结合的风景,更是面对我们特有的农耕历史文化。小麦基本上可以肯定是舶来之物,不过谁也无法确切地知道它是怎样舶来的,从地中海沿岸到太平洋西岸,也许是一阵风,又一阵风?也许是一只鸟,又一只鸟?也许是一个人,又一个人?都不知道。是一个谜,或一个神话,也正是想象、科学和文艺的起点。
2011年5月23日晨,我在安徽省长丰县吴山镇镇外一个看得见菜地、行人、小块黄熟麦田,菜地、行人和小块黄熟麦田也看得见我的极简易旱厕上厕所。上隔壁简易女厕所的妇女不时从我面前经过。我得一直保持着淡定。不过,我已经十分不习惯这种原生态的如厕方式了。俄顷,隔壁的女厕所冒出了浓烟。起初我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故,后来看见一切如常,我才醒悟那可能是驱除异味的一种“偏方”,一种因地制宜的乡土方式,或传统乡镇的一种日常生活技能。
在这个时节,黄河南北的冬小麦,都还只处于“小满”状态,到6月上中旬,那里才会陆续开镰收割。
2011年5月23日 长丰县吴山镇合淮旅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