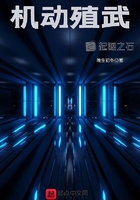且说瑞福晋自秋狄回来后,自感无聊,便邀请一众官家小姐夫人去她家院子听戏。看似是女子简单嬉笑之会,实则是想邀请白苏家的夫人高氏与小姐落棠前去,好让她们俩人能有机会与她的小儿子见见面。落棠知道瑞福晋的意思,断然是不肯去的,白苏大人与高氏自然是愿意的,若是落棠博得瑞福晋喜欢,有意与他家作亲,这自然是美事一桩,所以他们夫妻二人连劝带拉地让落棠上了马车。落棠才不管瑞福晋会不会喜欢她呢,她只想知道茵姐姐会不会去。
马车没多久便来到瑞王府的侧门。几个婆子丫头迎了出来,笑道:“夫人来了,刚才大福晋还念叨着,担心您和小姐不会来呢。”高氏笑道:“福晋不嫌弃我们身份低微,有意相请,我们怎肯不来呢。还劳烦嬷嬷在此等候,真是过意不去。”婆子笑道:“夫人哪里话,奴婢们能见到夫人小姐一面,也不知是修了多少的福气。”高氏笑了笑,任由几个婆子带领进去了。
落棠见那几个婆子,实在不喜,努努嘴,不肯挪步。一旁的高氏早看出她的心思,拉过她的手压声道:“听话,不过是半日时间,何必这样?惹得别人笑话。让你阿玛知道了,仔细一顿打。”
阿玛才舍不得打我呢。落棠不情不愿地跟了进去。
那婆子是瑞福晋身边的人,自然是知道瑞福晋的意思,所以对落棠是万万不肯怠慢。一边儿在前头引路,一边儿有意儿无意儿地提起小贝勒。“今儿个真是巧,咱们小贝勒也在府里,前儿个到福晋那里请安,知道福晋请了夫人和小姐来听戏,高兴的和什么似的,书也看不下去了,还得王爷发火,才肯去书房。今儿个一早,康亲王府的世子来请小贝勒去赏画,他也不肯去。”高氏看了看落棠一脸不在意,笑道:“那可真是太好了,小贝勒与我家落棠是见过几次面的,每回见过面回来了,落棠也是念个不停,说小贝勒为人处世极好。”落棠眼见母亲睁眼说瞎话,但在外头,实在不好驳了母亲的面子,所以只是看了母亲几眼。
那婆子听了,更是来劲了,又是一个劲地暗示小贝勒对落棠的意思。“小贝勒也是,他常说落棠小姐长的很是标志,为人又机灵。夫人要知道,我家小贝勒向来不肯轻易夸人的,他肯这么夸小姐,可见小姐非一般平常女子。”人常言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到了落棠这可就变成说者有心,听者无意了。那婆子不时用余光扫一眼落棠,希望她听了后,露出笑容。可是落棠只顾打量周边景色,似乎并不在意她说什么。
那婆子顿觉尴尬,又见已到后院游廊,便领着高氏和落棠绕过游廊,去了后面的拂绿楼。登上楼,早有一众官家夫人小姐坐在那里看戏了。落棠看了看楼下搭的戏台上正在唱道:“姐姐,你停针不语,却是为何?”“我停针不语身倦怯,觑著那画眉帘外日儿斜也,刚绣的来一对锦蝴蝶。”“姐姐既然身子困倦,向花园里散散心儿罢,只管绣些甚么?”“听,听声声巧鸟双弄舌,道则么有甚关情也,走向空庭把花自折。”“不是飞红多口,姐姐,我觑你近新来呵,”……
高氏带着落棠,先是跟着去拜见过瑞福晋。瑞福晋笑道:“你们可来迟了,我们等不及,便先点了一出戏。”高氏道:“都怪小女,听说要来瑞王府,高兴的和什么似的,左试一套衣服,右试一套衣服,生怕穿的不好看,惹得别人笑话。”落棠站在后面气的直发抖,她阿玛和额娘就是这个毛病,一旦想要和谁套近乎,总要说一些假话来逗得别人高兴。
瑞福晋看了落棠几眼,笑道:“落棠生的好看,穿什么都好。瞧瞧这身量,这模样。怪不得外面的人都说你白苏家生了个嫦娥模样的姑娘。如今我看来,却是比嫦娥还美上十分呢。”一旁的婆子笑道:“可不是,难怪小贝勒爷天天提起落棠小姐。这落棠小姐出落成这样,莫要说小贝勒爷,就是奴婢看着都喜欢。”
瑞福晋站起来,拉过落棠手去,又细细打量一番,笑着吩咐道:“得亏你提起,我倒忘了,你去将皓儿叫来,今日不必读书,若是王爷问起,就说是我的意思。”嬷嬷们答应着去了。
瑞福晋又问了几句话,无非是平时爱吃什么,女红如何。都是等不到落棠开口,高氏便急着回答了:“她平时就爱在屋内做些刺绣活,不大爱出门。就连平时的赏灯花会也是不肯轻易出门的。”瑞福晋点了点头,似乎很是满意。落棠已经习惯额娘的谎话了,便扭头去找寻锁茵的身影。四处张望下,看到锁茵正坐在不远处的一张桌子上对着她笑,很明显,锁茵已经看明白她们几人的心思了。她锁茵用手轻轻招了下。落棠扭头对瑞福晋道:“福晋,我想去看看荣福晋。”瑞福晋不自然地笑了笑,“好,你去吧。”
落棠迫不及待地跑到锁茵身边,坐下来道:“真是讨人厌,好好地要人来看什么戏,这个天,坐这么高,也不觉得冷?”锁茵拿起一个果子给她,笑道:“我看你额娘似乎很是愿意攀上这门亲事。依我看,这门亲事着实不错,门当户对。”落棠冷笑道:“哪里好?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哪里……”哪里配得上长枫哥哥?话到口边,便不好意思地住了嘴,“他们这是一厢情愿,反正我是不会同意的。”
“你这丫头,你同不同意有什么用,还是得看你阿玛额娘的意思,他们若是愿意,强逼着你嫁给小贝勒,你还能怎么办?”一旁的人早换了一杯茶上来,锁茵一面吹一面问她。
落棠一愣,这是她没有想到的,若是父亲母亲强迫她怎么办?对方又是有权有势的王爷,是皇室,她该怎么抗拒?天啊,她难道真的要嫁给她眼中那个乳臭未干的人?以后跟一个自己并不相爱的人相守一生?这该何其痛苦,何其悲哀?她此生岂不是过的毫无意义?她心中早有了想嫁娶之人,虽然眼下不知那人是何意思,可是她一想到她不能和他在一起,就觉得人生一下子就到头了。她不自觉地咬了咬唇,一时无措、悲伤之感从心口溢出来。
锁茵轻抿了一小口茶水,是西湖龙井,并不是刚才那一杯碧螺春。她看了一眼落棠,见她在出神,便笑问道:“不知这台上的戏是唱的什么?”落棠抬眼看了看台下,只听得一书生唱道:呀,姐姐径去了,怎生发付我也?我到此承舅妗相留,出入堂庑之间,与姐姐时或相遇。见其凝妆正色,不敢轻语相挑。今此倚床长叹,似有动情之意。却才以一言试之,又把他辞拒我,正视逡巡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