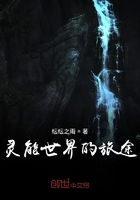伦培尔坐在马车中,身边就像以往一样,只有罗兰菲尔。
罗兰菲尔不知在桌上写着些什么,而旁边那个五大三粗的女仆则不断地把罗兰菲尔已经写好的一叠一叠的信盖上蜡封,然后装起来塞给外面的快马驿卒。
而伦培尔手中,则把玩着一把精致的小匕首,这是他从费迪南德十一世的藏品里,找到的为数不多的好东西。把手握起来十分舒服,匕首本身的长度也正正好好,不算柄的话刚好有手掌的长度。一把锐利且耐用的匕首,是可以很轻松的切开滋油的羊肉那酥脆的表皮的,当然,也能切开别的什么东西。
比如信封。
罗兰菲尔拿过了伦培尔手中把玩的精美匕首,割开了手中一封信的信封,把信拿出来一抖,读了起来。
“谁啊?”伦培尔拿回自己的匕首,顺手从桌子上的果盘里拿了个苹果,削了皮啃起来。
“我在铂勒斯的亲信,公主殿下如是说。”
伦培尔躺在了沙发上,把匕首收回到鞘里“你在铂勒斯还有亲信?”
罗兰菲尔白了他一眼,另一只手写着“允许你和安东、提比乌整天在一块,就不让我在铂勒斯有个眼线了?”
伦培尔显然有些尴尬,他喝了口自己水囊中的清凉饮料“姐,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是谁啊?我不知道,靠谱么?”
“你从骑兵军官还有炮兵军官里找的亲信,我的自然是从商业和财务的官员中选的,”罗兰菲尔一手在纸上写着,另一只手展开了另一张信纸“是阿库耶尔的副手。”
“哦?阿库耶尔,你对他不放心么?”
罗兰菲尔叹了口气,翻了个白眼,把信纸放在旁边,盯着伦培尔眼睛,另一只手在纸上写着“是谁整个风月都在跟我抱怨共和派贼心不死的?”
伦培尔挠挠头,一摊手“没办法,公务繁重,忘了,忘了。”
“要说公务繁重也是我公务繁重,你繁重什么,”罗兰菲尔像是被伦培尔滑稽的动作逗笑一般,在纸上写道“差不多是时候了吧。”
伦培尔收起那副云淡风轻的样子,拿过手头的指挥刀,挑开窗帘,看了一眼“黄昏了,差不多了。”
他走下马车,看了下眼前的三位将军已经笔直地站在马车的门口,伦培尔点点头“就在几个小时前,南路军回报称,敌军已经撤离了特里古奥城墙的南段,经过游击哨确认,敌人的南路军正在向北支援敌军由他们的国王,也就是所谓的奎达率领的北路军,预计在几天之后,就会到达。恐怕当时,会爆发敌人对第二面城墙的全面进攻,我们需要在那之前整合整个瑞齐克-亚历山德拉的战斗力。”
“是!”三名将军又一立正,靴跟碰撞发出了清脆的声音。
伦培尔看着三名将军,点点头。
“提比乌!”
“是!”
“你率全体胸甲骑兵前往敌军城北金顶宫卫戍大营,尽可能不要杀伤敌人,以缴械为主,有反抗倾向的,一律斩杀。”
“是!”
“塔乌斯德!”
“是!”
“你的任务比较重,指挥五千骠骑兵和三万线列步兵封锁阿罗尼亚的几处首都军火库,然后尽可能的把城里的人集结到金顶宫前的广场上,能做到么?”
“能!”
“好,安东!”
“是!”
“你,带着掷弹兵团,急行军,控制敌人的西城大营和南城大营!”
“阁下!请问是掷弹兵团还是近卫掷弹兵团!”
伦培尔被他问得一愣,然后正色道“你把我的近卫掷弹兵也带上!我自己留一个中队就够,你办事我放心!”
“是!谢谢执政官阁下的信任!”
“全体做好作战准备,落日后开始行动!”
“是!”
三位将军急忙朝着自己要去的军种的位置跑了过去,而伦培尔坐在马车前,看着太阳。
阿罗尼亚人留在自己大营周围的人,不管是不是眼线,他都让营地周围的游击哨清理掉了,而通常情况下,探子被敌人发现干掉,是至少一整天后的事情了。也就是说,他清理的这些探子,应该不会妨碍自己的行动。
在两个小时前,他曾派数十人骑快马武装从城外奔入城内,告知阿罗尼亚女王敌人可能攻城的消息,但是快马回来的时候,他们报告称,一路上并没有任何警卫阻挡他们。但是,自己带一个中队,也就是三百人,可能的确有点悬吧。
太阳慢慢地沉入西方的地平线下,火红的霞光仿佛把整个城市还有那四棱锥形的金顶宫泼上血一般。传闻那金顶宫最顶上闪光的一部分,并不是和下面一样是沙砖,而是真正黄金打造的顶。
太阳落下时,光芒就像从那巨大的金顶宫下散发出来一般,但是当太阳彻底沉入地平线时,那金顶宫也和黑夜融为了一体。
“近卫掷弹兵‘旗手’中队。随我出击。”
弗伦索西亚军的驻扎地实际上和瑞齐克城距离很远,至少和他们的所谓第三面城墙有至少五公里的距离。伦培尔实际上对这座城市,对阿罗尼亚人很是鄙夷。因为如果是弗伦索西亚的城市,五公里以内出现了任何在夜里以行军速度行进的武装集团,城市的警钟都会立马响起,给附近驻扎的军队准备时间。
他骑着马,身后跟着排成六列纵队的近卫掷弹兵,在大路上以三倍行军速度朝着城里前进。没多长时间,就到了城门口,但是没想到,却被门口的门卫一横枪拦了下来。
“什么人!”
“弗伦索西亚执政官,前往金顶宫,和女王陛下协商御敌事宜!”
“你带这么多人干什么?”
伦培尔一时语塞,他根本就没想到门口的门卫有胆拦他,此刻真是不知道如何是好。
“你等我去禀报一声。”
这时,一个行伍中的掷弹兵走了出来,抡圆了胳膊给那卫兵扇了一巴掌“你这腌臜东西!吃了几天肉就不知道屎是什么味儿的了是吧!执政官阁下和女王商议事宜什么时候轮得到你这末流野狗允许?”说着,又是一脚蹬在那卫兵肚子上,愣是把他踹得飞出去两米“军机大事!你耽搁得起么!”
行伍中的掷弹兵们看到这一幕,也没出声,只是默默地从腰带上摘下了刺刀,用力的卡在了背后背着的火枪头上。
那被踹翻了的卫兵急忙站起来,弓着身赔笑,他似乎也已经习惯了被不知哪的贵人一脚踹开“不是,大爷,您看,我这不是执行公务么,您要是有要事,您走便是,我也不敢阻拦对不对,就是例行盘问,例行盘问。”
刚刚那动手的掷弹兵鼻孔一出气,一口痰吐在那卫兵脚边“知道就好,狗眼看人低的东西。”说完,回到了队列中。
伦培尔瞅了后面的行列一眼,清了清嗓子“咳咳,三倍行军速度!前进!”
就这样,一个三百人的掷弹兵中队,从瑞齐克最宽敞的大道一路朝着金顶宫的正门跑去。没有任何人敢于阻拦,一方面是因为天黑,看不清军服,而另一方面,则是城门都放行了,还有谁有理由阻拦呢?
整个大道长约两公里,由城门起,至金顶宫大门终。用了十分钟,众人便看到了金顶宫灯火辉煌的大门。
“什么人!”
门口两个卫兵看到这样的行伍,心里多少也有些发怵,但是能出现在城里的,应该还是友军,所以只是喊了一嗓子,并没有真的提起警备。
但是当他们看到这群人走到自己面前的时候,就后悔了。
蓝色的步兵外套,红色袖口和领口,白色帆布裤子和皮靴,头上戴着金边黑三角帽,帽子上还别着各式各样的帽徽向他们宣示着这群人的功勋。而且,他们的火枪前面,是上好了刺刀的。
没等那骑马为首的伦培尔回答,掷弹兵们便挺枪一刺,了结了两个卫兵的性命。
伦培尔下了马,拎着自己的仪仗剑“六十人跟我来,分六十人封锁入口,剩下的进去肃清所有能看到的人。碰到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记得别下手。”
“是!”
伦培尔拎着自己的仪仗剑,按照记忆的路线,一路走向那金顶宫极尽奢华的宴会大厅。路上,他的近卫掷弹兵并没有给他多少拔剑的机会,碰到人基本上就是挺枪就刺,无论是侍女还是卫兵抑或厨子,都被一刺刀刺死,然后没死透的人可能还会被补上一刺刀。
当他踹开宴会厅的门的时候,被里面的场景震惊了。
阿罗尼亚的王公们,还在喝。
有的在拿骰子玩着不知什么酒桌游戏,有的在打着纸牌,还有的一边喝一边聊着什么。唯独没人在意伦培尔执政官和他六十位掷弹兵的到来。
唯独对着六十位掷弹兵表现出些什么的,是安娜,和亚历山大两个人。他们脸上,是惊讶、嫌恶还有一丝谜一样的嘲弄。但是下一秒,当他们看到伦培尔不怀好意的拄着骑兵剑站在两人面前,而掷弹兵们丝毫没有收起刺刀的意思的时候就明白了伦培尔想做什么了。
“女王,您看,这就是我的财富,”伦培尔微微笑着,大拇指指了指自己背后的掷弹兵“我可以带着他们,在您的首都如入无人之境。”
此时的安娜和亚历山大无比惊恐,他们希望面前这位伦培尔执政官只是想要接管阿罗尼亚,而不准备危害他们的性命。而伦培尔则有恃无恐的凑到安娜面前,旁若无人的解开了她绑在脑后装饰用的紫色丝带。
“抱歉冒犯了,我今天没带丝带,就先借您的用一下,”说着,伦培尔把自己的那微微过肩的长发扎了起来,在脑后梳成一个低马尾“希望您不要在意吧,紫色这么尊贵的颜色,我还想从您那蹭点光彩呢,说起来,紫色是什么染的来着?”
安娜和亚历山大并不敢说话,生怕这句“紫色是什么染的”是一句有什么暗示的语句,他们面面相觑,谁都不敢出声。
“你们不知道么?诶你们不是最常用紫色么?”伦培尔笑着回头看向自己的掷弹兵“你们谁知道紫色是什么染的!”
“报告阁下!是紫螺!一种海边的玩意儿!”
伦培尔点点头,咋了下嘴,回头问道“你什么出身!”
“报告阁下!我是渔夫的儿子!”
“好!祝你父亲的海船永不倾覆!”说完,他又看着面前两个一动不动的人,微微一笑“你知道我为什么敢向你们动手么?”
安娜摇摇头。
“因为你们的军队,不是军队,”伦培尔拿过旁边的一个盛着不知名液体的杯子,喝了一口,发现是酒,吐了出来“你们的军队,连我奥临恩城堡里的女仆都不如,同样的问题,你们问你们的军队,能得出答案么?会有人喊着‘报告!是紫螺’么?不会,因为他们连门都看不好,更别说回答主子的问题了。”
他随便拎了一把椅子。得益于宽敞的空间,王公们似乎还觉得,这些军士是来护送他们回住所的,而伦培尔只是来和女王聊聊天。
伦培尔坐在安娜面前,拔开自己水囊的塞子,喝了口饮料“女王,我的军队里,有渔夫的儿子,有猎户的儿子,有农夫的儿子,也有乞丐工匠脚夫裁缝的儿子。莫说正眼瞧他们了,您这辈子见过他们么?”
安娜又一次摇头。
“嗯,所以说,你不懂他们,你不知道你的人民需要什么,所以就算我砍掉你的小脑袋瓜,然后告诉所有人我是阿罗尼亚国王,他们也不会有任何反应,你知道么?”
安娜的表情变得惊恐起来,她看着面前伦培尔夸张的笑脸和因为笑已经眯起来的眼睛,根本止不住颤抖。面前的这个人,就像是一个恶魔,一个即将将自己彻底吞吃的恶魔,她想逃走,她想跑回自己的床上,睡一觉,然后第二天醒来发现一切只是个梦,但是她颤抖的双脚,似乎并不准备给她这个机会。
“好了,差不多聊到这吧,”伦培尔拍了两下巴掌“旗手们!送各位王公上路!”
大厅中,响起了行伍长的叫喊声。
“标尺三十米,两侧酒桌!全体!投弹!”
王公们有的,被这从天而降的铁球砸到,干脆晕了过去,而有的,则在一瞬间认出了那是什么,马上清醒起来,踢开最近的铁球,朝着不知何处冲去。
晚了。
一切都晚了。
几秒后,黑火药手榴弹的爆炸,席卷了两侧的宴席,断肢、内脏、血浆被炸得到处都是。有的被炸到那大理石的少女雕塑上,有的被炸到四周漂亮的大壁画上,还有的被炸到了安娜面前,就好比那只肥硕的、戴着五个宝石戒指的断手。
安娜终于抑制不住心中的恐惧,高声尖叫着,甩开了脚上带跟的鞋子,一路跑进了走廊,而在她离开后,大厅中真正的杀戮,开始了。
实际上,只有很少的王公是真的被手榴弹炸死,多数,都是被炸断了胳膊或者腿,然后发出杀猪般的尖叫。而掷弹兵中,似乎也不乏杀猪好手,他们果断地将刺刀捅进那些王公们的喉咙,顿时,血染红了桌椅的黄金或象牙把手。
而有的还有能力奔跑的王公,则受罪更大,被一刺刀捅进肚子,然后豁开,之后再捅开喉咙了结生命。他们甚至有机会看着自己的肠子,从肚子中慢慢地流出来。
这当口,伦培尔自然也没有消停,他果断地一刀砍了亚历山大之后,追着安娜的身影,深入到了后面的走廊。他追着安娜的背影,一路追着,手中拎着那把来自紫山的指挥刀。他此刻,似乎不再是什么即将成为国王的执政官或是军队的统帅,他拎着那把刀,就像是一个追捕受伤猎物的猎人。
这位猎人,追着那个穿着紫色金线裙子的女孩,一路绕来绕去,走过无数个走廊和楼梯,终于,看到那个身影闪进了其中一个房间。
一脚把门踹开后,他看到的,是缩在墙角里的女孩和那张很明显属于这个女孩的紫色的床。
他走过去,拎起安娜的领口,丢在床上,而安娜也一脸惊恐的往后退着。
“你不能这么做,我是,我是阿罗尼亚的女王!”
伦培尔哂笑一声,把剑丢在一边,解开了自己外套的扣子“小姑娘,我母亲,梅拉菲尔.奥临恩.佩兰,在我太祖父、祖父一家受奸人毒计遇害之后,继承王位,与我父亲艾福阿比亲王生下我和我姐姐罗兰菲尔后,难产而死。她十二岁登基,十三岁去世,统治了一年。她将叛徒丢进地牢里任他们腐烂,将敌人的头盖骨做成酒杯,就算是这样!就算是这样!”伦培尔不知为何,有些歇斯底里的感觉,他头上青筋暴起,而双手上也是同样,就像一只发狂的被刺到伤口的野兽一般。
“就算是这样!弗伦索西亚的人民仍愿意为她冠以‘仁慈者’之名!当她去世的消息传到每一个弗伦索西亚的城市时,没有人不哀嚎!没有人不恸哭!”他一脚蹬上安娜的床,发出了与他阴柔外貌完全不符的大吼“就连农户的孩子都在担忧,梅拉菲尔女王死了,是不是坏的时代就要来临了!那才是一位君王!一位配得上两千三百万人的泪水的君王!你算什么?戴着黄金、珍珠、紫色丝绸与象牙王冠的婊子!你配叫什么女王?”
他穿着的马靴走到床的一边,拎起安娜,强吻在了她的嘴上,粗暴地吮吸着,但是没过两秒,他就把这个女孩甩回到床上“你自称你是一位君王,一位女王,一位阿罗尼亚这黄金之国的女王!我倒要看看,你配不配得上这顶王冠!你将变成囚笼里的牲口,玩物,我想要看看,有多少人愿意突破重重困难险阻,帮他们的女王重获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