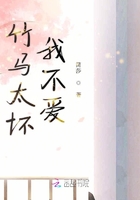高阔华美的大宅院,擘红小榭,一个妇人靠着阑干,穿一件青色对襟褂子,下身是盘金彩绣锦裙,她眉眼如远山,肌肤胜雪,粉黛娇憨。
“清儿,慢些跑,别摔了。”她柔声对着亭榭外嬉闹在花丛中的小女孩说话,眼里尽是温柔,如一池春水。
十二岁的王幼清已出落得极其娇美,细眉弯弯,大而乌黑的眸子莹莹发亮,笑成了弯月,她正和婢女玩着追赶的游戏,她身子娇小,弯腰窜过花丛,直向娘亲跑来,一把扑进娘亲的怀里。
王幼清嘟着小嘴撒娇:“娘亲,爹爹什么时候回来呀,我等着吃爹爹做的长寿面呢!”
妇人轻轻揉着王幼清的小脑袋:“爹爹不是上朝去了吗,晚些回来就给你煮面,你哪一年生辰的长寿面给你落下了?”
“可是爹爹去了好久了,是皇帝叔叔把他留在宫里吃饭了吗?”
想起爹爹,老是一大早上朝,别人的爹爹都回来了,就自己爹爹总是接近傍晚才能回家,她每次都问,爹爹都说皇帝叔叔要留他吃饭,皇帝太寂寞,想要有人多陪陪他。
小孩子不满地嘟囔:“怎么每次都让爹爹陪,皇帝叔叔真不懂事,明明姑姑也在宫里……”
娘亲笑得开怀,双手把王幼清抱到膝盖上:“真是个小着急~”
突然天空一阵“轰隆”声响过,惊吓了娘亲怀中的王幼清,不过一会,大雨倾盆,下人们慌乱回房去拿伞,雨水砸得地“哐啷哐啷”响。
却原来不是雨水的声音,是盔甲,是兵士们踏地的脚步声,王幼清楞楞抬头,她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拿剑的人冲进家里,把她和娘亲包围住。
一个老爷爷双手捧着明黄的圣旨,从中间走过来,王幼清认识他的装扮,爹爹说过这是宫里的公公,以后见到都要礼貌行礼。
王幼清对着这个老爷爷甜甜一笑:“大公公好!”
可这个老爷爷不理她,只扯着嗓子高喊了一声:“动手!”
然后,那些魁梧的兵士们开始挥动双剑,所有人哭喊、撕扯着尖叫,在院中狂奔。雷鸣电闪,泼天的大雨冲着满院的猩红的鲜血,汇成红河,一个一个抖索着脖颈的人,血流如注,如同宰杀的活鱼,他们瞪大了双眼,瞪得黑瞳突起,死不瞑目。
“幼清,别怕,别怕……”
娘亲把她护在身下,在她耳边不停颤声重复着“别怕”,然后娘亲被人拉走了,她看着娘亲散乱着长发被提起头颅,那把沾满血的剑割断了娘亲细长的颈,暗红的血从脖子里四处喷射,刺进她的眼睛,满目赤红。
“娘!”
然后,黑暗,无尽的黑暗……
天乾三年,端康皇后在宫中施行朔朝巫蛊禁术,诅咒皇室,被褫夺封号赐死,同日,太子谋反,举兵攻打皇宫,兵败承天门,皇帝震怒,下旨诛连皇后母族王氏九族,上京王氏上下整八百人,悉数斩杀,无一幸免。
朔朝繁盛百年的王家,就在一场大雨中轰然倒塌,唯有遗留的千丝万缕的关系,让人们还能隐约想起那个曾经耀眼的世族。
-
八月,纭州的桂花开了,秋风乍起,是满江细碎月色,花香醉人。
江南一片的人都知道,纭州有三绝:桂花、酒酿、晏娘。
晏娘是锦雀楼的花魁,江南第一名妓,弹得一手好琵琶,生得一副倾城容貌。
今天是八月十五,每年今天,锦雀楼的画舫有一场盛会,以酒斗词,最特别的是,晏娘会择一首词,为其谱曲,江南一带,人人皆饮晏娘曲,民间好词之风盛行,若能一词成名,是极得意的事。
“姐姐,姐姐,我瞅着纭江上今年的船又比往年多了些呢。”
小舒推开窗户,用叉干支好,江上轻风入户,飘起妆台前的脂粉,为镜前女子上了妆。这女子梳着灵蛇髻,髻上步摇轻晃,柔荑拾黛为眉细细添上一笔,眉角上扬,朱唇明艳,正是那传闻里的女子,晏娘。
“小舒,去帮我擦擦琴吧。”
“好!”小舒转身进了侧间。
晏娘拿起妆台上的香油盒,中指划出薄薄一层,在脖颈两侧轻点,顿时便漫出桂花的香气。
这时船舫外乐声缓缓起了,江上船只荡漾,人群熙攘之声顺着秋风到了晏娘的耳边,是啊,今夜人又多了。来锦雀楼五年,每年慕名而来的人越来越多,她也好像越来越习惯了自己如今的身份。
“姐姐,琴擦好了,可要试一下音?”小舒抱着琵琶走出来。
晏娘接过小舒手中的琵琶,熟练地拧桩试音,这时厢房外有人敲门,是锦雀楼的鸨妈妈:“晏娘,好了没?时辰要到了。”
“妈妈,点灯吧。”晏娘声音娇俏软酥,微辣又甜。
晏娘的声音一出,鸨妈妈立马叫小厮去传话,锦雀楼舫上三千盏灯一齐点亮,此时灯火多如繁星,一盏接着一盏,光亮不曾有隔断。
斗词大会以晏娘的琵琶曲开场。
她抱着琵琶,登上了船舫最高处的台阁,此处,能让纭江上所有地方的人,都看见她。
她一出来,众人都吵嚷起来。
“晏娘子来了!”
众人朝台阁看去,那女子一身红衣,裙上金线勾出妖治的牡丹,酥胸软腰,尽是风情。
这就是江南第一名妓!哪怕早已听过她的艳名,众人还是被此时的美色震惊了。
有人喊道:“晏娘子,今夜可要擦亮眼睛,选个最好的词,说不定还能选个好郎君。”
闻言满堂大笑,晏娘也“咯咯”地笑起来,声音娇脆如同黄莺:“好啊,那诸位郎君今日一定要好好表现,说不定本姑娘就瞧上个俊公子,直接跟着就走啦!”
这一下厅里炸开了锅:“哎哟,晏娘子可发话了,大家努力啊!”
如此绝色美人儿,到底谁能获取她的青睐呢?一船的人,激动又期待。
乐声起了,清脆如小溪叮当,徐徐展开一场美妙的视听盛宴,晏娘道:“一曲春江花月夜,为诸位洗尘。”
此时,锦雀楼旁边的谢家船舫,有一人刚刚从小舟登上了船舫,这人雄鹰般的矫健身姿,气势冷冽似古剑锋利,浓眉挺鼻,尤其一双眼睛,如一汪幽潭直让人深陷。他不说话旁人也能感觉到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沉沉威势。
“李公子,请随小的来。”
小厮在前带路,引这人往船舫里走,上了几层短梯,到了一阁房间,推开门,一个白衣风流者笑声迎面而来。
“博衍来啦,有失远迎啊!”
李博衍觑了谢桢一眼,自顾走到桌边坐下来,这里正好朝着锦雀楼那边,他从窗口望了一下,只看见一个女子怀抱琵琶,风姿绰约,也没细瞧面容。
青楼女子,他不感兴趣。
“我说怎么去府里找不到你,跑这来风流了,身为谢家唯一的嫡孙,你还真敢撒手跑路,你爷爷快被你气死了。”
李博衍虽说和谢桢是从小玩到大的兄弟,但他和谢桢这爱享乐的性子不同。
他们李家男儿,从出生起就定下了必是征战沙场的命,他爹和大哥都是在战场上摸爬滚打多年拼出来的功名,他也是十五岁便开始领军打仗。
谢桢撇撇嘴,只当没听见,转移话题:“不过,你的伤怎么样了,上次那仗虽然赢了,你可是九死一生。”
“谢谢关心,死不了。”
谢桢喝着酒,突然一脸兴致看李博衍:“我是躲我爷爷来江南,你来江南干嘛?”
“自是有事来的。”李博衍不多言。
“是来找她吧?”想起那个明媚的姑娘,谢桢也黯淡了脸色,“五年了,你还没放弃吗?”
提起她,李博衍心下的苦涩涌上来,叹息道:“没找到怎么能放弃。”
“你想没想过,有可能她已经……”已经死了,后面那句话,谢桢不敢说出口。
李博衍当然明白什么意思,但他不信,那么聪慧一个姑娘,怎么可能轻易丢了性命,再说,她只是失踪。
他把酒杯朝桌上一搁,“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不然这辈子我就一直找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