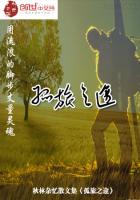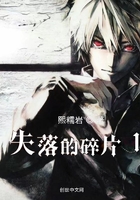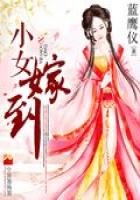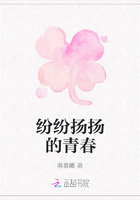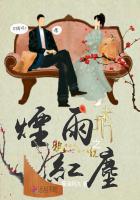三爷带着志明从吴彪家里出来,太阳已经爬了老高,没有一片云彩敢挡住太阳的光芒。镇上唯一的长街两边的店铺都开始了一天的营生,各色行人各种味道充斥着不宽的街道。有赶着羊群叼着旱烟的老羊倌,也有骑着摩托车上下班的青年,还有穿着各色校服打打闹闹的学生,志明看着这一切,仿佛又从那天的前朝景色切换到了二十世纪年末。
一直沿着长街向东走,走到村子的最里边,有一扇大门的样式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褐色的木门被岁月和雨水冲刷的斑驳难看,上面贴的门神估计也好几年没换了,破破烂烂的纸张已经和那扇同样破烂的木门融为一体,勉强能看出来秦琼的大概模样。三爷缓缓俯下身子,摸出来一张那天换的二十元,放地上使劲蹭了几下,再踩上两脚。然后就从门底下塞了进去。志明看见也不明白三爷这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就调侃了句
“三爷,您老这是嫌钱多啊?”
三爷直起身子,跺了跺脚
“就你屁话多,你过会儿就知道了”
志明见三爷没解释什么,自知没趣。
“那三爷我们现在去哪儿?”
“学校。”
学校,是一个志明比家还熟悉的地方,但是他不知道三爷一个道士去学校干什么,也没好意思问三爷去学校干什么,因为志明知道就算问了三爷也不一定会回答,就只能默默的跟上。
小镇的街道并没有城市里干净,毕竟没有清洁工定期清扫,路上的垃圾和动物粪便随处可见,这些粪便和不远处的垃圾堆散发着最原始最狂野的味道。让一般人唯恐避之不及,志明没想到三爷却无视这一切,直勾勾的朝垃圾堆走了过去,顺手从脚下拾起了一个饮料瓶,抖干净里面剩下的一点水,又一次摸出二十块钱塞了进去。塞完后又把瓶子盖好,丢回了垃圾堆。目睹了全过程的志明开始觉得,现在要么三爷是傻子,要么他是瞎子。
想了一路的志明还没明白三爷这么做是什么用意,就和三爷到了一个小学门口,学校的样式和志明上过的小学差不多,都有着粉红色的墙壁,暖色的屋顶,五层楼左右,中间一定会是个小花园,操场也一定在后面。因为全国学校都差不多是同一个样式的。
警务室的门口迎出来一个高大的老头,大概有七十多岁,但看起来身体极其硬朗,比志明还高出半个头,背挺的笔直的,走起路来虎虎生风,就连朝三爷拱手作揖时,志明都感觉这老头袖口带风。
“妙清师傅,今天来的够早啊,还带着一个俊小伙儿。”
老头张嘴就算一句就是字正腔圆带着儿化音的京片子,让志明觉得这绝对不是一般的门卫大爷。
“不早了,王老师,老道路上还耽误了不少时间呢,不然我两个小时前就到了”
“走吧您嘞,咱有话屋里说,我炉子上可炖了个好东西。”
三爷刚走了两步,听见这话就笑起来
“你是给贫道抓了东海的王八,还是给贫道捞了西王母的鳖啊?”
志明跟着三爷刚刚到警务室门口,就闻见了一股浓郁的鸡汤鲜味,顺着志明的嗓子眼一直往下滑,直溜溜的掉到了胃里,把那馋虫给钓了上来,志明顿时觉得口舌生津,情不自禁的咽了一下口水。走在王老师自然是听见了这咕噜一声,有些得意的掀开了炉子上的砂锅盖。
“瞧好了您,这可是个好东西,我专门从老顾那重金请过来的,您又不是不知道老顾那人有多扣,秒清你今天是赶着趟儿了。”
只见一只肥硕的乌鸡把黑紫色的砂锅挤得满满当当,乌鸡旁边漂着几粒煮的发涨的红枸杞,志明还看见了几段当归,党参,黄芪,最底下好像还有一棵西洋参。三爷也凑到炉前,等鸡汤的雾气散去,瞅了一眼砂锅,恍惚间有些愣神,似乎回想起来自己年轻时做国宴的风光。
“王老师啊,你这生活越来越养生了啊”
“人啊,不得不服老,再说食不厌精嘛,今天这炖可是大补,正好咱贴贴秋膘,我估摸着鸡还得炖那么一个小时,咱先干正事儿。”
志明没想到三爷要去学校还真的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去学校学习。王老师从柜子下摸出来一个写满字的小本子,又递给三爷一支笔,就开始给三爷听写起生字。三爷也是一本正经的趴在小桌子上,拿着半截铅笔一笔一划的写,这两个年龄加起来有一百五十岁的老人,居然干着正在不远处教学楼里低年级学生正在教室里干的事情。
这教三爷写字的门卫老头就是王老师,名鸿志,这名字出自司马迁《史记》陈涉的那句“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可见家人对其希望之大。王老师刚刚出生时的王家是当地最有钱的乡绅,家里出了好几代秀才,是出了名的书香门第,也是出了名的老顽固,明末的时候号召反清复明,清末的时候又希望反民复清,永远不思变故,看不清时局的发展,安于现状,结果王家一代不如一代,眼看就要没落了。但好在王老师没辜负他名字里“鸿志”那两个字,打小就聪敏伶俐,有着远大的志向。就是思想有些叛逆,天天爱跟自己私塾老师叫板,跟传统教条为敌,气走了三个先生,惹得他爹天天拿藤条抽。十六岁的王老师在又气走了一个先生后,还没等他爹要拿出藤条,就对着老父亲喊了句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之后的二十多年里就再也没在那个家出现过。后来听说他在另一个有着先进思想的亲戚帮助下,去了浪漫的法国。王老师在法国一呆就是二十多年,在他最美好的年华里,没有在什么名牌大学进修,也没有拿到什么重量级的学位,更也没有赚到什么钱,但是他把法国人的浪漫和柔情学了个淋漓尽致。王老师在法国刚刚呆了三年,法语都说不流利,就成了一名交际大师,他在各种肤色,各种国籍的女人之间完美周旋,处理各色感情游刃有余,他和多少女人进行过法式湿吻就连他自己都记不清楚。终于有一天,王老师厌倦了醉倒在各中花色的裙摆下,决定回国看看,回到二十年没联系过的家人身边,看看当年那些老顽固们过得怎么样了。
王老师的时运好的让人不可思议,在法国的那二十是国内最动荡的日子,而回国的那年又刚刚赶上文革结束,百废待兴。在法国逍遥二十年的王老师并不知道到国家的教育事业在文革时期遭到多么严重的打击,更不知有多少知识分子死在了乡下的牛棚和批斗台上,剩下的极少数人精神和身体也多多少少受到了影响,从海外归来的知识分子更是少之又少的香饽饽。
王老师的归来,被认为是留学二十年的爱国青年学成归来支持中国教育的典范,一度成了人们争相学习的好榜样,他那张穿着西装的黑白照时不时出现在当时各种主流报纸上。国内各省的名牌大学抢着请他去当教授,有的甚至请求挂名当荣誉校长,王老师一时间成了人见人爱的香饽饽。经过深思熟虑的王老师最后去了离家乡最近的一所大学,只是想和家人弥补一下失去了二十多年的亲情。谁都没想到当日的家乡报纸主题就是王老师,标题是《感人至深!王鸿志教授放弃高薪岗位,一心振兴家乡教育》。当年拿藤条抽王老师的那位老父亲,在这时带上老花镜,仔细端详着那张用一整版报道王老师的报纸,真真正正的觉得他儿子成为了一只远飞的鸿鹄。
虽然王老师在法国没有取得重量级学位,但好歹是喝了二十年洋墨水的人。他把西式教学带到课堂,进行了教育革命,用他那独特的法式魅力和感染力,让自己的课堂节节爆满,专讲数的他在课上穿插中外历史文化,心理学,甚至还有爱情。这无疑在当时闭塞沉闷的课堂上如闪耀的太阳般吸引人。加上王老师打扮时髦,长相俊朗,有些文史学科的女生甚至为上一节他的课而熬夜钻研数学,就这样,王老师从一个神奇的角度提高了全校的数学成绩。
这时的王老师成了全校女老师和同学的梦中情人。刚开始王老师还保持着老祖宗留下来的矜持和为人师表的基本道德。但有一句话说的好啊,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很快王老师就又恢复了在法国时的风流,他像一条金枪鱼般不断的游绕在女学生和老师之间,和身边不同的女伴在各个时段出现在校园的各个角落。但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终于有一天,纸不但没包住火,反而燃起了森林大火。那些深爱过他的女学生和老师将他团团包围,有人愤怒,有人难过,有人渴望他给一个解释,有人希望他只爱自己一人,甚至还有人原谅。这条陷在网里的金枪鱼看着这些他曾经深爱过的女人们,思考起来,他到底爱谁。
最终的结果是王老师离开了,学校受到的压力实在太大,选择了明哲保身,将他辞退。虽然王老师在自己的感情处理上面是煤渣,但在教育上面确实是一块好钢。国家真正的做到了好钢要用到刀刃上,把他下放到最需要文化教育的大西北,去一个全校任何女老师的小学做基础教育,但谁能想到,王老师居然在这里遇到了真爱。
这所乡村小学的基础设施极为简陋,是民间筹款自建的,全校老师和教工加起来只有六个人,六个平均四十岁的男人,这六个人其中两个的文化水平只是初中毕业,但他们却担任着一百多个学生的各科老师。
王老师的一切与这破旧的学校格格不入,无论是他那油亮时髦的发型,还是笔挺的衬衫西装和擦得油亮的小牛皮皮鞋,都与这挂满黄土的一切形成了剧烈的反差。全校唯一的女性是这座小学的校长,她也是旁边村里考出来的唯一大学生,大学毕业后一线教育奋斗了多年,回家乡设立了这里的第一所小学。二十六岁的她在当地已经算大龄的再不能大龄的剩女,受过多年高等教育的先先进观念和当地男人格格不入。就连帅气高大的王老师也不是她一眼相中的白马王子,那些风流韵事她早已有所耳闻,所以看王老师格外的不顺眼,处处给小鞋。但王老师说真的有点贱,女校长越给他穿小鞋,他反而越对她感兴趣,天天把皮鞋和头发收拾的油光锃亮去有意无意的找事,谁知道女校长根本不吃他那一套。坚持了一年,王老师终于剪掉了他那时髦的发型,天天除了沾灰没其他用的小牛皮鞋也换成了老布鞋。在这穷乡僻壤,中分还真没几个人能剪出来,专门擦皮鞋的鞋油也不好买。当王老师小平头老布鞋出现在女校长眼前的时候,女校长反而觉得他顺眼了许多。
日子过得真快,死皮赖脸了两年多的王老师终于追到了女校长,两个人终于走到了一起。王老师虽然过了风流的年纪,但浪漫却是渗到骨子里的。他把那些浪漫花在女校长一个人身上,有时只是田埂上的几朵野花,或门前的一个拥吻,有时是亲自下厨一桌家常菜,或是托人在省城买当时最流行的碎花裙子,两个人把困苦的生活过成了情诗,年过中年的两人活成了当时人见人妒的神仙眷侣。
这世上天妒英才的例子太多了,神妒情眷的例子也不是说没有。王老师和女校长的爱情可能真的让神仙也嫉妒吧,女校长一心一意的扑在学校的发展上,一直加班到深夜。那时一个下着骤雨的夜晚,她被超载的卡车撞死在前去送伞的王老师眼前。
女校长的棺材下葬的时候,王老师就把自己的魂跟着埋进去了。他天天抱着女校长的遗像喃喃自语,整日不知时也不知食,蓬头垢面的过了一周。邻居们看不下去了,请那时头发还没白的三爷去看看,三爷什么也没带就下山去了,这事他有经验。邻居们没见三爷驱鬼,也没见三爷给王老师招魂,只见三爷拉了个小板凳,陪王老师聊了一天一夜。至于说了什么,邻居们谁都不知道。你要是问起他们俩任何一个,都会说忘了,至于是真的忘了还是怎么的,那也只有他们两个知道了。
三爷走的第二天,王老师就又熨平白衬衫,打上领带回学校去了。他接手了女校长的工作,如同当年的女校长一样一心一意扑在了学校的发展上,王老师放下身段四处给学校拉赞助,找老师,筹款建新的教学楼,还把女校长的赔偿金全拿出来,给学校建了一个爱心食堂。多年以后,整个小学成了省里数一数二的学校,一拨有一拨的学生送出去了,没想到又一拨又一拨的学生回来了,他们都成了这个小学最年轻最好的老师,没有人可以忘掉女校长,也没有忘掉王老师。
食堂竣工的第二天大早,王老师就撂下一帮等着剪彩的校领导,一个人跑上山找三爷,说他又梦到女校长了,她笑的很高兴,还说让他多保重身体。自打那以后,王老师戒了多年的烟酒,天天抱着个养生书看,保温杯里永远泡着枸杞和红枣,那栆还是三爷道观里的。
王老师想了很久不知该如何报答三爷,一次偶然得知三爷大字不识几个的时候,他体内的那股教育之魂又燃了起来,非要教三爷写字,三爷怎么都推辞不过,也就随了他。但三爷毕竟老了,学了忘,忘了学,过了十多年,还没从小学毕业。当两个人头发都花白的时候,王老师退休了,但他舍不得两口子拼了命建出来的学校,就执意留在门卫处当起了保安,说要用剩下的命继续守着这个学校,守着女校长的心血。
你看他们俩真的是,就算阴阳两隔,还要继续给世人秀一段恩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