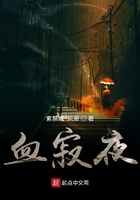眼镜本想走过去介绍梁老师跟钟伯认识一下,钟伯却急匆匆地走了,留下一脸错愕的梁老师。
梁老师问眼镜:“刚才那位是谁呀?”
“钟伯,开二手家具店的,算我和肖生的朋友吧。胖子也认识。”
“哦,没听胖子提起过。刚才一进门,看他的神情吓我一跳,还以为走错病房,冒犯到人家了。”
“哦?钟伯人还蛮随和的。”
“是吗?看起来不是很好相处的人。”
“不会不会,他就是面相严肃了一些。”我解释道。
梁老师笑了笑:“那就好,怕你俩遇到难对付的人。你俩还没吃饭吧?我炒了几个清淡的菜带过来给你俩换换口味,医院的饭怪难吃的。”
今天真是有口福了,又有十全大补汤喝,还有私房菜吃。前几天一直吃医院那啥味也没有的饭菜也真是快吃吐了。
“来吧,尝尝我做的饭好不好吃?”
我和眼镜乐得嘴都合不拢,这家里炒的菜就是香,吃下去感觉伤好了一大半。
不知道刚才钟伯到底是什么表情,似乎给梁老师留下了很不好印象。她不停地跟我们确认:“那个钟伯真的是你们的朋友哦?”
“哈哈,真是朋友,刚才钟伯到底怎么了?”眼镜笑着问。
“也没什么……说不上来……就是有点吓人。”梁老师想了想,也说不出到底是个什么奇怪的感觉,便说自己可能是被歹徒捅伤我的事情吓到了,有点心理阴影。她跟我们闲聊了一会儿,见没什么事就回去了。
梁老师前脚刚走,眼镜就可激动地跑过来跟我说:“刚才!钟伯撞见梁老师的时候,脸都红到脖子根了。”
比起钟伯脸红,眼镜八卦的样子,更让我吃惊:“我猜钟伯还是单身汉,他又那么宅,见到女人,尤其是漂亮女人脸红也正常嘛。”
“太红了,比我见到女人脸都红。”眼镜骄傲地说。
我白了他一眼,没理他。
“我觉得以钟伯的性格娶媳妇不难。”眼镜估计是太无聊了,忍不住还要八卦,“肯定年轻时有过浪漫的一段,后来没成就一直单着了。”
“你是在说自己吧?”
眼镜白了我一眼:“我和小毓一定会结婚的。”
哎,有的时候,我是真羡慕眼镜这种傻富二代的单纯,二十大几的人了说出来的话像高中生一样。但同样的话,我好像也跟小岩说过吧:我们一定会结婚的。还是四川话骂的好:“你结个脑壳昏(婚)哦”。
眼镜见我一脸不屑,不服气地说:“以后逮着机会,我就要问问。说不定钟伯初恋就长梁老师这样。”
我看他和小毓是真复合了,最近智商又严重不在线上。吃完饭,眼镜没在沙发上坐多久就开始磨皮擦痒的了。一会儿去厕所折腾一下发型,一会儿对着窗户整理仪表,两分钟不到就要看一下手机,来来回回地在病房里走来走去。
走到最后,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你今天晚上是要去干嘛?”
“嘿嘿”眼镜笑得牙花子都要龇出来了,“生哥,今晚我回去住。”
“滚吧。”
“别这样嘛。我一会儿去跟护士台打个招呼,让他们看着点。你别怕……”
“怕个屁,滚吧。”话虽这么说,但我心里还是有点怵,万一要是再遇到点啥。但眼镜也确实不应该天天在这守着我,也不是什么致命伤。
眼镜只会冲我傻笑,“那我回去了啊。”说完就一溜烟跑了,这怕是憋坏了啊。
唉,这时候要是小岩在就好了。
我手机游戏也打腻味了,苦苦盘算着怎么度过漫漫长夜。想着前天晚上的事情就不寒而栗,赶紧把手机设置了报警快拨键。但神奇的是,明明才九点过,我的睡意却浓烈袭来,不知是不是钟伯那十全大补汤喝的,整个人轻飘飘地,已经好久没有这么想睡过了。
头顶的白炽灯渐渐模糊,风吹进来了,白炽灯直摇晃。
“好球。”突如其来地喝彩声,吓了我一跳。我从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正躺在台球室的皮沙发上。
一间不大不小的屋子里,摆着3张台球桌。最靠墙的一桌,有几个赤膊的年轻人正在打球,旁边还站着2个穿超短裙的黄头发女人。豹纹的短裙,紧紧地包裹着她们丰满的身材,纤长的腿像圆规一样站着,上身穿着黑色紧身T恤,漂亮的小蛮腰没有一丝赘肉。
我看得着了迷,忽然一个双色球飞了过来,重重地砸在我的手臂上,痛得我直咧嘴。我激动地坐起来,准备跟砸我的人大干一场。
空空如也的台球室里,什么人也没有。台球桌上落满了灰尘,一只大蜘蛛正在沙发背后的货架上结网。
我赶紧站起身来,却发现自己连鞋都没有穿。地上是厚厚一层灰,不,是一层泥,黑乎乎的。我的脚却像踩在小石子上一样,膈应得难受。很快,那层泥土动起来了,我俯下身仔细一瞧,那根本不是土,而是密密麻麻的虫。那些虫正从墙角源源不断地爬出,像一股黑色水流。
我在桌球室最里面的角落里,四周一扇窗户也没有,大门敞开着却亮的发光,根本看不见外面是什么,但能听到车水马龙的声音。
我赶紧冲了出去,一条笔直的马路沿着地势起起伏伏,路上什么车也没有,路旁全是铲平了的空地,除了那个孤零零的台球室,一眼望过去看不到其他任何建筑物,像是一个拆迁出来的沙漠。
“滴滴滴……”马路的那头有人在按喇叭,可我根本看不见车在哪里。
“滴滴滴……”车主似乎看见了东张西望的我,喇叭声更急切了,“滴滴滴……”
我跑了起来,身轻如燕,从来没跑得这么快过。那喇叭声还在响,但我还是看不见车在哪里。而且我跑得越快,那喇叭声离我越远。但只要我一慢下来,那喇叭声就会响得更急切。我能感觉到,在路的那一头,有人在焦急地等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