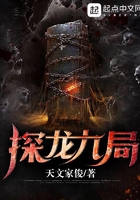我们到现场的时候,警戒线外被围得人山人海。因为是周末,大家都不用上班,人格外多。
出事的的确不是我和眼镜昨晚上去的那栋楼,而是旁边的一栋。离我们上去的那栋楼,5米远不到。
我们几个完全挤不进人堆里,只是站在外围远远地观看,除了几个警察在那晃晃悠悠,也看不出什么名堂。
我和胖子都觉得,我们应该找个能看得见那栋楼屋顶的地方。眼镜不吱声,隔了一会儿神秘地说:
“你们跟我来,我知道什么地方可以看得到。”
眼镜领着我们走进了一条东向的巷子,越走越远,我和胖子都很纳闷:
“你确定这能看到吗?”
“肯定能,你们放心吧。”
又走了一会,在一条极小的巷子口,眼镜灵活地钻了进去。在巷子的尽头,几栋8层高的空楼,大门口贴着封条,看样子是刚封不久的。门口的牌匾已经被人拆走了,很难看出以前是做什么用的。说是学校吧,又小了点,连个操场都没有;说是工厂吧,空间也不够宽敞;倒是像机关单位,但什么机关单位会在这个小巷子里呢。
“眼镜,这以前是什么地方呀?”
“不知道。”
“那你怎么知道这里?”
眼镜支支吾吾:“朋友带我来过…………”
哇哦,斯文的眼镜真是够野啊,约好居然来这种地方,重口味。
胖子也挺诧异地看着眼镜,一副万万没想到的表情。
只见眼镜轻车熟路的踩着铁门上的铁条就翻进去了,我已经好多年没做过这么高难度的动作了,硬是像个淑女一样,蹩手蹩脚地爬了半天才翻过去。
胖子就更别说了,我感觉这一翻,他三高都快出来了。
眼镜领着我们走到了正中间那栋楼的后面,只见有一扇窗户已经被人敲碎了,房间里丢满了各种垃圾,看来这里是年轻人聚会的圣地啊。墙上还有很多看不懂的涂鸦,五颜六色的。
果然一翻进去,往里走,每上一层楼,就能看到不少丢在地上的安全套。眼镜的表情颇为微妙。
这里的楼梯也非常奇怪,扶手的上面都架起了高高的铁围栏,阳台上也全是严严实实地铁围栏,看起来怪怪的。每层楼的每一间房都是严严实实的铁门,在墙的高处开了一个小小的窗。
我怎么看都觉得这里像是监狱一样,可监狱怎么会被查封呢。反正这栋楼让人觉得很不自在。
这栋楼看起来不高,但足足有9层,我的亲娘,爬起来也是要人命的。好不容易爬了上去,我和胖子都气喘吁吁,眼镜却气定神闲:
“你们看。”
这回眼镜是真挑对地方了,站在这个楼顶能清楚得看到那个被封锁的屋顶,有几个警察在来回走动我们都看得清。奇了,明明走了那么远,却隔得这么近。
眼镜得意地说,“这条巷子是斜的,走出去就绕到那条街的街尾了。而且这个楼很奇怪,看起来矮,但其实很高,可能是地势的原因。”
反正我对地理空间这种是不太闹得明白的,但站在这里看那边确实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
警察们正在屋顶上取证,我还能看到旁边那栋楼上的白色塑料桶。就这相邻的两栋放着两个白色塑料桶,大小也是差不多的。警察也发现了,都围着那两个桶转。不知道我看见的那个桶里放的是什么。多半是流浪汉丢我的猪血、内脏。
其实还是隔得有一定距离,我们还是看不清细节,只能图个心里安慰。胖子特别激动,在这楼顶来回踱步,不断地找最佳视角,忙活了半天最后叹了口气:“除了警察和桶,什么也看不见。”
“找陈警官问问吧,都又一起案子了,肯定是连环作案了,你是受害人家属也有权利知道案子进展情况。”
胖子挠了挠头:“可能是我找陈警官太频繁了,他现在都有点躲着我。”
眼镜示意我们蹲下,不如太明显了,万一被警察看见就麻烦了。我们齐刷刷靠墙根蹲着,我个字高,一下重心不稳,向左边倒了一下,下意识地手撑了一下,却按在了一个贼锋利的东西上,痛得我差点叫出声音来。
我扭头一看,是一个碎陶片。那土黄土黄的颜色,似曾相识,在哪里见过呢?可这脑子吧,真是越到用时越不好使,死活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
就在这时,楼下突然一个东西掉在了地上,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我们三个吓了一跳,贴着墙一动也不敢动。
然后又是某扇门被打的彭彭直响,我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生怕遇到什么犯罪分子。
我看眼镜和胖子脸色已经惨白了。
我们等了好一会儿,楼下又完全没有任何动静了。我跑到正对大门的那一侧一看,只见巷子里一个戴黑色鸭舌帽,穿黑色运动衫的人,正迅速地走出巷子。他的手上提着一个编织袋。
眼镜胆子可真够大,这种地方也敢来。确认没有人了以后,我们仨灰溜溜地迅速逃离了那栋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