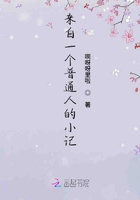第二天上班,我本以为张老板要放大招,但一天都没见着他人,一问胖子才知道,大领导临时把他抓去出差了。
不过胖子还很担心我,让我早点做跳槽的打算,他怕张老板在大领导面前吹耳边风,一告状大老板不高兴说不定会辞退我。毕竟在策划案中,泄露商业机密非同小可。
我倒是有点死猪不怕开水烫了,要是张老板真敢把我炒鱿鱼,我就写封举报信把他跟实习生事抖出来。
实习生一夜之间又回到了刚见她时的样子,见到我就翻白眼,好像她只会这么夸张地表达自己的嫌恶一样。这都什么年头,连实习生都学会了狗仗人势。不过,对胖子她还是依然一副无公害萌妹子样。无知到可笑,这些人都是混了十几年的老狐狸,你那点套路,也就坑坑我。
眼镜今天又没来上班,我都闹不明白他究竟是在热恋,还是失恋了,一会儿一个样。下午他发消息来提醒我,让我下班跟他一起去找钟伯。
总感觉钟伯最近很是神秘,也不怎么主动联系我们了,以前还每天跟我和眼镜分享点每日新闻,现在有时候发消息给他他都不回了,估计是有大生意要忙。正好,去档口看看他在忙啥。顺便也挑些家具,布置一下新屋。这回得好好捯饬捯饬,住得像个人样。弄好了,把我妈叫过来住两天,她也就知道我在广州没瞎混日子了。
下午事情多到忙不过来,下班已经快8点了。我在食堂草草扒了几口饭,就往钟伯那儿赶去。眼镜已经在那儿跟钟伯喝起功夫茶了。唉,这不上班的过的才叫日子,整体想干吗干吗。我一个月拿那么点工资,人却完全卖给公司了。胖子这种就是抵押给公司了,玩命工作,我估计这个星期,他就没9点前下过班。
才拐进小巷子口,就听见了钟伯爽朗的笑声。档口昏黄的灯光照亮了门前的空地,钟伯和眼镜一人一把躺椅,手摇着蒲扇,不要太惬意。钟伯最先看到我来,从躺椅上站起来,高兴地喊道:“来啦,吃饭没有啊?”
“吃过了,钟伯,好久不见。”我走过去,毫不客气地躺在了眼镜旁边。
“什么好久不见,前几天才见呢。你们倒是好久没来这里了。”
“那不是事情多,没逮到机会嘛。”
“嘉恒说你要搬家啊,要不要在我这里挑些家具啊?”
“钟伯,你这也太会坐生意了,我屁股还没躺热呢,你就给我推销上了。”
“合适的免费送啊,嘿,不过太贵的不行啊,便宜的免费送。”
我一听还能免费送,立马从躺椅上坐起来:“哪些免费送啊?”
“你先挑,挑好了再看。”钟伯精明地笑笑,一副“老谋深算”的样子。
好久没来,档口放的东西都又换了一波,以前看到的一些古旧十足的实木家具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设计挺简约的现代家具。
钟伯走过来,拿起一个小茶几说:“这个你要就免费送啦,这些都是刚收回来的,现在的年轻人会生活啊,住的地方都要去那个什么家买些便宜家具回来布置一下,质量是差了点,不过样式很新潮。”
原来是二手的宜家家居,这不是捡着大便宜了嘛。设计都挺好看,在钟伯眼里又不值钱,我干脆全搬回去算了。
钟伯看出了我的“狼子野心”,笑着说:“可不能全搬走啊,钟伯穷着呢,你留点给我卖钱。”
我走到最里面的货架,看到货架下放着的魂瓶少了不少,都是些样式很普通的魂瓶了,看起来跟个地摊花瓶差不多,没什么特色。唯独中间有一个,瓶口裂了个小口。这魂瓶我看见好几次了,每次都觉得在哪里见到过,因为它的颜色是一种很特别的土黄,生活中不太常见。
我小心翼翼地把瓶子拿起来,端详了一番,这玩意看多了也不觉得恐怖了,反倒有几分亲切。我看得正起劲,听到了一声清脆地东西摔碎的声音,可往外看,眼镜正坐在躺椅上,钟伯站在档口大门口,正摆弄着新买的兰花。
我四下看了看,只见档口的里屋换了扇崭新的防盗门,眼看着厚得跟堵墙似的。我指着门问钟伯:“钟伯,屋里好像有什么东西碎了,你听见声音了吗?”
钟伯一听,神色有些慌张,却又立刻镇定了下来:“哦,没事,可能墙上挂得东西掉了。”
话音刚落,“啪”又是一声,防盗门太厚,声音闷声闷气地传了出来。钟伯慌得有些掩饰不住了,丢下喷水壶,急急忙忙往里走:“你们坐会儿啊,我进去看看。”
钟伯拿出一把钥匙打开了门,推开了个一人宽的小缝,快速地溜了进去,然后“嘭”的一声关上了门。
眼镜走过来,小声说道:“你说钟伯的值钱宝贝是不是都藏在里面啊。”
“应该是,你看那防盗门厚的,像电影里银行金库的门。”
“嗯,是那个感觉。我怎么觉得像里面有人在摔东西?”
“是吗,不会吧,那钟伯直接喊一声不就完了。”
“哈哈,你说钟伯会不会金屋藏娇?”眼镜的表情极为幽默,他一说话我俩哈哈大笑起来。笑得正起劲,门开了,钟伯像泥鳅一样钻了出来。
“不好意思啊,后面库房有个架子倒了,东西散了一地,要收拾一下先,就不陪你俩吹水了啊。”
眼镜不知趣地说:“那要不要我们帮忙收拾,我们反正也没什么事。”
钟伯客套地笑笑:“不用,不用,都是些细碎的东西,我自己慢慢整理就好。”
想必钟伯是不会让我们进到他那宝库的,这又是在委婉下“逐客令”。“那钟伯我们就先回去了,改天等你不忙了,我们再来。”我戳了眼镜一下,便往门外走去。
我本以为钟伯是心里过意不去把我们送到了门口,还看着我们走出了小巷子。等走到家门口,才反应过来,他是要确认我们是不是走了。
我实在有些好奇,他到底要秘密做什么,便站在楼下抽了支烟,然后又折回了巷子。我才注意到小巷子里今天格外黑,没什么灯光。钟伯的档口已经关门了,但卷帘门上方的孔洞里还是透出了一束束昏黄的光。
我躲在靠档口半米远的地方,竖着耳朵偷听了一会儿,什么声音也没有,四周一片静悄悄。可能就是整理货架吧,我也是电视看多了,戏有点足,想什么呢。
一转身,黑暗里背后还蹲着一人,我吓得要叫出声来,那人忙上前,一手掐住我脖子,一手捂住我嘴。
一看,是SB眼镜,我恨不得直接剁了他的手。麻蛋,被一个大男人捂住嘴的感觉也是够恶心的。
我倒是闭嘴了,档口里却传来一声怪异的叫喊,那声音既像人,又像猫,尖声尖气,刺耳得让人起鸡皮疙瘩。紧着是急促的脚步声,感觉正向门外走来了。
我和眼镜赶紧起身,以掩耳不及迅雷之势,迅速脱下鞋拎在手上,赤脚跑出了小巷子。反应之快,自己都佩服自己。
跑出来后,既有点惊悚,又觉得傻得慌,便顾左右而言他起来:“回去了啊,你几时搬到我那边?”
“就明后两天,趁周末先搬点。”
“嗯,走了。”
我俩在黑乎乎的巷子里默默穿上鞋,各回各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