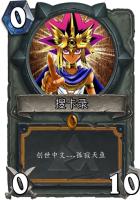嫁衣繁复间,她寸步难行,可丝线不依不饶,缠着她的手腕朝前拖,任她瞎几把踢腿摔手挣扎。
眼前一花,来到个空旷处,牵着她的丝线化作烟雾散去。她抬眼定睛,原来那层层嫁衣中掩藏着一只小小的铜铃。
铜铃精巧,上刻着花鸟虫鱼,低端一行小字:嵇清霖。
她情不自禁,伸手触碰它。
温和得如玉般,仿佛是个长者对晚辈的关怀。
可是又有点难以言说的伤感,几乎要落泪。
蜡烛已熄灭,只余下阴风阵阵,吹得珠帘响。
时澜睁眼时,嵇时匡昏昏欲睡,哈喇子流的老长。剑忘了收,几乎要戳到腿上。
她拿出扇子狠狠抽嵇时匡:“你妈的为什么,说好了护法的呢,说好了做彼此的天使呢,你这也太不靠谱了吧。“
嵇时匡被打醒,疼得嗷嗷叫,满屋子跑:“师妹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快把你那扇子收回去,误伤就不好了……“
时澜举起扇子:“我今天就是要打死你。“
被嵇时匡躲开,时澜自知修为比不上,便习惯性拿着扇子扇了扇风,扇得自己冷得一哆嗦。
嵇时匡看着她,满脸震惊:“师妹,你……“
时澜心里奇怪,下意识摸摸脸,果不其然,摸到一手血。
她淡定掏出手帕擦擦鼻血,看见嵇时匡一脸痛色便知道他想歪了什么,忍不住狠狠踢他一脚:“什么眼神,我这次真的没看见什么少儿不宜的东西。我傀儡身,自然比不上往日岁暮山嵇时澜。”
嵇时匡脸色更沉痛了:“师妹你的傀儡依旧那么叛逆,明明就是同一个人。”
时澜深呼吸,闭眼,懒得理他。
她坐下打坐调息,道:“我找到了清霖师姐的铃铛,在那日破庙相会的新娘身上。但那铃铛用蜡封住,发不出声响。”
闻言,嵇时匡正色道:“那可否得到师姐下落?”
说不清。
时澜怅然:“师姐大概还未遭人毒手。”
但是否生不如死,就不一定了。
两人一起沉默。
直到前院鞭炮响,烟火绽放,璀璨的色彩抹在浓重的黑里,像纸上溅射的墨滴。窗外大亮,时澜才意识到竟已入夜了。
此夜必将不会太平,好戏即将上场。
只是有那个黑衣青年作梗,她不好搞事情啊。
嘤嘤嘤麻麻好可怕,我还叫过那个人老黑,老黑这么简单粗暴的名字怎么能适合有一个娘里娘气的鬼帝鹤容。
会死无葬身之地的。
正逢新娘新郎拜堂之时。
这日来了许多修士,低则练气筑基,高有金丹元婴。大能者上座,其余皆远远在酒席上观望。
时澜一个垃圾修士,连入门筑基都尚未到达,只能被人潮挡在外,万分哀怨地看嵇时匡朝里挤。
其余修士皆站高了朝里看,兴奋嚷嚷:“你瞧那是不是许家的人。”
“可不是,没想到林家娶亲连许家都能请动。”
“那边大概就是近日赫赫有名的白境了。”
惹,白境?
时澜连忙站起,掂脚朝里看。
人潮拥挤,熙熙攘攘都是人。目光所及处,乌泱泱都是晃动的人头,唯能看见大堂处一片红,甚是喜庆。
她挠挠脸,觉得有些难办,
她记得白家与谢家相邻,白境与谢和言事穿开裆裤的交情。幼时她得幸见过白境一面,只是不知这么多年过去,白境是否还记得她这等无名小辈。
如果能委托师兄进去把人叫出来就好了。
她陷入沉思,忽然觉得自己似乎忘记了什么。
沃日谢黔!!
此时,林家后院。
许黔正与师弟对弈。
许家素来爱清净,许黔更是极端,曾经几年将自己关入房中不见人,多说一句都嫌吵。
师弟捏着手中的棋子,看着许黔专注的神情,小心翼翼问道:“师兄,你打算何时回门派。”
许黔皱眉,师弟心里一凉,内心小人以头抢地,嚎啕大哭。
完了,问了不该问的问题。
他咽了咽口水,硬着头皮道:“师父师娘很是想你,还有小蓉师妹都盼着你回来。”
许黔手落一棋:“知道了。”
话音刚落,却见他如风一般闪出小亭。
师弟目瞪口呆,沃日沃日这是要去干嘛。
嵇时匡正解决完人生大事,随手拔根狗尾草叼着。
夜黑风高之时,身旁突然一阵疾风刮过,一把利剑直直奔向他面门。
嵇时匡一时的错愣,片刻身稍稍一倾,躲开那把剑。持剑人也不介意,“哐”一声扔了剑。
嵇时匡:沃日这手法好熟悉。
果不其然,一支利箭破空而来,要取他姓名。
他早有预料,摸到身后的树干,趁势躲在树后,待那箭刺入树干,才闪身出去,一息之间到许黔背后。
他嚷道:“兄弟不要这么记仇好噶。”
许黔面无表情,抽出匕首朝后刺去,下手又狠又快,要取人性命。嵇时匡一时躲不及,被剑刃划伤脸。
他发出土拔鼠的尖叫:“毁容啊兄弟,快住手。”
许黔冷冷吐出几个字:“有病。”
这是嵇时匡第一次听见许黔说话,往日都是动刀子不动嘴,差点让他怀疑许家大公子是个哑巴,没料到一开口,声音还挺好听。
嵇时匡不敢轻敌,拿出剑雨许黔缠斗起来。
剑在手中,却不出鞘。
许是着激怒了许黔,他一跃而起,退出几米外。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哦豁,小伙子手挺快,单身了几年的速度。
箭已瞄准。
嵇时匡比他更快,鬼魅一般飘落在他身后,搭了搭肩。
旁边冷不丁有人发声:“师兄?”
两人齐齐僵住。
许真扫开耳畔的枝叶,抬眼看贴得过紧的二人,微微一愣。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他脸一红,低头,无法直视。
场面一度很尴尬。
嵇时匡决定打破尴尬,拿开自己的咸猪手,鼓起掌:“许兄,箭法甚好,正中树干。”
拉弓的手还未收回,许黔冷笑一声,收起弓转身走人,头也不回。如玉的脸庞波澜不惊,眸子却深似海,糅杂着说不清的情绪。
见状,许真狠狠敲了自己的脑壳。
完了,又坏了师兄的好事。
他正打算露出个假笑给嵇时匡以示安慰,那厮却压根不看他,扒开拦路的枝条便追出去:“许兄,等等我。”
可惜许黔脚劲极好,没能追得上。心中握手言欢,化干戈为玉帛的梦想破灭,他蹲下身很是伤春感秋一阵,却见前院燃起火光,一阵骚动声。
噫,差点忘记正事。
时澜正在看戏,全然不顾周边修士是多么惶恐慌乱。
有人大胆推开护院,却被领头人一刀挥过去,身首分离,血溅到时澜搁瓜子的桌上,汇成一条川流。流淌下来,滴滴答答。
时澜皱了皱眉,换了个桌子。
眼瞧着外边的进不去,里面的人出不来,她不免为自家师兄捏了把汗,只希望师兄不要因为嘴贱被杀人灭口。
骚乱之中,有人乘机挑衅生事。看她一个低修旁若无人地磕着瓜子,心中难免不快。于是一把刀劈在桌子上:“小娘子孤家寡人坐在着,好生可怜呢。”
时澜看着被刀砍得四散开的瓜子,没有说话。
“小娘子是在等里面的夫君吗,只是里面金丹修士打架,只恐怕你夫君随随便便就被一阵余波弄死,出不来咯。”
她心中纳闷,她和嵇时匡那狗子很有夫妻相吗,为何别人第一眼总以为他们是道侣。
那大汉看她沉默,笑一声,伸手欲掀开她的帷帽前的白纱。
时澜不动声色后退一步。
大汉嘎嘎笑几声,戏谑道:“给我们看看你小脸蛋。”
噫,小脸蛋儿。时澜一阵恶寒。
两道身影飞上天际过起招来,两股掌力相撞,引起惊涛骇浪,将树叶吹得四处翻飞,人仰马翻。
时澜眼里吹进了沙子,闭眼时那大汉趁乱抓住她衣袖。
她懒得和这个人纠缠,扬起手中的折扇划过去。
待睁开眼时,只见一位老者和一位中年男子在空中打斗,掀翻的一堆人蠕动着爬起来,不知谁先看见脚下的血,惊叫道:“死人了。“
时澜收起折扇,擦了擦血,放回袖中,紧紧盯着空中的两人。
那老者手持拐杖,苍白的胡须和脑门仅剩的那一撮毛被风吹得胡乱飞舞。他冷笑一声:“无知小辈,想从我手中抢走东西,简直痴心妄想。“
论嘴上功夫,那男子也不甘示弱:“你这把要死不死的老骨头,半截入土的人,何不滚回去养老。“
老者怒道:“那便看看,谁能抢到这清霖铃。“
清霖铃三字一出,四下哗然。众修士皆蠢蠢欲动,但在两个金丹修士面前不得不望而却步。
时澜有点懵逼,据她所知,清霖铃不过是个施过法的铃铛,虽然限量且绝版,许多人想要收藏,但也不至于大打出手吧。
她记得,她幼时还啃过师姐的清霖铃,上面还留着她的牙印
怎么现在人人都抢呢。
金丹修士打起架来可谓是地动山摇,修为不济者被二人的威压震得吐出一口血,当即晕过去。
场面一片混乱,哀号遍野。
时澜作为一个垃圾低修被掀翻在地,痛恨自己为什么就上了她爹的当去修法。
就那一瞬间,老者拿到清霖铃,狰狞一笑,朝下俯冲。
哇哦,居然想混迹人群中逃匿,拿到东西就跑,好不猥琐。那男子一转眼看老者不见人影,怒目圆瞪,不依不饶在掌心凝成一股威压,朝下方人群掷去。
空气一瞬间凝固,风也销声匿迹。
不知情的修士好奇抬头看。
时澜抬腿便跑,顺便捎上撞上她的小孩。“哗“地一声撑开了伞。
那威压直直坠下,眼见要砸上众人。在座的修士皆错愣。可是已经来不及。
时澜稳住身形,收伞,垂眸,不去看那尸骨遍地。
宁可错杀一百,也不肯放过一个。果然世间凉薄。
她转过身,抬眸。
那抹黑色的衣角不出意料的出现,直对着她,中间隔着浑身是血的尸骨抑或伤残哀嚎的人群。
那面色苍白的少年坐在树上,好整以暇地歪了歪头看着她。他手中抛玩着一物,抛了几下,握住,拿手撑着树干,那物什隐藏在他掌心中。
仿佛一切,都在运筹帷幄中。
时澜不知道他看见了多少,不知道他是否看到她杀人,是否看见她撑开伞抵御伤害,也不知道是否看出她是岁暮山的人。
如果看见了,她不介意杀人灭口,哪怕这个小贱人是鬼帝鹤容。
可他只扬唇笑笑,唇线拉长,像极了小孩子捣乱后顽劣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