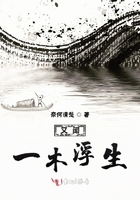大早上起来,路面上已经铺了薄薄的一层雪,偶尔看到几个野猫野狗的脚印。刚开始,雪花卷着寒气自由铺展开来,可能都算不上雪花,只是颗粒大小,后来越下越小,快五点半的时候基本上停了。还没怎么擦亮的天边给人冷飕飕的错误视觉。我妈硬是让我穿上前年和她一起买的亲子装棉服,颜色和款式很不打眼不说,看起来还很笨重。
“妈,我穿上这没法跑操,”我边解扣子,边试着挣脱我妈双手的束缚。
“今天挺冷的,穿着,啊,”我和我妈推推搡搡地下了楼梯。
林陌正从三栋楼走过来,手里攥着副有点面熟的手套,捏了捏头顶沾雪的一撮头发,“沈阿姨。”
“诶,”我妈冲林陌笑着,帮我把棉衣的扣子都扣好,“快和林陌去学校吧,不早了,”我不乐意地哼哼了两声,又被我妈唠叨,“别脱啊,小心感冒了。”
我有点尴尬地慢吞吞地挪动着,脚边的四道积雪印缓缓朝前延伸。
“要迟到了,顾浅浅,”林陌故意拉长每个字。
“噢。”
我妈一直目送我俩走出小区。
“诶呀,我妈真是,这个棉衣这么厚,还丑。”
林陌把手套立在我头上,笑着,“是有点。”
“这个手套?诶?”我戴上林陌手里攥着的手套,“你不是送过我一双粉色的。”
“对啊,买一送一。”
后来听叶梓忆说,那副手套是学友刚上新的,不打折。当时不记得被什么事耽搁了,也没怎么向林陌再提起这件事。
我和林陌走在人寥寥无几的路上,远方的天空灰蒙蒙的,像烟似雾,踏过的两排脚印相依相偎,仿佛永远通不向最后。马路两旁的行道树被白色粉饰,勉强能透出一点树干的棕色,而地上的一薄层雪正缓缓摊开原本的颜色,踩过后发出酥酥的浅唱。
2014年的第一天还是没能成功躲过跑操。我穿着棉衣站在一班的最后一排跟着队伍跑了三圈。雪后没来得及反应的气温开始同闷热靠近,教室的空气随着跑操结束后同学们的陆续进入变得拥堵。等我走到自己的座位旁已是汗流满面。
“我来。”林瀚在我的手快要碰到凳子腿时,搬下了它。
我脱下棉衣挂在凳子靠背上,从桌兜里拿出抽纸,“受不了了,好热。”
“瘦不了就胖着,你这样挺好的,”林瀚拉着我站了起来,“张义。”
随后,教室里晨读的声音越来越大,二氧化碳聚集的浓度也越来越高,前后门都大开着,但窗户都紧闭着,隔一会儿会看到一两个巡查领导的出现。
而我,依旧处于热的状态,一直找不到出口。
林陌突然把他旁边的窗户打开了。
路晓楚把校服领口立起来,把拉链拉到尽头,“你不冷吗?”
“我有点困,”林陌打了个哈欠。
路晓楚把手里的古文资料重新抖立了两下,咬出的之乎者也更尖利了。
窗外的风徐徐吹来,加速黏在我脖子上的汗的蒸发,蒙蔽了排在毛孔还未流出的汗,我顿时凉快了很多。
由于天气原因,领导们着急去吃早饭,晨读大概持续了三十分钟就结束了。默写的时候,教室里自觉地铺满翻书声和笔尖触碰纸张的声音。我在晨读时一心对付正在滚动和即将冒出的汗,默写的时候也不知道该写什么,笔不受控制地写着一个接一个的“林”字。叶梓忆躲在桌子上一摞书的后面睡觉,于果用几根前后并齐的笔芯抄写英语单词,林瀚在日记本上写歌词,林陌在,给他同桌讲题。
“你先把第一个式子的分母有理化,然后再求定义域,你看,这样……”林陌把下巴轻轻砸到摊在桌子的胳膊上,盯着手里快速转动的笔。
“可是我也这样算了,就是算不对。”
“那,我也没办法了。”
路晓楚托起自己的马尾辫甩到背后,有点不满地继续在草稿纸上算着。
“林陌,你看昨天晚上的跨年演唱会了吗?”我转过身。
林陌依然保持着原来的姿势,“看了一点。”
“怎么样,有好听的歌吗?”
“郁可唯唱的《时间煮雨》还不错。”
“明星多吗?”
“没怎么仔细看,有钟汉良,好像还有华晨宇、张杰……”
“哇,张杰哦,好可惜,我那会儿在写检查,都没看。”
林陌把头压得很低,试图藏住自己不好意思的笑。
“顾浅浅,现在是默写时间,你能不能别老扭过头来说话。”路晓楚把桌子向外挪了一小截。
“切,又没跟你说话,你不也没默写吗?”
林陌把自己的桌子也向外推了一小截,声音有点响,和路晓楚的桌子对齐。
他盯了她一眼……
还没有来得及看到林陌是怎么维护我的,林瀚把我的凳子转了小半圈,“小香菇,我这句歌词是不是写错了。”
“一会儿吃饭叫我,”林陌枕在伸出的手臂上。
“知道了,哥。”
林瀚笔记本的颜色是我比较欣赏的带有厚重感的棕黄色,每一页都写满歌词,“天涯的尽头是风沙,
红尘的故事叫牵挂,
封刀隐没在寻常人家
东篱下,
闲云野鹤古刹,
快马……好像,没错吧。”
“没错啊,那是我记错了吧。”
不知从哪节课开始,我和我的后桌,也就是路晓楚,经常时不时地起口角,不互怼两句总不舒心。每次林瀚和林陌都帮我收尾,有意无意地缓解调和。
一整天的气氛都徘徊在阴沉和潮湿之间。地面上最初的雪水还没彻底消融,隔了一段时间又覆盖了一层。校园里随处可见的瓷砖减小了不少摩擦,除了去餐厅吃饭,几乎没人往教学楼外走。
下午周练课前,叶梓忆说教室里太闷了,硬拉着我去楼下玩雪。我把整个身子都钻进校服里,站在楼道口。叶梓忆很大胆地在教学楼和办公楼的空地上滑来滑去,偶尔捧起一把雪朝我洒过来,“浅浅,快过来。”我抖落了雪,干脆坐到台阶上,“你慢点,小心摔倒。”
几分钟后,广播里有一个很甜美的声音,“上课时间快到了,请同学们进入教室,准备上课。”
叶梓忆从裤兜里拽出一个黑塑料袋,在花坛附近装了些没被破坏的雪,“走吧,上去接着玩。”
我攥了一点在手里,“叶子,看你头发上这么多雪。”
叶梓忆感觉什么东西从脖子掉进后背,凉丝丝的,“顾浅浅,你干的好事,看我怎么收拾你。”
我和叶梓忆从楼梯间打闹到教室门口。“嘘,张义。”叶梓忆瞭着后门窗户。
我从黑塑料袋里抓了一小把,“这袋雪怎么办?”
“就,先放在墙角这儿吧。”
我和叶梓忆裹着一身冷气走进教室。张义没有止住声音,只是盯了我俩几分钟,深邃的眼神让我失去了下次出去玩的欲望。
“顾胖胖,又去小卖部了?”
“不是,玩儿雪去了,”我看见张义转向黑板,把手里快凝成形的冰块搁在林瀚桌子上。
“哥,”林瀚转后身去,把它塞进林陌的领口。
“林瀚,”林陌嘴角留有一丝笑意,稍站起身,一只手托在桌角,另一只手锁住林瀚的脖子,“老弟,长能耐了啊。”
林瀚缩成一团,“没有没有,哥,我错了。”
张义正要转身,“运气好,先放过你了,”林陌边坐下,边弱弱收回胳膊。
我伴着呼出的热度搓着手,看着林陌林瀚兄弟俩相爱相杀,一直震动式笑着,早忘了楼道外那袋被保洁阿姨收走的雪。
“坏了,我的雪,”叶梓忆合住新一期的《男生女生》。
“什么雪?”
“我在楼底装了一袋雪,还在外边放着呢。这个张老师,占用了周练课,还一直叨叨说个没完了。”
“估计这会儿成一袋水了吧,”于果朝讲台看了一眼,“诶,晚上咱们去操场玩儿。”
“逃课?不行不行,我身为班长……”
“我爸说了,今晚上全城电检,会停电。”
“真的呀,不错呦。”
晚饭的时候,餐厅突然停电了,“哇”、”啊”的声音此起彼伏。混乱中,我们五个顺着窗外的一点点光亮走了出去,如约来到了操场。
操场上,偶尔有几对小情侣经过,通常两人一前一后,也极为隐蔽。那片沦陷了我们无数强烈心情的草地和橡胶跑道,被刻了清晰可数的几双脚印,如同我们晦涩的青春在上面留痕。
“吃棒棒糖吗?”我从兜里掏出一堆荧光棒棒糖。
“吃,谢谢浅浅,”叶梓忆拿了两支,给于果手里塞了一支。
“你们嘞,”我拿出其中一支棒棒糖,把棒掰了一下,荧绿色透亮了整支短小的空间,“这个是荧光的,你们要不要试试。”
林瀚抢过我手里的棒棒糖,“当然要试试,我省得掰了。”
林陌选了几支蓝色的棒棒糖,“少吃点糖,我没收了。”
因为突然停电,学校没备好足够的蜡烛,晚自习推迟了。我们在操场上一遍又一遍地回到上一圈的起点,然后踏过自己的印记。
后来,于果无意摔碎了“荧光棒”,为数不多的小块斑驳了不平整的雪地。
“真好看,”叶梓忆也把手里还没扔的小棒摔到地上。
远远看去,仿佛漆黑的夜把星空让给了雪地,满眼温柔。
踩过雪的“沙沙”声、捧着雪乱洒的空白心情、猝不及防被雪砸的惊喜表情,那些在心头盘旋的,也从不敢忘记的铭心纪念,都刻在永远停滞不前的昨天,等待我们去回忆想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