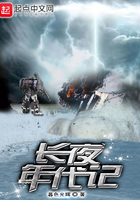圣都,申时。
公子惜去到帝宫宣读天诏,并非是在雨石苑的墨香阁内,而是封禁多年的璟暄殿。
璟暄殿,正是十九年前,司马子仁当着众臣出示先帝血诏的地方,乃是历代圣帝与群臣议事之地。一幢鎏金玉瓦的建筑,金色琉璃为窗,素色玉石作门,无处不在的氏族纹饰,金色铁线莲枝蔓缠绕,浮雕于白玉石墙,阳光照耀之下,金光四溢。
然而,自司马子仁即位,这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就此封禁。圣帝改以清雅的墨香阁作为议政之所,竟然也借此成全仁义之名。
公子惜当然不会理睬这些沽名之事,径直来到璟暄殿,挥手解了封禁,也不顾忌殿中尘埃遍布,阴冷弥漫,唤来值守帝宫的玄铠尉将,将圣帝及众臣请来进殿听诏。
当尉将说出听诏二字之时,司马子仁仿佛听到什么鬼话一般,顿时将面前的书案拍成齑粉,喝问道:“天诏?从何而来的天诏?!”
前日黎明时,齐自诺与司马子仁的一番交涉,正是为了这世间再无“天诏”。然而,尉将怎会知道这些?他战战兢兢地回答道:“御心公子惜宣众臣即刻前往璟暄殿,于申时宣读天君诏谕,特命末将请圣帝移步璟暄殿。”
司马子仁强行压住怒火,心中暗自计较:难道齐自诺连个十几岁的小孩子都对付不了?还是,他又在暗地里作妖?犹疑之间,司马子仁想到去往青峦峰的一万玄铠军,便问道:“言总督可有消息?”
“并无消息。”
“先锋营呢?”
“一切依常,并无异样。”
两天的风平浪静,忽然来了个天诏,而且偏偏在封禁多年的璟暄殿内宣读,这就奇了......司马子仁思之左右,虽是犹疑不定,却也不便就此与御心族撕破颜面。
璟暄殿之中,数十位朝臣跪了一地,司马子仁亦不例外。待这一道长长的天诏念罢,众臣皆是惊惧不安,暗地议论悄然四起。
司马子仁更是惊惶交加:原来这个十几岁的少年才是作妖的!三个无念境界的人,其中两个人还是一步而逍遥,带着一万玄铠精锐,这样都杀不掉一个小孩子?!难道他是无论怎样都杀不死的妖怪?!
司马子仁远远望着公子惜手中的白绢,突然有一种莫名的感觉:这一番举动,该不会是御心族在搞什么把戏吧?
恰巧,公子惜扫过一眼,从容言道:“不多时日,君尊自会召见众朝臣,也请诸位仔细斟酌,如何履行属臣之责,如何遵循天道之规。”
君尊召见......司马子仁不免游思沉浮:“若是沐氏断了传承,却不知君尊会是何人......若是御心公子悟坐上了天君之位,这天下又当如何?”
散了众朝臣,司马子仁仍是一派春风和煦的模样,谦逊温和得毫无破绽,“听闻公子一路风尘来到圣都,着实辛苦。若是无有他事,不妨移步雨石苑墨香阁,且以煮茶聊解乏意罢。”
公子惜亦不推辞,与司马子仁于帝宫内一路浅谈慢行,来到墨香阁内安坐。唤来茶官布茶,待茶过三巡,司马子仁斟酌再三,试探问道:“敢问公子,不知君尊现在何地休养?伤情可否要紧?”
公子惜却是慢条斯理地品茶,吊足了胃口,才缓缓言道:“其实,君尊并未受伤。区区封山的结界,又怎会伤到君尊。”
司马子仁不由心中一个咯噔:并未受伤?前日公子悯与公子憾拿着苍翠剑去找齐自诺兴师问罪,说是沾染妖毒,误入结界再受重创......
眼见司马子仁满面疑云,公子惜微微笑道:“子仁帝,你该不是当真希望齐自诺能在泠曙山一击得手吧?他若是功成,你确定他会善待司马一族?还是,天真地认为自己可以偏安一方?”
天真?若非血脉传承,天生便是帝王之后,司马子仁自认或许真能成为无瑕之玉,与子卿兄弟怡怡。他立即抛开这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公子误会了,寡人怎会对君尊心生不敬。只是目不识人,未能看清齐氏的狼子之心,确是惭愧。”
公子惜亦不揭穿,与他不痛不痒地闲聊了半个时辰,便告辞离去。
柳溪庄。及至戌时,正在书房内查看各分庄文书账目的影屏,忽而掌中聚集一团银云,惊喜之间,急忙去到茶室,找到对弈正酣的公子惜与公子悯,兴奋言道:“君尊来信!”
公子悯手中棋子一顿,“这么快?!”
影屏将掌中的银色云团送至棋盘之上,二人扫过一遍,公子惜不由笑道:“君尊当真是让我等一刻都不得安闲。”
影屏问道:“公孙雴云是否已然离开圣都?”
公子惜一面把玩手中白子,一面肯定地说道:“午后离开柳溪庄之后,他回滨水沼泽看了一眼,便乘赤隼去往暗影森林的方向。此时,应该已在迦楠院了。”
公子悯却有些担忧,“他能这么老实?不去泠曙山看一眼?”
“看什么?无非是确认月影的生死罢了。然而,他岂是看重他人生死的人?若是月影死后重生,必然要向一干人寻仇,最终得以搅乱天下,正是他梦寐以求的结果。”
影屏又问道:“公子惜,你看那司马子仁究竟打的什么主意?”
公子惜仍是不以为意,“什么主意?大概是与齐自诺一样,认为我御心族意欲翻覆天下。”
公子悯不禁噗哧一声,“齐自诺也就罢了,毕竟亲眼所见。怎地司马子仁也会这么想?”
公子惜却摆摆手,“要说这泠曙山当真是一个诡异的地方,我去山外探过一番,也是琢磨不透。一片死寂之地,寸草不生,唯一活动之物仅仅是山腹之内的熔浆。也难怪齐自诺等人深信君尊已然殒命。”
影屏却是想到另外一件事,“要不是天石是在暮宗山失踪......”
公子悯又笑道:“我说影屏庄主,天石于去年岁末遗失,月影却是六年之前失踪。莫说两座山相距百十里,时间也是隔着五年呐!”
公子惜止住公子悯的玩笑,严肃地说道:“公子悯,你不如即刻去一趟墨香阁罢。”
~~~
第五日,卯时。竹渊庄园,醉竹院。
云生站在二楼檐廊之上,望了望仍是漆黑一片的天色,揉了揉迷蒙的双眼,暗自发着牢骚:“天不亮就要备好早膳,难道修仙之人都不用睡觉的吗?原本以为,这位冷公子住几天就会离开,没有想到,一夜之间,他竟然成了竹渊庄院的新东家。”
一阵寒风扫过,云生拢了拢单薄的衣衫,接着自言:“若是他天天均是天不亮就要伺候着,那真是......也不知道为啥,再没见到与他同行的另一位公子,大概也是忍受不了他这般冷如冰霜的性情吧......”
正胡思乱想着,云生忽觉得眼前一暗,一股比秋风更森冷的气息从身旁飘过,只见一身玄衣的天落跃至院中,随即,平淡清冷的声音响起:“你且记住,醉竹院须每日仔细清扫,各个房间须时时焚香,院落不许见杂草落叶,青竹不许见尘埃枯黄。每日戌时之后,书房及茶室必见灯光,且不得移动或取走房内任何物件。我若发现有一项没有做到,便断你一指。你可听得明白?”
云生听得一个哆嗦,好像严冬时节从冰窟窿里捞出来一般,心里暗道:“这些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偏偏被他说得如此恐怖。”寒意森冷之下,他结结巴巴地应道:“公,公子放,放,放心,小~的,一,一定做,做,做到。”
话音且落,碎羽滑行而至,优雅地停在天落身边,亲昵地摩挲着衣衫,欢快地低鸣。天落也不多言,跃上碎羽之背,飞快地消失在黛蓝色的天幕之间。
未及半个时辰,天落依着灵体的记忆,引着碎羽来到柳溪湖上空,盘旋数周,寻得一片茂密的白桦林,钻入密林,于林间穿行片刻,停在一幢灯火璀璨的小楼前,正是柳溪庄内白墙金檐的闻樱阁。
闻樱阁檐廊之下,影屏、公子惜、公子悯及公子憾四人已是等候多时,眼见白鹤徐徐降落,便齐齐伏身行过礼,将天落迎入正堂之内。
天落仍是微闭双眼,在梨木椅端坐,随意地说道:“诸位不必拘礼,且请落坐罢。”待众人坐定,他问道:“圣都之事,诸位颇费心神,如今是否安排周详?”
公子惜微笑言道:“依君尊之意,均已安排妥当。”
天落略略点头,“辰时,在临水小楼内召见司马子仁即可。”
影屏立即起身,言道:“我这就去将茶室收拾一番。”
“不必。”天落淡淡地说道:“不过阶下之徒而已,书房即可。”
公子惜悄悄打量着天落,问道:“不知君尊打算在圣都盘桓几天?”
“两天足矣。”天落以灵识暗暗扫过数人,“你们先去临水小楼,我随后即至。”
众人起身告辞,公子惜却落在最后,踌躇片刻又返了回来,忧心忡忡地问道:“来到圣都后,我听公子悯提起血毒之事,我见君尊一直闭着双眼,难道是因血毒之故?”
天落却缓缓睁开双眼望向公子惜,紫色双眸依然流光溢彩,星辉醇厚,隐隐透着湛蓝色的光芒,“公子过虑了。”
公子惜颇为意外,略为尴尬地笑道:“惜确是想多了。”言罢,便欲离去,天落却说道:“无妨。你且安坐片刻。”
二人于闻樱阁内畅谈一番,及至辰时临近,便一同穿过白桦林,来到临水小楼外。
司马子仁已然在临水小楼的书房中等候,站得端正,满面谦谨,仪态一丝不乱,行止内敛平和,未见分毫逾越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