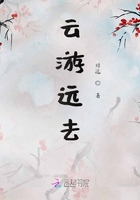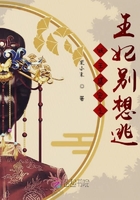南宫轶带着周身缭绕的酒气踏进房间时,便听见一声高过一声的唤声:“南宫轶------南宫轶------”
南宫轶感觉满天都开始带着微微的醺醉之意,少女每一次唤声都在迷乱撩拨着他的心。他三步并作两步,想快些把自己送到她的面前,让她抚摸他的心,感受他的感动。当南宫轶的头歪靠在门上,眨着眼睛,颇为动情地找寻佳人时,他看着那只黑色大狗摆着尾巴,昂着头,垂涎着顾谙手里的熟肉,眼睛里满是乞怜之情。
顾谙伸手轻抚着大狗,抚摸两下后却又故意地重拍了一下,嘟着嘴问:“南宫轶,我不好吗?”
南宫轶看着少女娇羞的模样,听着她婉转于耳的唤声,心里满足至极,不自觉地转回头,背靠门板上,以唇形道:“你很好,真得很好!”
屋内大狗“唔唔”了两声,看起来是得到了熟肉,正在欢喜地吃着。
“南宫轶?”
南宫轶刚要开口应声,却听到大狗又“唔”声。南宫轶恍悟,顾谙不知他回来,她在唤那条狗------
南宫轶倏然回身,堂皇入室,指着大狗怒问顾谙:“你唤它什么?”
顾谙猝不及防,被吓得一激灵,眼皮上下打了一架,抬起头,看着从夜色中闯入南宫轶,竟没有答话,却揪着大狗的耳朵,吃吃笑道:“他也叫南宫轶,你看他像你吗?”
大狗扭头看向南宫轶,突地“汪汪”不停,挑衅之势盛起。
“谙谙,你这是闹的哪遭?”
顾谙松开手,慢慢抚着狗耳朵,问:“未来大舅子的酒宴可好?”
南宫轶有些没有跟上顾谙的思维,顿了一下道:“无非走个过场,他如今亟需各国承认与支持,纵心里对我有不满也不会表现出来。”
“不满?”顾谙听言起身,径自对向面宫轶,脸上凝了冷意,问道,“二聘已送至长公主府,他对你还会有什么不满?”
“二聘?什么二聘?”南宫轶不解道。
顾谙呼出一口气,南宫轶这才注意到顾谙喝了酒,疑道:“谙谙,你喝酒了?”
“允你喝的,我就喝不得?”顾谙耍着性子道。
“早知你想喝酒,我今日便不赴宴了,只陪你喝酒。”
顾谙摇头:“宫宴最费时,倘不拉你赴宴,二聘如何能瞒着你送达?”
“二聘?谙谙你是说给唐不敏的二聘?”
顾谙眼底流过黯然:“南宫轶,恭喜你,佳偶天成。”
南宫轶心一沉:“谙谙既早知为何不先拦下?”
“南宫轶,我是你何人?为何要拦下你娶亲的聘礼?”
“那也可以先劫下啊?”
“然后让天下耻笑我的花痴,一而再地为你劫聘礼?”顾谙反问道。
“此事怪我,是我大意,没有想到母后会隐瞒我行事。谙谙别生气。”
“南宫轶,我有什么权利生气?有什么权利指责你?没有。你没有错,这场世人皆知的婚事里我是闯入者,但有错都在我,在我------”
南宫轶将顾谙拥入怀,安慰道:“谙谙,你没有错,错在我,是我疏忽。不要难过,我来解决。”
顾谙推开南宫轶的怀抱,摇头道:“情之一事最是伤人,这话真是不假。所以南宫轶,我不想与你再谈情,你也不要再来烦我。”
南宫轶再伸手去拉顾谙,顾谙向后一撤,扭身跑了出去,南宫轶紧追而去。
室内,大狗愣着神地环看着满屋的空荡,不适应地吠起来。
隔壁,女姁吓道:“破狗,入夜别叫了。”
大狗却跑到门口,对着远去的两个黑点狂吠着。
女姁不悦道:“破狗,哪天宰来吃肉喝汤。”
犬吠声倏止。
“瞧,道理有时候是讲不通的。”
章儿将头认真地埋在绣绷下查看自己下针是否正确,然后小心地摩挲着被绣的七扭八歪的怪图案,满意地点头,准备继续往下绣。
女姁看着惨不忍睹的绣面,开口道:“谙儿今晚喝了一壶四路酒,这大晚上的你不用跟着保护?”
“小姐虽不是我的对手,但行走江湖不是问题,再说这里是唐不愠的围苑,他会不派重兵把守?”
女姁立在章儿身后,研究着她绣的到底是枯树枝还是烂竹子,又道:“我瞧着两人拌了口角,你确定不用跟去劝和劝和?”
章儿抬眼笑道:“若真散了,不是正合四师您心意?”
女姁终是直言道:“章儿,你在刺绣一事上真是不会有作为了,还是作罢吧!”
章儿听了女姁的话,不甚同意地将绣绷举过头顶,对着烛光又辨了辨,道:“还好吧?我觉得有些蝴蝶的模样了。”
“章儿,去外面随便找只死蝴蝶,我给你钉在绣绷上,保证瞧不出假的。”
章儿拒绝道:“他说想要个我亲手绣的帕子。”
女姁抚额叹道:“你想像一下手里拿的不是绣花针,而是支暗器,看会不会好些?”
章儿反问:“四师你也懂刺绣?”
“我不懂,但我不瞎。”女姁道。
“四师您这么无聊,不如您去看看小姐?”章儿撵人道。
女姁活动活动身子,不屑地转身离去。身后章儿绣绷上突地活出两只飞舞的蛱蝶在渐现的花中灵动展翅,章儿怒起,朝女姁凌空的方向喊道:“四师,你欺负我!”
半空,有笑传来。
围苑某处,却有歌声传来。
女姁驻足,那是顾谙的歌。
“那是个遥远遥远的地方,
那里的夜晚星星特别明亮,
我就是在那辽阔的土地上,
伴随着阿妈温暖的歌儿成长。
是谁在呼唤我儿时的名字,
是谁还在风中静静遥望,
我还是站在这无边的土地上,
告诉阿妈孩儿要去远方。
(这是首蒙古歌——《遥远的妈妈》)
有心事的女孩,想娘了。
女姁静静地立在当处,不再向前行,转身开始向回走。
自夫人去世起,她便将顾谙看成自己的孩子,希望她活成最快乐的自己。
可是,有心事的女孩,心里总有一个角落是不快乐的。
围苑里青草香浓郁,少女坐在山丘上,眼望着天,哼唱着从小的歌谣。
南宫轶听着歌里的忧伤,拥着少女的手更紧了。
星辰在高空悬挂着,彼此无相偎,它们俯视着人间这一对。
山风打着转,伴女姁默默前行。
“南宫轶,曾经我以为情爱与我无缘,以为某一天找个与自己名称相当的人嫁了,或守着相师堂孤身一世,这就是我的生活,我不长久的人生。”顾谙看向南宫轶,认真道,“我看过许多人的情爱,包括我爹娘的,以为情爱最伤人,所以固执地认定自己不会嫁给爱情。白日里我也存着不会嫁你之心,以为无论是你付与谁的聘礼,你娶了谁都与我无关。我不过是你曾喜欢过的那个人,你不过是我曾用心去待的某个人。可是,现在我不愿这样去做了。即使我不嫁你,也不愿你娶别人为妻。南宫轶,这样自私的我,你还愿意接受吗?”
南宫轶深情的眼底一片澎湃:“谙谙,此生你不嫁,我便不娶。”
(《世说新语》中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