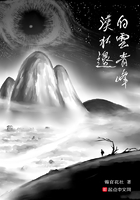初六,是送穷的日子。
天蒙蒙亮,王庆就被牛小娇扯出了被窝,心不甘情不愿的走到院子里。
王砉、王进、惜春都在,全都眼巴巴的盯着他看。
一般送穷,就是初一到初四不倒垃圾,等初五的时候再一起倒。那么宋朝如何送法呢?
‘探聚粪壤,人未行时,以煎饼七枚覆其上,弃之通衢以送穷’。
用大白话说,就是大清早弄一铲子大粪,盖上七张煎饼,然后扔大街上去。
这就太恶心了。
过没多会儿,牛小娇掩着鼻子从茅厕里走了出来。王庆见她手里平举着一铲子,凑过去看了看,端的好大一坨,兀自冒着热气。
在王砉的指挥下,惜春抱了七张煎饼过来,二话不说,直接盖在了上边。
牛小娇把铲子递给他,笑道:“去倒街上吧。”
王庆苦着脸说道:“倒街上多不卫生啊,我这辛辛苦苦的盖起来的房子,到处倒屎算是怎么回事。”
牛小娇柳眉倒竖,喝道:“不去倒了,一年都要受穷。”
王庆还待分辨,诸人一发上,围着他就是一通声讨,连王进都说习俗不可破。他一张嘴敌不过七嘴八舌,只得捏着鼻子接过铲子,摇头走出了家门。
走没几步,就看见悯月端着铁皮铲子,唉声叹气的走了过来,就差把倒霉二字写在脸上了。
“妞儿,你也来了。”
悯月唉声叹气的说:“以前府里有下人做这些,现在家里就我和娘子两个,我不来,难道让娘子动这些污秽么。”
“这话说得,我堂堂一寨之主,还不是端着大粪到处走。”他左顾右盼了一会,问道:“这玩意倒哪里啊。”
“又没有街道,随便找个地方倒了就是了。”
王庆一脸嫌恶的说:“我家这一片人来人往的,行人踩了,还得在我家里刷鞋洗浴,多恶心。咱找个远点的地方倒吧。”
悯月想了想,道:“说得也是,那就走远一些。”
两人顶着冬日清晨冷冽的风,人手一铁皮铲子,满脸嫌恶的前行。
悯月跺了跺脚,一脸不悦的说:“我不想再走了,倒这算了,好恶心。”
“啊?”王庆苦笑道:“倒在宝哥家门口,不大好吧?”
“这有什么,又没倒他家院子里,再说了,他又不知道是咱俩。”
王庆连连摇头,道;“不妥不妥,宝哥对我忠心耿耿,我往他家门口倒屎就太过分了。而且这不是一般的粪,这可是穷啊。”
“你好生啰嗦。”悯月气愤愤的在他胳膊上打了一下。
王庆平端着铲子走了半天,胳膊又酸又麻,手一抖,铲子里的东西就摔在了地上。
“呀,这可是你先倒的。”悯月一边呵呵笑,一边把她铲子里的污秽倒在地上:“这不就成了。”
王庆仰天一声长叹:“可怜我一世英雄……”
话才说了一半,大门吱嘎一声打开了,李宝提着一铲子走了出来,看见王庆还打了个招呼,一低头,可就看见地上的东西了。
王庆这个郁闷,连忙辩解道:“宝哥,事情不是你想象中那样的,你听我解释……”
李宝脸色铁青铁青的,咬牙切齿的说:“你俩也太过分了,合起伙来欺负我,罢罢罢,今日不报复回来,我妄称小关索!”
说着,他端着铲子,雄赳赳气昂昂的往王庆家走去。
悯月大怒,拦在他面前喝道:“你想干什么?”
李宝斜瞥了她一眼,哼道:“你最好让开些,不然溅你一身粪便,可别怪我。”
“还反了你了!”悯月双眸一瞪,抬腿就是一脚,踢在了铲子上。
那铲子一颠,上面的煎饼登时飞起,直打在李宝脸上。
王庆在一边都看呆了。
李宝发了半天的愣,面孔渐渐变得狰狞,咬着牙一字一顿的喝道:“悯,月!”
“妈呀!”悯月眼见头势不好,掉头就跑。
李宝哪里肯放,跟在后边就是一通狂追。
“这都什么事啊。”王庆看得又好气又好笑,他寻思着回家可能撞见李宝,这哥们糊一脸粪饼,多半疯魔了,还是不见为妙。略略一想,就溜溜达达的去了白秀英家。
到时,阎光正提着一铲子往外走,王庆对这玩意甚是抵触,见了躲得远远的,等他走远了才过去敲门。
开门的是阎光浑家阎刘氏,三十四五年纪,穿上绫罗绸缎后,也勾勒出几分丰韵。
“寨主来啦。”阎刘氏见是王庆,十分热情,把人请进厅里,就忙着去沏茶。
“不用忙,我去找秀英说点事。”
阎刘氏笑道:“白娘子和小女正在琴房练琴,老妇给寨主引路。”
飘香别院建在空旷山头上,占地颇广,足有二十多间屋子。因总共只有几口人住,所以空屋子极多,各种琴房、乐房、书房、收藏室应有尽有。
刘氏把他领到琴房门口,就离开了。
王庆推门而入,不见白秀英,只有阎婆惜在拨弄琴弦。
见是王庆,阎婆惜离座而起,笑盈盈的说:“寨主今天来的恁早?”
王庆找了个榻子坐下,叹道:“还不是送穷送的。”
琴房里有沏好的茶,阎婆惜给她倒了一杯,递到面前,一双俏眼只顾在他身上睃来睃去。
王庆被她瞧得浑身不自在,接过茶碗问道:“秀英呢?”
“秀英姐去书房拿西厢记了,过会儿便来。”
王庆应了一声,低了头只顾喝茶。
不片时,白秀英拿着剧本走了进来,见了他不由问道:“你怎么来了?”
她一来,王庆就没那么拘谨了,苦着脸把送穷的事讲了一遍。
二女听到悯月飞起一脚,把饼连着粪都掀在李宝脸上,一起大笑起来。
王庆目光扫到阎婆惜花枝乱颤的娇躯,心脏为之一紧,双眸为之一迷,忙侧过了头,不敢直视于她。
这就是个妖精啊。
白秀英目光如炬,看出他尴尬,便侧顾阎惜娇:“妹子,你去把大伙都叫来,准备好家伙事,把咱排好的两折演给寨主看。”
阎惜娇应了一声,袅袅婷婷走了出去。
王庆惊讶的看着她:“这就排好两折了?”
白秀英笑着和他说明了原委。
因为之前答应秀英,要唱两段给她听听,王实甫的西厢他又没听过,只得把南西厢默写出来,递给她,然后硬着头皮唱了一折佳期。以他这嗓音唱佳期,就像让腾格尔飚海豚音一样,可想而知,白秀英直接被他给唱跪了。
既然指望不上王庆,她只能依靠自身经验去摸索,去创造。作为一个先行者,她完全不清楚真正的昆曲是什么样的,事实上在听王庆唱了一段后,她对那种唱法不由自主的产生了抵触。
她和阎惜娇商榷了许久,又征求了林娘子、童娇秀等人的意见,毅然选择丢开王庆那本小册子,开辟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王庆听了甚是期待。
昆曲是好,可惜缺个真正的行家作师傅,单凭理论文字如何能行。王庆的水平属于一瓶不满半瓶晃荡,让他教白秀英唱曲,就像让张青指点林冲枪法一样,越教越迷糊。
白秀英瞥了他一眼,道:“你若是看上婆惜,收了她就是。又想看人家,看了就发情,然后又要躲,我都替你累得慌。”
王庆老脸一红,道:“好端端的,怎么说起胡话来了。”
白秀英伸脚在他双腿间撩了一撩,道:“别人又不是瞎子,鼓成这样,还要瞒骗哪个。”
王庆辩无可辩,只得叹口气说:“婆惜身姿曼妙,确实惹火。只是这妮子可以远观,不可深交,我这还有多少大事要做,没空。”
白秀英疑惑的望着他:“婆惜虽是常常撩拨你,也是一片爱慕之心。奴家只见她容颜妩媚,聪明伶俐,哪有你说得这么不堪。”
王庆微微一笑,道:“你不懂,我天生有识人之明,一个人秉性如何,我一眼就能看得分明。”
白秀英哼了一声,道:“你要觉得她为人不堪,为何又想法设法把她弄到山上来。你坐拥八百里梁山泊,多养几个人无妨,却不是误了她一生。”
王庆神色一正,道:“其实是因为我做了一个梦,话说那郓城县……”
白秀英不待他讲,欺身上前,小拳头对着他后背就是一通乱锤:“上次说的那个梦,我至今还怕得不行。好容易缓了缓,你又要做梦,你就不能好好睡觉,整日价作甚鸟梦!”
王庆笑着打趣道:“别打了,再打雷横要来了。”
白秀英尖叫一声,果然住了手。
王庆回头看时,只见她两行清泪簌簌滑落脸颊,连忙劝道:“乖,乖,不哭了。不是说了么,有我在此,那雷横断不敢招惹你,他敢动你一手指头,哪一根碰的我就剁下哪一根,好不?别哭了,别人听见只道我欺负你了。”
白秀英一头扎进他怀里,拳头在他胸膛乱打,带着哭腔嗔道:“你就是欺负我了,没来由编那故事吓唬人。”
王庆无奈,只好温言劝慰。这状况纯属自找,要怪,也只能怪自己嘴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