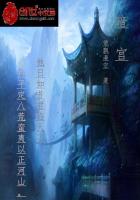在相扑勾栏里,女飐只是一场开胃菜,拿出来热热场子。
之后的男摔,才是正菜。
王庆正看得兴起,听得旁边哈欠连天,侧头看去,牛小娇一脸的困倦:“娘子,困了啊?”
牛小娇揉揉眼睛,吐了吐舌头:“奴家只爱看女飐,男人相扑不好看。”
王庆刮了刮她的鼻子,笑道:“说的也是,俩老爷们光膀子摔跤,有甚好看的。走,再带你逛逛去。”
牛小娇犹豫了一下,道:“可是都交过钱了,不看完岂不是亏了,二百钱呢。”
“二百钱博娘子一笑,值得很。”王庆说着,起身拉住她的手,带她离开。
别说,退场的还不少。也不是谁都爱看俩肌肉棒子互摔,好多人就是冲着女飐来的,看过瘾就走,一点也不留恋。
出了勾栏,走到大街上,月已中天。
牛小娇抱着他一条胳膊,头也歪在他臂膀上,脸上浮现着一抹悠闲静谧的意态。
真是容易满足的女人啊。
王庆宠溺的摸了摸她的发髻,牛小娇抬起头,冲他咧嘴一笑。
这一笑又安静,又纯净,又甜美,把王庆的魂都勾去了,忍不住弯下腰,在她脸颊上亲了一下。
牛小娇倏的跳开,似笑似嗔的斥道:“浪什么,在街上也不怕人笑。”
王庆一跃身捉住她,把她揽在怀里:“怎么,你怕人笑话啊?”
牛小娇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听了这话,搂着他脖子跳起来,在他脸上使劲嘬了一口。
旁边有斯文人路过的,斜瞥着两人大摇其头。
有那年少轻狂的,热血上涌,也要学王庆亲吻女伴,嘴唇还没落下,头上先重重挨了一记爆栗。
王庆微微笑道:“多时不见你这般快活,以后我时常带你出来逛逛,好过在家里闲闷。”
牛小娇双睛发亮,紧拽着他的胳膊说:“可是说定了呢。”
王庆点点头,道:“嗯,说定了。”
牛小娇大喜过望,乐得蹦蹦跳跳,像个孩子一样。王庆拉着她一只手,看她在街上撒欢,心中像是抹了蜜一样甜。这种简简单单的感觉,已遗失了太久太久。久到,已记不起来何年何月了。
两人迤逦而行,沿路买些甜点吃,说说笑笑,到了岳庙前。
“夫君,可要去庙里上柱香?”
王庆晓得上香是要花钱,笑着摇摇头:“有那钱,不如买些好吃的给娘子将养身子。”
牛小娇嗤嗤一笑:“都被你养胖了一圈,再养可是要胖成小猪了。”
王庆故作诧异的望着她:“世道真是变了,连小猪都如此美貌,看来娶妻还不如娶头猪。”
牛小娇笑骂着拍打他:“驴怪物,又作怪。”
正说着,忽听东侧传来一阵喧闹,王庆是个好事儿的人,拉着牛小娇就凑拢过去。
抬目望去,只见几个人拿着弹弓、吹筒、粘竿,都立在栏干边,胡梯上一个衣着华丽的后生独自背立着,伸手拦着一个雍容美丽的妇人,笑嘻嘻说道:“你且上楼去,和你说话。”
妇人红着脸,转头想走又被几个帮闲的拦住,气苦道:“清平世界,是何道理,把良人戏弄!”
王庆吃了一惊:“这个不是我林家嫂嫂?”
上次鲁智深倒拔垂杨柳,这次高衙内调戏林娘子,两回都让他赶个正着,冥冥之中,怕是已有定数。
王庆侧头看了牛小娇一眼,她杏眼圆睁怒啐了一口:“只管呆看个鸟。瞎了他的狗眼,连我嫂嫂也敢欺辱,夫君你还不过去厮打,打死打残,老娘赔他家钱!”
“得嘞。”王庆正待出手,林冲如风似电般赶到,把那后生肩胛只一扳过来,大喝一声:“戏弄良人妻子,当得何罪!”
拳头待要落下时,林冲看清了你无赖后生的脸,身子一滞,拳头便停在了空中。
王庆无暇多想,吩咐牛小娇站远些,一个纵身跃了出来,口中爆出炸雷般一声大吼,伸手便去揪高衙内。
林冲正犹豫不定,见王庆猛虎般冲过来,生怕打坏了高衙内,高俅面上说不过去,慌忙将身抱住王庆,苦劝道:“贤弟休要上前,愚兄自有理会。”
王庆双眼瞪得如牛铃一般,嘶声吼道:“争奈这厮无礼,欺辱俺嫂嫂,俺便把他一双狗腿打残,看他今后如何再行歹事。”
王庆在汴京也是有名的风流子,围观的见他说出这番话,无不窃笑。大哥别笑二哥,你自身也不是什么善茬,还有脸去骂别人。
高衙内认得林冲,不识王庆,当即发作道:“林冲,干你甚事,你来多管!”
林冲本来把心思转在拦王庆上,高衙内此言一出,又勾起他胸中怒火,转过头来,双目如刀子般狠狠瞪向高衙内。
帮闲的虽多,哪敢和林冲王庆厮斗,纷纷上前相劝:“教头休怪。衙内不认得,多有冲撞。”
林冲虽怒气填胸,终究碍着高俅的面子,下不得手。
帮闲们见状,也不管高衙内愿不愿意,簇拥着就走。远远的,兀自听得高衙内大呼小叫:“小娘子,俺是当朝高殿帅之子,跟了俺,保你一世荣华富贵!”
王庆拳头攥得咔咔作响,恶狠狠的说:“这厮一贯仗势欺人,哥哥如何不让俺打他一顿。”
林冲苦笑一声:“他是高俅的螟蛉之子,打了他,殿帅面上需不好看,只得饶他一次。”
正说间,鲁智深大步奔来,后面跟了十多个泼皮,个个摩拳擦掌。
林冲见了,叫道:“师兄,哪里去?”
和尚雄赳赳的将禅杖砸在地上:“洒家来帮你厮打!”
林冲道:“原来是本管高殿帅的衙内,不认得荆妇,一时间无礼。林冲本待要痛打那厮一顿,他父亲面上须不好看。权且让他这一次。”
鲁智深闻言大愤,把禅杖狠狠落下,直将地面捅出一个坑来:“你却怕他爹是殿帅,酒家怕他甚鸟!俺若撞见那撮鸟时,且教他吃酒家三百禅杖了去!”
林冲知和尚莽撞,怕他真个去打杀了高衙内,连声劝阻。
王庆立在一旁,若有闲思。
别人不知,他却晓得这件事并没到此为止。高衙内会接二连三的出招,最狠的是一招‘持刀误入白虎堂’。这一招直接让林冲身败名裂流配沧州,从此走上一条落草为寇的不归路。
王庆帮他过白虎堂这一关不难,到时候提点两句,林冲也不是傻子,自能看出其中的厉害。这种陷人的招数,只要识破就彻底废了。
问题是,救也只救得一时。
高衙内只要不死,就会对林娘子死缠不休,早早晚晚寻个错过,也要摆布了林冲。可若不救,有失兄弟义气。
正寻思间,耳中响起炸雷般一声大喝:“直气破了洒家的肚皮!”
“智深哥哥,休要闹了。林教头心情不好,咱们去陪他喝酒,嫂嫂受了惊吓,正好让内子陪她说话解闷。”
林冲不想把事情闹大,闻言连连点头,左手挽着王庆,右手挽着鲁智深,径回家中。牛小娇则陪伴林娘子,劝慰她看开些,只把高衙内当个屁放了。林娘子是个文雅女子,见她满嘴脏话,骂骂咧咧,觉得有趣,不一会儿竟被逗笑了,和牛小娇一起咒骂高衙内,污言秽语,骂得甚是畅快。
林冲回到家里,仍是郁郁寡欢。王庆和鲁智深不住的劝酒,彼此痛饮。
当夜喝了个酩酊大醉。
王庆摇摇晃晃回了家,在牛小娇的服侍下洗了个热水澡,舒舒服服的躺到了床铺上。
喝酒的时候,他心中就有了决断;林冲的事,不插手。
靖康之难不会因为天地玄变而消泯,王庆自付无力改变天下大势,可他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家兄弟投身劫难。林冲刺配,这是冥冥中给他的一条生路。
自己把这件事抹过去了,林冲不经这场劫难,肯定死心塌地的留在京城当教头。过几年金兵打进汴京,以林冲的性子誓必死战到底,闹个玉石俱焚。这算是救人,还是害人?
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理由,可明知兄弟有难,却袖手旁观,任他去吃苦受罪,心中难免还是有几分愧疚。
“罢了,我保住林家嫂嫂,便是了。”
喃喃的念叨了一句,脑门上登时挨了一记巴掌。牛小娇横眉立目叉着腰,气急败坏的冲他叫道;“驴怪物,做什么就去抱住林家嫂嫂。天天在外面沾花惹草也就罢了,如今作这歹念,好不知羞耻!”
王庆捂着脑袋苦笑道:“娘子,你听差了。我说保住,不是抱住。那高衙内是个难缠的主,既然看上了嫂嫂,早晚寻个事由害了林冲。身为结拜兄弟,我当然不能坐视他家破人亡了对不对?”
牛小娇半信半疑,哼道:“又说大话。那高衙内又不是凶神恶煞,岂会为了这点事就害人家破身亡。再说是他撩拨嫂嫂,又不是林大哥去招惹他。”
王庆摇摇头,长叹一声:“你还是不了解那些纨绔公子啊。在他们眼里,草头百姓都是待宰的羔羊,想害你还需要理由?说让你死你就得死,他办不到,他爹高俅自能替他打点一切。”
牛小娇听得不寒而栗,身子向后缩了缩:“听你这一说,奴家怎么觉得这汴梁城这么危险呢。”
“人生何处不凶险,几人命能不由天。”王庆伸手搂住她腰肢,柔声道;“将来事将来了。春宵苦短,娘子咱们歇了吧。”
牛小娇满面绯红,倚入他怀中:“死怪物,整日没个正行。”